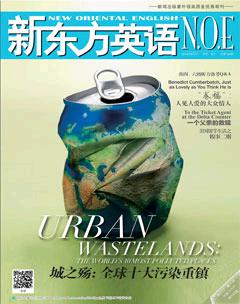翻譯擂臺
His words were green and red, but of a light shade showing me he believed them.
如今看到這一池的蓮葉,就像看到了一池的清涼。
上述兩部分分開評獎,參賽者可任選其一進行翻譯。譯文請在2014年6月10日前在網上提交,網址為http://www.dogwood.com.cn/intro.html;或者用稿紙謄寫工整,寄往北京市海淀區海淀東三街2號新東方南樓19層《新東方英語》編輯部“翻譯擂臺”收,郵編為100080,截止日期為6月10日(以郵戳為準)。我們將隔期刊登有關譯文的詳細評點,并評出若干名最佳譯手(獎品:《一瞥一驚鴻——一生必看的58部電影(下)》)和潛力譯手(獎品:《漂亮的英文句子——英文這樣寫就對了》)。快來一試身手吧!
2014年4月號英譯中獲獎名單
楊龍 崔秀忠
葛嬌嬌 潘蓀億 黃媛
2014年4月號中譯英獲獎名單
陳曉燕 方埼逍逍
趙莉莉 肖月 呂鵬
在上一期的翻譯擂臺評點中我們提到,在翻譯夸張修辭格時,譯者在理解方面不存在太大問題,因為夸張修辭格的字面含義違背常規,很容易引起譯者的警覺,聯系上下文就不難理解其真正的含義,但如何在譯文中表達有時卻不好辦。這其中的原因在于英漢兩種語言的表達習慣不同,如果照搬原文的表達方式來翻譯,譯文讀者可能不理解夸張修辭格的含義,或是雖然可以理解其含義,但會覺得生硬;如果在譯文中進行靈活處理,又可能曲解原文的意思,或是削弱原文夸張的力度,影響原文的修辭效果。也就是說,即便理解不成問題,譯者要翻譯好夸張修辭格也要過兩關:一是決定原有表達方式的去留,二是在決定舍去原文表達方式后考慮如何變通。在翻譯實踐中,這兩關都不好過。本次翻譯擂臺的參賽譯文就體現了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具體分析。
2014年4月號翻譯擂臺英譯中評點
英譯中題目
At that time Bogota was a remote, lugubrious city where an insomniac rain had been fall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y.
翻譯要點
英文原文是最近剛剛去世的拉美作家馬爾克斯的一部作品中的名言,已成為英語修辭學教科書中一句經典的夸張例句。其中rain had been fall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y明顯使用了夸張修辭格。無論什么地方也不可能從16世紀初開始就一直下雨,這么說的目的是極力渲染波哥大的陰郁,與lugubrious和insomniac兩個詞相呼應。這一處夸張理解起來并不難,但許多參賽譯文在夸張的表達上出了問題,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問題一 參賽者對原文的夸張進行增譯,導致夸張的程度減弱,修辭效果受到影響。
例:那時的波哥大是一座偏遠的、充斥著陰郁氣息的城市,自16世紀初以來,它就經常陰雨不斷,令人難眠。
評析:譯文中添加了“經常”一詞,把原文中過去完成進行時所表示的不間斷的現象改譯成了間歇性的現象,夸張效果大打折扣,甚至看不出是夸張,因為有些地方確實會經常陰雨不斷。原文夸張所營造的心理上的壓抑感在譯文中消失了。之所以有這樣的增譯,估計是因為譯者擔心直譯原文中的夸張表達法會讓讀者難以接受,但這種擔心沒有道理。既然是夸張,就是要突破常規,讓人在出乎意料、不合常理之處看到內在的邏輯,增強表現力。有前面的lugubrious和insomniac兩個詞,讀者應該可以理解夸張的用意。
問題二 參賽者套用漢語習慣用語,譯文意思不準確,削弱了原文的修辭效果,或是賦予了額外的含義。
例1:在16世紀初期,那個時候波哥大還是一個地處偏遠的小城鎮,常常陰雨綿綿,一片凄然的景象。
例2:那時,波哥大是一個偏遠、陰郁的城市,霏霏淫雨從16世紀飄落至今。
評析:第一個譯文使用了常用的四字詞“陰雨綿綿”,并在前面增譯了“常常”,來譯原文中的“… rain had been falling …”。譯文讀上去非常流暢自然,表達的意思也和原文接近。但仔細分析,譯文和原文的意思還是有差異的。前者強調的不僅是“雨”,還有“陰”,即天一直是陰著的,但雨未必一直在下,這和原文中所說的不間斷的雨有所不同。況且,“陰雨綿綿”也是一種自然現象,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會“常常陰雨綿綿”,這樣翻譯使原文中的夸張消失了,譯文的修辭效果因此也遠不如原文。第二個譯文用“霏霏淫雨……飄蕩至今”來譯原文的夸張,意思與原文接近,但也有細微差別。“霏霏淫雨”顯然是借用了范仲淹《岳陽樓記》中“淫雨霏霏”的說法,描述的就是一直不停的雨,也是一種夸張的說法。但是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淫雨”指的是“連綿不停的過量的雨”,“霏霏”是雨雪紛飛的樣子,二者合在一起,所表達的含義比英語原文要豐富得多,不僅多出了對雨的形狀的描述,還多出了對雨的態度,即“過量”。這和原文貌似客觀中立的描述有所不同,因此嚴格來說,這種譯法也不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有將近一半的譯文都用了類似的譯法,這說明參賽者對原文夸張修辭格所表達的意思都理解了,漢語的表達能力也很好,但沒有意識到套用習慣用語的弊端。雖然有些翻譯教材里主張多用“地道”的漢語表達,但在翻譯實踐中卻要謹慎使用套用現成習慣用語的譯法,除非迫不得已,不應削足適履,用不準確的慣用法去翻譯外語原文。
問題三 參賽者誤譯時間狀語,削弱了夸張的程度。
例1:波哥大曾是一個地方偏遠,陰郁彌漫的城市,從16世紀開始,這里的雨就下個不停,從不歇息。
例2:16世紀初,在波哥大,這個偏遠而陰郁的小城,雨一直下著,令人難以入睡。
評析:第一個譯文把原文中的beginning漏掉了,第二個譯文把原文中的since漏掉了。 “16世紀”和“16世紀初”、“16世紀初”和“自16世紀初開始”在時間上還是有明顯差異的。這樣一來,譯文的夸張程度就不如原文了,表達效果自然會受到影響。再者,像馬爾克斯這樣的作家用詞造句都很講究,原文把時間描述得這么具體必然有其用意,譯者不應輕易改動。況且把原文直譯過來并不影響譯文的可讀性。兩個譯文還都把原文中的at that time省略了,這說明譯者對時間狀語很不敏感,忽視了其重要性。
除了在夸張修辭格的表達方面存在問題外,參賽譯文還存在以下兩類問題。
問題一 參賽者無故增譯,譯文增加了原文所沒有的成分,意思與原文有出入。
例:那時,波哥大是一個幽遠,陰郁的城市,從16世紀初開始整個城市籠罩在失眠的細雨中。
評析:譯文中的“細”是原文所沒有的,原文只是說波哥大的雨讓人失眠,雨量如何并沒有說,“細雨”把原文模糊的內容具體化了。漢語中的確習慣用“細雨”這樣的表達法來描述人悲傷、哀怨的心理,但就本句來說,按照原文忠實翻譯,讀者同樣可以看出原文所要描述的心理,因此這種增譯是沒有必要的。
問題二 參賽者對原文中的移就修辭格處理不當。原文中有兩處移就。一是lugubrious,《新牛津英語詞典》對這個詞的解釋是“looking or sounding sad and dismal”,也就是“悲傷,憂郁”的意思,其邏輯上的修飾對象顯然應該是人,意思是人到了波哥大后會感到憂郁。另一處移就修辭格是insomniac,即“患失眠癥的”,其邏輯上的修飾對象也應該是人,意思是波哥大的雨讓人失眠。正如以前我們在翻譯擂臺的評點中指出的那樣,移就修辭格的翻譯在理解和表達兩個環節都有不少陷阱,譯者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現問題。下面我們分別來看參賽者在翻譯這兩處移就修辭格時在理解和表達方面出現的問題。
就理解方面來說,參賽者出現的錯誤主要是對移就修辭格進行解釋,但意思不準確。
例:那時的波哥大既偏僻又陰沉,自16世紀初一直下著令人心煩意亂的雨。
評析:原文中的insomniac被翻譯成了“令人心煩意亂的”。一個地方如果一直下雨,確實會讓人心煩意亂,但心煩意亂是指心情煩躁,與憂傷或憂郁有所不同,與前面的lugubrious無法形成呼應。也就是說,這種譯法是譯者根據生活經驗做出的推斷,忽視了句子內部的聯系。更重要的是,此處譯者沒有必要把原文所暗含的意義明確地表達出來,按照原文進行直譯,讀者也能夠理解其含義。這種以明示代替暗示的譯法是翻譯初學者常犯的一個錯誤,誤以為這樣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卻沒有想到任何明示都只是譯者的一種解釋,與原文的暗示并不完全相等。如果譯者功力不夠或是對上下文的理解不充分,這種解釋甚至有可能是錯的。因此,除非直接翻譯過來確實難以理解,否則譯者沒有必要加以解釋。
參賽者在移就修辭格的表達方面的錯誤要多一些,主要有三類:一是漏譯移就;二是機械翻譯移就,譯文表達不自然;三是用詞不當,移就修辭格消失,削弱了表達效果。下面來舉例說明。
例1:自16世紀初以來,連綿不休的雨水落在波哥大,那時的一座遙遠、陰郁的城市。
例2:那時的波哥大是個偏僻而可憐的城市,從16世紀初起,那兒的雨就日夜不寐地下個不停。
例3:在那時,波哥大是一個遙遠、悲慘的城市,自從16世紀開始就一直下著失眠的雨。
評析:第一個譯文漏譯了原文中的insomniac一詞,雖然譯文讀起來很流暢,但以省略原文關鍵信息為代價的流暢無論如何是不值得提倡的。在翻譯實踐中,有兩種省略比較常見,學術界通常也予以接受:一是原文意思有重復,比如說近義詞疊用,其含義在譯文中沒有必要完全體現出來;二是原文的含義在譯文中難以表達出來,強行表達的話譯文會太生硬。原文中的移就不屬于這兩種情況,因此這里的省略只能看做漏譯。
第二個譯文忠實地把原文insomniac的意思翻譯了出來,譯文意思沒有錯,但“日夜不寐”的主語是“雨”,譯文讀起來比較生硬。在漢語中,“不寐”一詞明確指人,很少用來指物。連淑能在《英漢對比研究》一書中把人稱主語和物稱主語看做漢語和英語的主要區別之一,原因就在于漢語傾向于用人作主語,英語傾向于用物作主語。對于明確指向人的動詞,漢語更傾向于用人來作主語,用物作主語讀起來會很不自然。
第三個譯文用“悲慘”來譯lugubrious,雖然和“悲傷”只有一字之差,但修辭效果有很大差別。“悲慘”的邏輯主語未必是人,可以是波哥大這個城市本身,比如受到了災害的破壞。也就是說,如果用“悲慘”,原文的移就修辭格就消失了,表達效果比原文要差很多。
獲獎譯文:在那個時候,波哥大是一個偏遠而陰郁的城市,在那里從16世紀初開始一種令人失眠的雨就一直在下。(陳曉燕)
評析:譯文對夸張修辭格的翻譯沒有問題,對移就修辭格的理解也全都正確,但“令人失眠的雨”這種表達略顯生硬。對其略作修改,就有了下面的參考譯文。
參考譯文:那時波哥大是個偏遠而憂郁的城市,從16世紀初開始那里就一直在下雨,令人失眠。(韓子滿)
2014年4月號翻譯擂臺中譯英評點
中譯英題目
山歌手對歌對到狂熱時會忘掉一切,誰也不服誰,把空氣都能唱燃。
翻譯要點
中譯英原文中的“把空氣都能唱燃”運用了夸張修辭格,形容對歌時的狂熱氣氛。這個夸張理解起來容易,在目標語言中表達起來卻不容易。許多參賽譯文都在夸張的表達上出現了問題,下面來具體分析。
問題一 參賽者保留原文的夸張,但英語表達有錯誤或是不自然。
例:The folk singers can forget everything in the heat of antiphonal singing. No one will ever admit defeat and even the air around them can be sung afire.
評析:譯文的整體質量不錯,語義上沒有遺漏,用詞和句子結構也體現了一定的水平,但譯文中sung afire的說法很生硬。在英語中,動詞sing和afire一般不會這么搭配,sing這個詞后面很少接afire這類表示狀態的副詞。Afire的用法和fire的用法相似,通常與set搭配,比如說set a car afire (點燃一輛汽車)。
問題二 參賽者對原文的夸張進行解釋,但解釋有誤。
例1:People, living in the mountain, are quite fanatic about singing folk songs. Immersed in the joyfulness of singing, they almost forget everything around them. Neither of them could be satisfied with the others. Passion and enthusiasm of the competition of singing folk songs makes the whole sky of mountain full of delight and noises.
例2:When mountain singers sang in antiphonary feverishly, they would forget everything, never yield to each other and liven up the atmosphere by singing.
評析:第一個譯文用makes the whole sky of mountain full of delight and noises來譯“把空氣都能唱燃”,沒有直譯“燃”這個字,而是采用了解釋的譯法,但譯文意思和原文出入較大。把譯文回譯成漢語,意思是“使得山的整個上空都充滿了喜悅和噪音”,似乎說話人很討厭山歌手的歌聲,這種態度是原文所沒有的。另外,原文的夸張表現的是山歌手唱歌時的情緒,“整個上空都充滿了喜悅和噪音”表達不出這種情緒。第二個譯文也避開了“燃”字,將“把空氣都能唱燃”譯為liven up the atmosphere,即“活躍氣氛”,意思也不對。山歌手對唱或許有活躍氣氛的目的,但到了“誰也不服誰”的地步,就不僅僅是活躍氣氛那么簡單了。這種解釋性的譯法將原文豐富的意思簡單化了,因此不可取。
除了在翻譯夸張修辭格時出現的問題外,參賽譯文在用詞和句子結構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
問題一 參賽者對原文中一些詞的理解有誤。
例1:The ethnic singers will indulge wholeheartedly in their singing, regardless of all the other world and unwilling to give in; the great passion exploding between them seems to sparkle the air.
例2:Folk song singers immersed themselves in feverish antiphonal singing so much that they eventually forgot about everything. They were convinced of no one and could even burn the air by their songs.
評析:第一個譯文用ethnic singers (少數民族歌手)來譯“山歌手”,意思顯然不對。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山歌是“形式短小、曲調爽朗質樸、節奏自由的民間歌曲,流行于南方農村或山區,多在山野勞動時歌唱”。雖然許多少數民族都有山歌,但山歌并非少數民族獨有,漢族也有山歌,因此用ethnic singers不準確。第二個譯文用were convinced來翻譯“服”,把這個字理解成了“說服”的意思,但這里的“服”顯然是“服輸,服氣”的意思,翻譯為admit defeat或give in to都可以。
問題二 參賽者的譯文存在句子結構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從句缺主語,或是兩個獨立的句子直接用逗號連接。
例1:When the mountain singers singing in antiphonal style get so crazy that forget everything, neither will give in, which almost can ignite the air.
例2:Singers sing antiphonal songs on the hill, being avid and intoxicated, they were so enthusiastic that they cannot convince each other, even the air was to be burning.
評析:在第一個譯文中,when引導的狀語從句中有一個“so … that …”結構,其中that引導的是一個結果狀語從句,應該有主語和謂語,但譯文中that后面直接是謂語forget,沒有主語,句子結構不完整。第二個譯文中的前一個分句“singers sing …”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后一個分句“they were …”也是一個完整的句子,但兩個句子直接用逗號連接,不符合語法規范,應改為分號,或寫成兩個單獨的句子。
獲獎譯文:When folk singers are singing to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sometimes their enthusiasm is such that they would put everything else behind and even kindle the air without the slightest intention of giving in. (楊龍)
評析:譯文把“山歌手”譯為folk singers,把“狂熱”譯為enthusiasm,把“服”譯為giving in,把“唱燃”譯為kindle,譯得都不錯。把“對歌”翻譯為singing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意思也沒有錯,既然后面出現了“誰也不服誰”,說明相互之間確實有競爭。不過,put everything else behind的說法有點問題,原文說的是“忘掉一切”,那就應該是everything,不應加else。當然我們也可以更加貼近字面意思來翻譯,形成如下參考譯文。
參考譯文:The folk song singers became so frantic in the antiphonal singing contest that none of them would deem others better and their frenzy would even set the air on fire. (韓子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