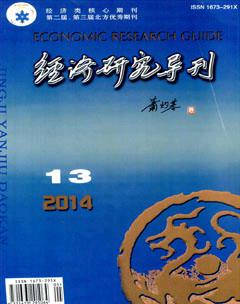“城中村”改造中的政府職能缺失分析
方亞利
摘 要:城中村作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特有現象,其內部存在著諸多問題,阻礙了中國城市化健康良性發展,而這些問題的產生與政府管理不善有很大的關聯,基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嘗試在解決城中村問題中政府職能的缺失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城中村”;政府職能;缺失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3-0233-02
在“城中村”拆遷過程中,地方政府在行使自身的職能時存在著很多問題。盡管其在表現上比較復雜,但分析起來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制度不健全,使得政府宏觀調控職能的實施無據,同時也使得政府職能的行使缺乏制度規范;二是政府濫用公益,弱化自身的市場監管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追逐自身利益;三是權力尋租,利用拆遷公權力謀求私利。
一、制度不健全,不能有效履行宏觀調控職能
(一)“城中村”拆遷制度不健全
“城中村”拆遷的制度不健全首先表現為拆遷主體角色錯位。“城中村”在土地所有權上屬于集體所有,所以“城中村”的土地必須通過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先將土地的集體所有制轉換為全民所有制,然后才能進行市場流轉。因此,無論是基于公益拆遷還是商業拆遷,對于“城中村”而言,地方政府都應該是拆遷的主體。然而,長期以來,由于拆遷制度的不健全,使得現實的拆遷呈現出了兩個發展趨向。
一是政府不履行作為拆遷主體的責任,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向國有土地所有權流轉及使用權的轉換中扮演中間人角色。地方政府在拿到土地出讓金及相關的手續費用后,將整個拆遷的責任交給土地使用者,而巨額的土地出讓金并沒有以公益的形式返還到“城中村”居民手中,或是用于“城中村”改造的社會公益中。這使得土地出讓金似乎變成了政府的中介費用,政府這種侵犯公共利益的隱形抽取,開發商必然會將其分攤到房屋價格上,必然性地導致了房價飛漲。
二是開發商從土地使用者的角色漸漸變成了土地征收的“主角”。政府角色轉化為征地中間人之后,必然會默許開發商這個“城中村”拆遷“主角”某些不公正的行為。這也是現實暴力強拆屢禁不止的原因。開發商在支付土地出讓金和相關手續費用后,由于應該作為拆遷人的政府沒有履行其拆遷人的角色,其為了達到自己的商業目的,只好扮演起拆遷的“主角”來。開發商為了達到其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使用各種方法來實現其利潤最大化。在“城中村”拆遷中,除了控制原材料的成本外,盡量壓低拆遷成本就是其實現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徑。由于政府對公共利益的攫取,使自己也身處市場中,因而就無法履行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因此市場規則下的等價交換就不復存在。大幅上漲的房價與極低的拆遷補償費之間的矛盾就成了暴力拆遷必然的邏輯原因。這種缺陷使政府職能的角色定位出現極大的危機,其很難從一個中立的角色上去制定“城中村”拆遷的相關法律、條例、政策、規劃,運用財政、稅收政策手段等對整個拆遷過程進行宏觀調控,無法對拆遷的相關市場主體進行管理和監督,無法對拆遷人與被拆遷人的利益分配進行有效調節,從而不能有效履行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市場監管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
制度不健全表現在拆遷補償上的表現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補償標準過低,不能滿足被拆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二是補償的支付主體不明確。《物權法》的第42條規定:“征收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依法足額支付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等費用,安排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費用,保障被征地農民的生活,維護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榆林市的拆遷補償費用,其與榆林市的房屋每平米均價7 000相比,幾乎不及其1/10,完全不可能達到物權法規定保障被征地農民生活的基本要求。而《土地管理法》第47條中規定:“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以及地上附著物和青苗的補償費……”而這個最重要的法律居然都沒有對拆遷的補償標準進行具體的規定。同時從規定也可以看出,二者都沒有對土地征收的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土地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的支付人做出明確的規定。所以,地方政府根本無法履行調節拆遷人與被拆遷人的利益分配,對“城中村”土地流轉進行監控的社會管理職能,根本談不上履行拆遷過程中的自然環境和生態保護及拆遷社會化服務等職能。
(二)地方政府行政權責不明確,無法有效履行政府宏觀調控職能
傳統的執政理念既強調原則性又強調靈活性。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政府一方面需要法律來約束和規制民眾,另一方面則通過所謂的靈活性擴張自己的行政權力范圍,造成了政府職能行使失范。執政靈活性與政府權責明晰是相悖的。權力的靈活性使得無法對其進行監督和問責,因而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市場監管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就無法有效地履行。在《榆林市城中村改造管理辦法(暫行)》第4條中規定:“榆林城區平房片區改造辦公室復雜中心城區范圍內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心城區城中村改造工作實行一站式辦公,市規劃、國土資源部門應當在市級城中村改造機構設立派出機構,實行雙重領導。各縣區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城中村改造工作。其確定的城中村改造機構組織實施本行政區域內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榆橫工業區、榆神工業區的城中村改造工作,由其管委會負責組織實施所在縣區人民政府應當予以配合”這個規定對城中村改造中所涉及的權屬缺乏細致的劃分,一旦出現問題就會互相推諉。這實際上是給地方政府履行宏觀調控職能、市場監管職能、社會管理職能設置了制度障礙。
在現實操作中,政府不僅沒有體現其作為社會公正裁判的角色作用,照顧好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被拆遷人的城中村居民。相反卻呈現出與開發商合謀的傾向,以共同占有公共利益。由于這些原因,政府不能有效履行其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和社會管理的職能,使社會不公正之風蔓延,阻礙“城中村”拆遷的順利進行。現實的抗拆案例中,雖有“釘子戶”漫天要價的情況,但絕大多數應該都是居民對拆遷不公的回應。
二、政府濫用公益,追求自身利益,難以履行市場監管和社會管理職能
土地出讓金一直以來都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項。在城中村拆遷過程中,由于現行法律對于公益的模糊界定,因此在更不能明確區分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行政裁判權相對于司法判定的前置,導致拆遷項目的公益性認定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同時公益拆遷和商業拆遷的土地使用權審批程序根本沒有差別,一般是在城中村土地使用權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土地使用權已經變更完畢,政府沒有經過集體所有制土地向國有的轉換程序就完全將土地使用權出讓與開發商,獨自占有土地出讓所得。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光新建南路原人民浴池2.18畝地,政府拍賣價就高達3 300萬元,每畝地價1 513.76萬元。西沙青山西路商住用地每畝拍賣價480多萬元。相反,政府給予被拆遷人的補償費用卻低得可憐。
現實的政府行為有提升政府形象,聲譽及公眾的支持率等訴求。為了這些訴求,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形象工程建設。形象工程的顯著特點就是大和快。因此在“城中村”拆遷過程中,形象工程是避免不了的。這主要是為政府官員獲得晉升機會,維護社會公正和謀求民眾福利就不是其首要考慮的問題,因而打著公益的幌子進行快速的行政強拆有其邏輯必然性。在榆林市,盡管市政府出臺《榆林市城中村改造管理辦法(暫行)》對城中村的拆遷改造進行了規制。如第14條規定:“縣區城中村改造機構組織改造區域內鄉(鎮)人民政府、村委會工作人員征求全體村民改造意愿。70%以上村民同意改造的啟動改造程序。”但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都會繞過這個程序,以公益的形式進行行政強拆,或是采取獎勵等威逼利誘的辦法實行“合法拆遷”。而且,“城中村”改造項目完成后的稅收、工商、技術監督及食品衛生管理等都是地方政府獲得財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因而也共同成為了地方政府濫用公益,履行職能錯位的源動力。
三、權力尋租,個別行政人員利用拆遷公權力謀求私利
權力尋租是行政權力擁有者利用行政法律范圍內的手段破壞各生產要素在不同領域中進行自由競爭從而獲取或維護既得利益的行為。在中國,行政權力無疑是最具壟斷性的。尤其是在現行法律不健全,缺乏權力的有效規制機制的情勢下,個別政府官員利用政府職能的錯位,進行權力尋租獲取利益。這種尋租導致了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市場監管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的弱化。
個別行政人員利用拆遷公權力進行權力尋租謀求私利的主要原因是相關信息不對稱和行政權力的壟斷性。一旦信息發布和權力操作存在暗箱,就勢必會導致個別行政人員利用手中所掌握的信息和行政權力與掌控資源的開發商合謀,共同攫取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1] 殷琳.西安市城中村房屋拆遷中的政府角色分析[J].資源與人居環境,2012,(1).
[2] 郝強.試論政府在城市房屋拆遷中的職能[J].西安社會科學,2010,(3).
[3] 楊永梅,段紅平.從行政法角度分析昆明城中村拆遷改造[J].法制與社會,2011,(5).
[4] 孫洪妮.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的政府行政行為失范問題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13.
[5] 榆林市城中村改造管理辦法(暫行)[Z].
[6] 李艷.政府介入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倫理思考——以上海市Z區為例[D].上海: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10.
[7] 孟祥林.城中村改造中的拆遷補償問題與居民安置對策調查分析[J].河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
[8] 張玲.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的政府職能錯位問題分析[J].前沿,2012,(4).[責任編輯 王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