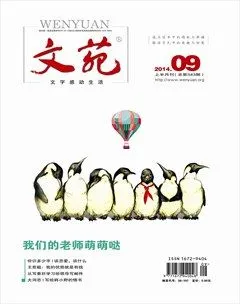那個年幼的開羅漫游者
蔻蔻梁
開羅是個見鬼的城市。太古老的文明像太多灰塵累積成殼,令這個總是炎熱的城市有種無法擦拭的陳舊感,所有的秩序都在暗中執行,對一個游客而言,開羅總有種看著你出笑話的距離感。
經歷了幾場粗暴的騙局我把自己的錢包和心防都看得很緊。晚上八點,吃過了晚飯,天氣總算涼爽一點,開羅人三三兩兩地聚在路邊,干點兒什么或者什么都不干,只是這么扎著堆,吹點風。
一個15歲左右的男孩子走近我,瘦瘦的,個子不高,穿著一件很難形容的夾克,和其他人一樣的牛仔褲:“你好,你是游客嗎?”不錯的英語,但我沒有力氣再對付一個小騙子。“哎,你好,我在跟你打招呼。你為什么不理我?”小孩有點兒不依不饒。
“你要干什么?”我盯著他問。他攤了攤手:“沒什么,我只是想練練英語,到處逛逛。你要不要我帶你到處逛逛?我不是導游,我不要你的錢,只想練練英語。”
這個皮膚黝黑的小孩有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眼睛里有令人信服的誠懇。一個孩子,又能把我怎么樣?我開始放松警惕,連自己都能感覺到自己聳起的肩頭垂了下來:“我來了好幾天,該看的都看過了。你能帶我看什么呢?”我問。
“啊,小姐,開羅很大,我帶你去看其他任何游客都不會去看的東西。”好吧,我承認這個孩子點中了我的死穴。路燈亮起來,我走在他略后面一點,跟他鉆進了開羅老城區里的小巷。每路過一堆人的時候都會有人打量我們這對奇怪的組合。一路上小孩跟很多人打招呼,從四五十歲的大人到與他同齡的小孩。
“你怎么認識那么多人?”我問他。
“在開羅,人們都認識很多人。你住在一個地方,附近一公里住的人你都會認識。”小孩子帶著一種毫不夸張的語氣說著這些話。
“你在跟他們說什么?”
“他們問你是不是我女朋友。”小孩嘿嘿地笑起來。埃及男人的貧嘴,好色,愛搭訕,這些日子以來我見識過不少,只是不曾想過這個其實也是童子功。
孩子喋喋不休地說話,他說平時沒事做就在街上亂走,“我覺得這些角落里的地方很神奇,我喜歡在城市里漫游,有些門只是一扇門,但是你推開它,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事物”。孩子說他從9歲開始滿街走,對開羅比對自己的巴掌都熟悉,“哪怕再小的路,我也走過至少一遍。”
這點,我相信,因為我發現自己已經很久不走在大路上了,開羅的夜晚很黯淡,路上本就沒有太多的霓虹燈,在這些小路上,即便偶爾有亮著燈的店鋪,也是一副電力不足的樣子,光線昏黃。開羅有很多貓,無聲無息地游蕩在街角。
孩子帶我來到一棟貌不驚人的老樓面前,推開一扇木門,徑直走了進去。我探頭看了一下里面的黑暗,有點兒躊躇。男孩在里面喊:“上來呀!上五樓來,加油。”剛變聲的嗓子聽起來有點緊緊的感覺。
五樓會有什么?更多的房間?我踏上半朽的木樓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男孩拉著我的手穿過五樓的走廊,盡頭是另外一扇小門,他推開門,日光燈的強烈光線一下子涌了出來——竟然是一個大的集市。它像一個隱匿在時空里的存在,一點都不真實地呈現在一個從外面看起來根本不存在的空間里。
這是樓與樓之間違建的一個平臺,居民自發形成了一個集市,補衣服的,賣小零碎的,賣冷飲的,賣二手舊物的……所有物品的價格都只是市場上的一半左右。人們各自架起一支日光燈,攤開一塊塑料布,認真而嚴肅地做著他們的生意。男孩得意地看著瞠目結舌的我,“他們會營業到次日凌晨兩點。”他說。這個奇妙的集市一點也不喧鬧,人們都只是在安靜地做自己手上的活計,或者沉默地背著手在過道里穿行。我一直不知道,記憶里的這種安靜到底是真實的,還是我當時因為受驚過度,全部注意力都在眼睛上,而讓耳朵失去了知覺。
我不得不相信這個年幼的城市漫游者。在余下的三天里,他陪著我去看“壞掉了的金字塔”,在“有四個老婆的人家里喝茶”,看“專門給妓女剪頭發的理發鋪”、“開羅最漂亮的一盆花”。我負責買他吃飯的單,每到吃飯的時候男孩都很懂事地只點最便宜的一點點主食,僅在我的再三勸說之下才會點一瓶最便宜的當地礦泉水,而大多時候他吃完飯只是到外面去喝自來水。告別的時候我總是想塞他一點點車錢,而他一定回絕說“我喜歡走路”。然后就穿著他破舊的小球鞋歡快地走開。
這是個快樂的男孩,唯一有點讓他悵惘的是他夢想有一部自己的電腦,“二手的就好。所以我要練好英語,找好工作,工作以后我會攢錢買的”。分手的時候我硬塞了他100美金,“算我支持你買電腦的股份吧。”我對他說。眼淚嘩地從他眼睛里涌出來。他把錢好好地疊起來,放在貼身的小口袋里,用手背不停地擦著眼淚。
準備離開開羅的時候我去附近的車站買票,意外地又看到這個男孩。他站在報亭邊上沖一個女孩說:“我不是導游,我只是想練練英語……”
不知道。我情愿相信一切都是真誠的。
摘自中國華僑出版社《如果你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