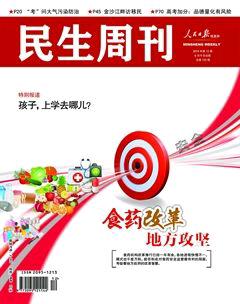三方博弈下的“移民后扶”
陳沙沙 王麗
“大家都選擇城鎮化安置,當了大半輩子農民,想進城做些生意。”看著新居道路旁閑置的土地,王秀萍和鄰居們開始栽種一些應季蔬菜。她們用這樣的方式紀念遠去的耕種生活,也以此貼補家用。
曾經,王秋萍是云南省綏江縣的一位普通農婦,因向家壩水電站建設,房子和土地被淹沒。2012年開始,她成為新縣城鳳凰社區的一名居民。
在云南省昭通市,綏江一直被鄰縣羨慕。這份心理,不單因為綏江移民工作的創新模式贏得稱贊,更多的原因來自復建的現代化新縣城。對于綏江脫胎換骨般的變化,當地有移民用“千年夢想,一朝完成”來形容。
向家壩水電站是目前我國第三大水電站,與居第一的三峽、居第二的溪洛渡同為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開發。
因向家壩水庫蓄水,綏江縣整座縣城、3個鄉鎮集鎮需要遷建,原地后靠上山,涉及移民6萬人。
5月上旬,《民生周刊》走入綏江。寬敞的道路,大片的居民樓整齊排列,一派嶄新氣象,絲毫不見昔日國家級貧困縣的模樣。
然而,茶館多、棋牌室多、廣場舞多的愜意氣氛,似乎也在警示著這座“早產”的縣城。像過往的任何一次大規模水庫移民一樣,“搬遷”只意味著移民第一步的邁出,而后期穩定、發展的挑戰才剛剛來臨。
不對等的博弈
10余年前,向家壩水電站將要開工建設的消息,成為一針強心劑注入綏江。三峽集團“建好一座電站、帶動一方經濟、改善一片環境、造福一方移民”的宣傳口號,使普通移民、地方政府開始展望電站帶來的改變。
“它是國家的能源戰略工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綏江縣副縣長周開江如此形容向家壩電站對于這座山區農業縣的意義。綏江地處高山溝壑之中,發展困難,但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成為水電站建設的先決條件。
“綏江老縣城有300多年歷史,但我們的現狀是什么?”周開江自問。
為了把握這次機遇,早在2004年,向家壩電站正式開工前兩年,綏江便貸款籌資1500萬元,從美國請來兩家規劃設計公司為新縣城進行概念性規劃和總體規劃。
藍圖中的新縣城被定位為“以人為本,以水為主,依山建城,山水結合,集旅游、休閑、度假為一體的人居環境最佳的湖濱生態園林城市”。
“如果沒有當初的規劃,移民搬遷堅持不到最后。”周開江認為,藍圖中的新縣城早已成為綏江人的目標,并從中汲取著力量。
向家壩水電站于2002年獲準立項,2006年可行性研究報告獲批并正式開工,三峽集團與云南省政府簽訂總包協議,2007年移民工作正式啟動。
但移民工作推進并不順利。因對安置政策不滿,2011年3月25日,綏江兩千余移民走上街頭,圍堵縣城長達5天4夜,引起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視。
綏江移民干部談到,如果不是在2011年初經省政府特批,把新縣城遷建項目統一委托給云南省建工集團建設,移民搬遷安置肯定無法在2012年10月下閘蓄水前完成。
《民生周刊》記者發現,移民搬遷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與三峽集團之間圍繞移民經費的“討價還價”,這場博弈貫穿移民搬遷安置始終。
按照《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國務院471號令),移民搬遷安置施行“政府領導、分機負責、縣為基礎、項目法人參與”的管理體制。但簽訂的總包協議并未產生足夠約束力,涉及經濟補償的安置方式、補償細則長期難以定案。
多位受訪的移民干部認為,作為處級行政級別的縣政府無法與三峽集團直接對話,來自移民的訴求很難由縣鄉干部直接傳遞,一般要經由省政府出面協調。而且,但凡涉及需要出資的搬遷實施細則,縣政府都無權制定。
對此,三峽集團總經理助理兼移民局黨委書記梁福林也稱這是“一場不對等的博弈”。但他認為,身為業主的三峽集團是弱勢一方。“移民、地方政府的要求越來越高,地方可以拖時間,我們卻拖不起。”
云南省移民開發局政策法規處處長秦躍武談到,有地方政府存在把歷史遺留問題和未來發展問題通過水電開發一次性解決的心態。
許多復建的基礎設施、道路橋梁標準都高于原標準。比如在綏江,一條主要的四級公路建成為二級,當地云川金沙江大橋、羅漢坪水庫等,都是以前沒有的新項目。
這種局面下,移民所需經費巨額超標。據媒體報道,按2005年、2006年分別審定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向家壩、溪洛渡兩站移民經費共約230億元,后經“博弈”,三峽集團不斷追加經費,2011年又增加200億元,接近翻番。
《民生周刊》記者從三峽集團得到的最新數字顯示,目前兩站移民經費已刷新至600億元。
“綏江的新縣城在全省都是數一數二的。”三峽集團移民局副局長姚英平談到,結合縣城集鎮搬遷復建的各類教育、醫療機構等,使公益性事業硬件發展水平提前近10年實現了地方制定的2020年發展目標,達到全省先進水平。
除了為移民安置“買單”外,三峽集團在金沙江庫區推行“愛心行動”,截至今年4月,已投入2661余萬元,用于援建庫區希望小學、大病救助等公益事業;2011年開始,與全國婦聯合作,出資3000萬設立“水庫移民婦女發展扶持基金”。
提前50年城鎮化
綏江全縣人口17萬,此次向家壩水庫移民6萬,其中約一半為農村移民。以老縣城為中心的沿江精華地帶基本處在淹沒區內,水庫蓄水后,為數不多的臨江良田被淹。所以,多數農村移民無地可分,只能選擇“城鎮化安置”、“逐年補償安置”等無土安置方式。
綏江縣移民開發局副局長李文利介紹,在農業生產安置人口中,有97.04%的人口為無土安置,0.27%的人口為少量有土安置。
在大量農村移民涌入城鎮的同時,全縣城鎮化率由不到20%升為40%,原來1.7平方公里的老縣城,變為5平方公里的新城。
“可以說,綏江城鎮化率提前50年實現,但是新縣城根本沒有做好準備。大量失地農民怎么辦?”周開江說,城鎮化急速提高之后的庫區正面臨產業支撐不足的挑戰,如何解決就業,成為地方主政者最大的隱憂。
“相當多的門面房難以發揮預期效益。”李文利說,城鎮化安置人口在政策上給予其在新城集鎮配置了人均7平方米的門面房(按建筑成本購買),但綏江目前的門面房規劃和建設已經供大于求。
綏江移民權益維護工作組組長王惠銀告訴《民生周刊》記者,根據他的調查,由于消費群體少,經營模式同質化高,已有很多門面房關門歇業。
而對于綏江產業支柱缺失,無法吸納就業的現狀,綏江移民認為與向家壩電站興建有關。
2003年2月,云南省政府下達了“向家壩水電站封庫令”,此舉意味著“停建”,庫區不再允許人口流入,不再允許新建房屋、產業,農民不再允許栽種多年生作物等。
“從此,綏江就很少得到上級的財政撥款。”綏江縣發改委黨組副書記茍邦正談到,在長達近10年的“封庫令”期間,綏江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縮水,社會消費被嚴重抑制。
他進一步說,因為水庫淹沒了大量良田,導致綏江目前一產不強,二產幾乎空白。唯一一家煤礦,今年也在云南省煤礦產業全行業整頓中被關停。
“我們不能再給老百姓一個沒有發展的新縣城。”綏江縣副縣長楊杰認為,被定格的10年,限制了經濟產業的發展,也促使綏江政府、普通百姓有著強烈的趕超發展意愿。
但是,他與多數地方干部認為,按照“三原”補償原則,制約了新縣城的復建,并使縣政府背負了沉重債務。
“早已超出‘三原’原則的標準。”梁福林告訴《民生周刊》記者,《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國務院471號令)規定了“三原”補償原則(即原規模、原標準或者恢復原功能)。三峽集團提供的數據表明,向家壩的移民政策,已是超國家標準的待遇。
三峽集團向家壩工程移民項目部副主任程劍平曾對媒體說,綏江“3·25”事件后的半年多,出臺一二十個新政策,如對移民建房困難戶予以兜底,確定人均25平方米磚混結構的基本安置標準。僅此一項,向家壩、溪洛渡庫區就增加近3億元投資。
“移民工程被業內稱為‘無底洞’”,看到三峽在補償上開的口子比較大,很多業內發電集團人士還埋怨我們補償過高‘帶壞了頭’。”姚英平說。
據綏江縣政府知情人士透露,去年年底,三峽集團已將114億元的移民經費劃給綏江。但是,綏江已使用的移民搬遷安置、新城建設等經費共達170余億元。
這組數字得到三峽集團、云南省移民開發局工作人員的證實。
三峽集團人士分析,綏江巨大的移民經費差額,主要來自新縣城施工建設中出現了不少超規模、超規劃的項目。
“作為央企,三峽肯定要肩負社會責任,但必須要掌握一個度。”梁福林表示,三峽集團會按照國家發改委的相關規定與當地進行決算。
秦躍武認為,綏江縣所提出的資金缺口,原則上三峽集團不能全部“買單”,超出遷建規劃的部分需要縣財政自行配套資金。
后扶的困惑
“如果數十億負債靠縣財政背負,幾十年也還不完。”多位受訪的綏江干部分析,綏江是典型的山區農業縣,2014年全縣生產總值為18.36億余元,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2.68億元,縣域經濟自身缺乏自我積累、循環發展能力。
“前兩年縣財政收入可觀,主要依賴移民安置房建設征收的建筑安裝營業稅等。但隨著施工期的結束,往后的財政收入會明顯減少。”
據了解,綏江縣已加快了產業發展步伐,但當地交通不便,資源有限等客觀原因,導致招商引資推進緩慢。目前,庫區主政者期盼著在土地、電力等方面獲得政策優惠,以利招商引資,以產業促就業。
《民生周刊》記者在綏江發現,更多地方干部和移民對未來的希望,仍然傾注到電站和業主身上。比如,王惠銀就曾建議三峽集團在綏江打造10萬畝竹園,打造竹產業鏈。
“處理好移民城鎮化安置后的長遠生計問題是長治久安的關鍵,需要產業發展。但是,很多地方要求的產業項目都超出了三峽的能力范圍。”梁福林說,三峽集團曾經計劃在杭州舉辦招商大會,為浙江的民營資本和庫區產業項目牽線搭橋。
同時,梁福林強調,根據2006年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完善大中型水庫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見》,地方各級政府是移民扶持工作的責任主體、工作主體和實施主體。
“我們肯定會幫助地方,可是‘等、靠、要’的思想是要不得的。”
梁福林算了一筆賬,向家壩、溪洛渡兩電站正常發電后,每年的稅費(包括增值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庫區基金、水資源費等,不含所得稅)總額近70億元。若攤到每個移民身上,人均稅費近4萬元。
在他看來,庫區經濟發展和移民安穩致富有著堅實的物質基礎。“問題是,巨額稅費收入有多少被用于庫區經濟發展,用于改善移民生活?往往是層層收繳、‘一平二調’后所剩無幾。”
他進一步解讀到,在移民搬遷安置、后扶發展過程中,一旦出現問題,很少有人從現行稅收及分配制度上找問題,而是眼睛盯著企業,讓企業掏錢。庫區城鎮化帶來的產業發展問題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而是需要進行利益調整。
“企業掏錢猶如送幾個雞蛋,但下蛋的母雞并未留在庫區,治標治本,一目了然。”梁福林比喻道。
此外,姚英平建議,即使下達了封庫令,也應保留國家財政對移民縣的各項財政支持,可以與移民安置資金拼盤使用。并且,電站建設產生的各種稅收應該向移民庫區和移民安置區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