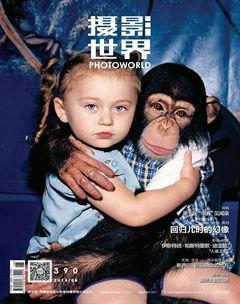聚焦第十屆“華賽”爭論點
趙姝婷



故事性之爭
在評選戰爭災難類新聞組照前三名的過程中,評委會成員爆發了第一次熱烈的爭論。入圍前三名的作品有《臺風海燕》、反映孟加拉工廠大樓倒塌的《“奴隸制”的代價》以及在最近一屆荷賽中獲得突發類新聞組照金獎的《大馬士革之戰》。作為進入到最后環節的組照作品,從圖片的質量、故事的完整程度來看,都令人難以挑剔。但評委吳才興卻發起了這樣的質疑:“如果把目光放在拍攝過程上,《大馬士革之戰》這一組照片只是一個短時間的事件,攝影師的整個拍攝過程也許只有幾分鐘時間。但諸如《臺風海燕》這樣的組照,顯然需要攝影師更長時間地跟進,有一個長期的拍攝計劃,如此才能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就講故事來說,我認為《臺風海燕》是更好的作品。”
他拋出了一個疑問,即人們如何看待組照的故事性,是否更完整的故事呈現優于那些故事的“剖面”呢?評委王身敦在討論中給出了自己的見解:“《大馬士革之戰》的確是一個相對‘短小的故事,但是想要把這樣的故事講好,卻考驗著攝影師的技巧和努力。我們看到的也許只是很簡短的一瞬,但拍好這一瞬的背后,是一個優秀攝影師長年累月的積累。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不應因為它是一個‘短小的故事而影響對攝影師及作品的評判。”
題材與影像之爭
新聞攝影比賽,到底評的是新聞,還是攝影?到底是題材令人拍案叫絕的影像更好,還是高質量高水準的影像更好?
這在業界恐怕已經是老生常談了。雖然人們始終討論不出個結論,但有句話說得好,“真理越辯越明”。在年復一年的討論中,人們對于什么是好的影像的理解才會愈發深刻。“這個獎項到底旨在視覺傳播,還是傳播視覺?”在本屆華賽的評選過程中,評委們也多次圍繞著這個核心矛盾點進行討論。
獲得本屆華賽日常生活類新聞組照金獎的作品是《背叛傳統的伊朗年輕人》,在這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一些伊朗年輕人隱秘的反傳統的生活側面。雖然這組照片的畫面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精良,但卻以新穎的視角和難得一見的影像俘獲了許多評委的心。但也有評委認為,如果不嚴格把控作品的影像質量,會對未來參賽的攝影者產生傾向性的誤導。在這一組別的評選過程中,評委的意見分化十分明顯。
力挺這組照片的荷蘭評委文森特·門采爾這樣闡釋自己的觀點:“一個攝影師在拍照的過程中需要依靠天時、地利、人和,但并不是說沒有這些條件就可以為拍不出好照片找理由。好照片最重要的品質是凝結一個瞬間,以向觀者陳述故事和觀點。在某些情況下,尤其是攝影環境特別艱苦和惡劣的條件下,即使照片的質量不盡如人意,也不應該成為其被發表和傳播的阻礙。當照片紀錄了一個重要的故事,它是值得被肯定的,有攝影師見證已經足夠。”
當然,題材出新并不是獲獎的保證。在本屆自然與環境類新聞獎項的評選中,《亞馬遜森林砍伐》就憑借著俯瞰的高空拍攝視角和令人震撼的視覺沖擊畫面,獲得了比《一座村莊保護一頭犀牛》和《基里巴斯——60年后消失的國度》更多的選票——雖然亞馬遜森林生態環境的破壞從幾十年前開始就早已是熱門話題,但大多數評委們似乎不太介意。然而新西蘭評委朱莉婭·德金對《基里巴斯》未能奪金的結果還是略感到遺憾:“基里巴斯是一個即將消失的國度,這是一個很重大的題材,也許目前很難拍到有沖擊力的照片,攝影師所能做的只能是講述一個漫長的故事。不過等這個國家消失了,這些照片就會非常有歷史意義。”
評委會主席黃文對于這樣的爭論,給出了如下看法:“盡管我們大多會說題材和影像二者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但我認為一個新聞攝影比賽首先是攝影比賽,照片的影像價值是我決定是否繼續觀看和閱讀的前提。這也導致了無論是華賽還是荷賽在首輪淘汰式評選時,不向中外評委提供圖片說明(華賽其實比荷賽還是稍微寬松一些,從評選一開始就在每幅照片上提供了標題),以確保評委完全從影像質量出發對參賽作品進行判斷。在完成初選淘汰,‘殺掉大多數照片之后,才開始從留下來的照片中選擇新聞價值更高的作品。這種評選機制可以較好保證最終獲獎作品在影像上的質量。當然,由于圖片說明中相關故事的介入,評委在后面的評選中多少會受到影響,并且改變對照片價值的判斷。有些時候,甚至是對照片評價的逆轉,這便是新聞信息的魅力所在。”
無論你對本屆“華賽”評選結果的感受如何,是否認同評委們的意見和作品排名,都不妨礙你仔細欣賞和品味這些評選出來的影像。如何看待照片,很大一部分可能要歸于觀者的主觀感受,但在不同觀點的碰撞中,總能獲得更多角度的思考和更開闊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