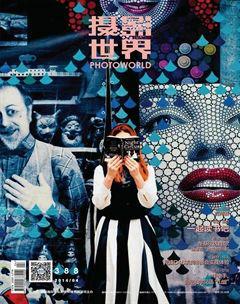全會華:艱難的抉擇
傅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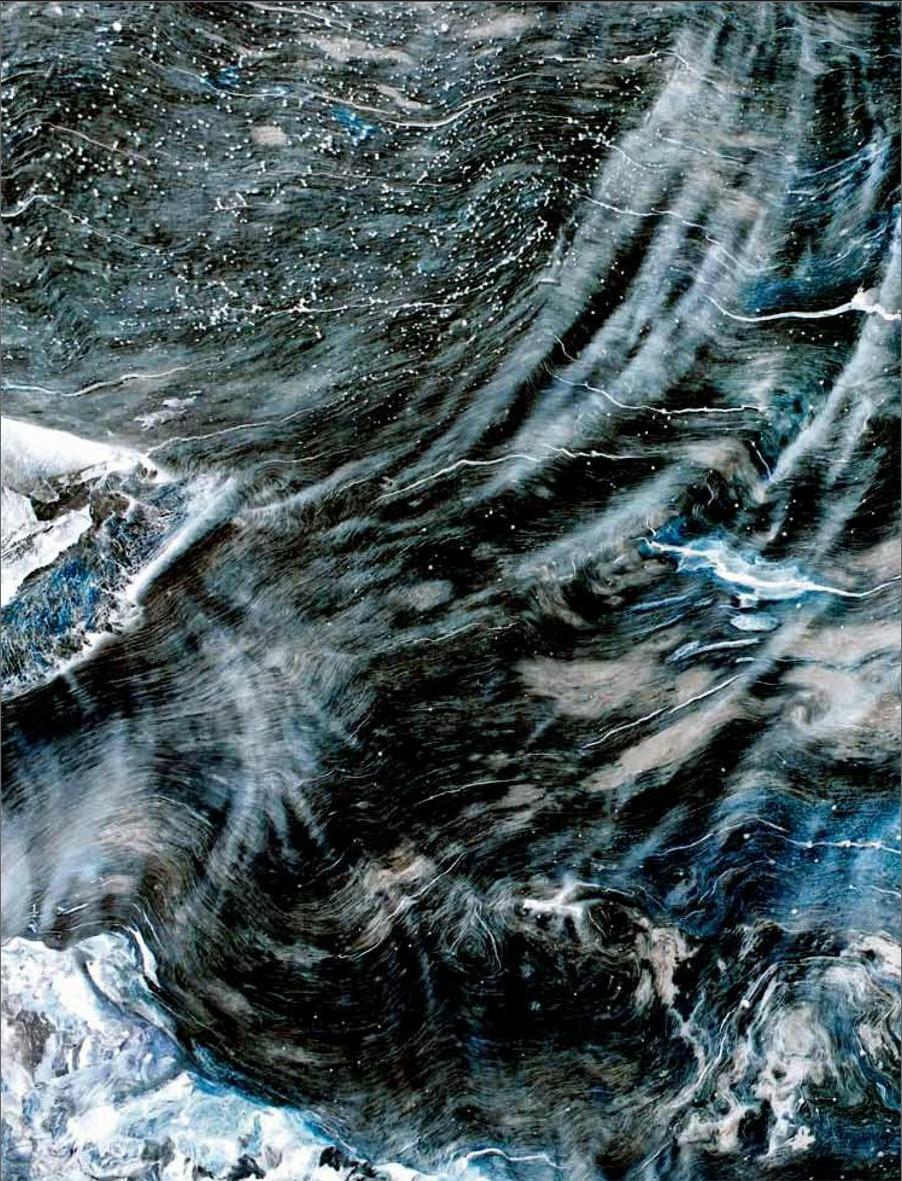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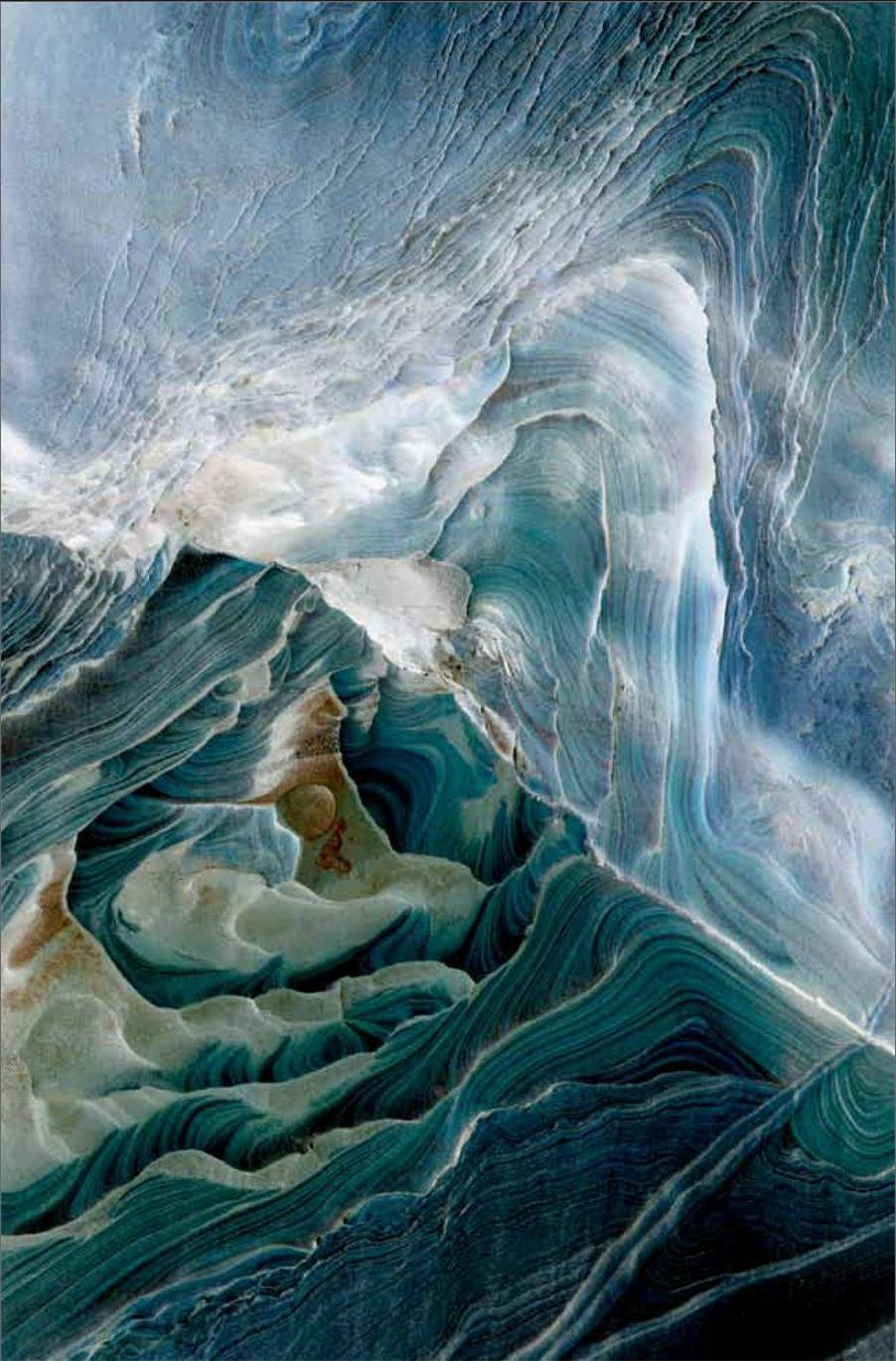

初見全會華,是在他新成立的一家公司辦公室,位于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的一棟大樓內。原本我想與他在其畫廊碰面,也就是臺灣攝影人都熟知的攝影畫廊—臺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Taiwan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Center,簡稱TIVAC),位于松山區八德路三段。不過,他更換見面地址恰好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臺灣攝影市場的形態正發生轉變。
2014年農歷春節前的最后一個星期,臺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在做完最后一個活動之后,對外宣布暫時停止營運,理由是進行內部整頓,關于何時重新開業卻只說另行告知。畫廊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重新開業?其實,作為老板的全會華也還在深深地思考之中。他陷入了發展的困境:究竟是要繼續支付高昂的管銷成本來維持畫廊的運營?還是將這些資金用作其他更見效的用途?按照全會華的預想,畫廊將面臨兩條路:一是繼續營業,但需做得更加深入,比如關注臺灣本土攝影師的培養;二是關閉畫廊,專攻攝影博覽會。
獨立辦展,勢如破竹
沒錯,與全會華碰面的地點,即是他的會展公司Taiwan Art Connection(直譯為“臺灣藝術聯系會”)辦公室。2013年9月,他的會展公司啟動了第一屆“臺北藝術攝影博覽會”(2013 TAIPEI ART PHOTO),舉辦地點位于臺灣的臺北花博公園爭艷館(圓山公園園區),此次博覽會共有10多個國家的50多位攝影師、畫廊及拍賣公司參與其中。其實,這并不是全會華第一次組織攝影博覽會,早在2011年,他就和臺灣“1839當代藝廊”的創立者邱奕堅一起,聯合舉辦了臺灣攝影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攝影畫廊博覽會:臺灣攝影藝術博覽會(Taiwan Photo)。
2013年,全會華從中獨立出來,做了“臺北藝術攝影博覽會”,主動將臺灣攝影博覽會的市場做了詳細分析。雖然跟2011年的“臺灣攝影藝術博覽會”性質類似,均以銷售作品為主要目的,但全會華的博覽會有其獨特性,即更加注重展覽的學術性。除了在博覽會期間舉辦一系列學術交流和講座外,他要求參展的每家畫廊在展示空間內,只展出一位藝術家的作品。對此,他的理由是:“這樣有利于收藏家更好地了解藝術家,畫廊也能夠對藝術家進行有效地推廣 。”
近兩三年,全會華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組織攝影博覽會上。去年,博覽會做得特別成功,超出了他的意料。回憶起來,他端起熱茶抿了一小口,說道:“博覽會那幾天,臺北趕上下雨,我擔心去的觀眾會少。但意外的是,早上10點,展館外卻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在臺灣看攝影展要排隊還是很少見的。在我印象中,以前只有日本當代攝影師蜷川實花和美國時尚攝影師David Lachapelle來臺灣辦展時,才有排隊的熱鬧場面。這一點增加了我的信心。后來,我特地在網上看了觀眾的反饋,絕大多數也都是正面的,這更增強了我繼續舉辦博覽會的信心和動力。”
長期經營畫廊,組織、參加博覽會讓全會華的業界經驗日漸豐富,他漸漸意識到:“攝影博覽會的發展已漸成趨勢,并不斷吞噬著畫廊市場,這種局面可能會影響到臺灣攝影畫廊的生存。”
“現在,臺灣的文化環境已經發生了改變,到處都是博覽會,每兩個月就有一個博覽會,這樣算下來,臺灣藝術方面的博覽會一年就有五六個,但參加的也就是那幾個畫廊。畫廊本來是一級市場,沒想到二級市場反而喧賓奪主:一級市場漸被壓縮,一、二級市場漸趨融合;按照這樣的趨勢,畫廊必將面臨兩種命運:一是畫廊關閉,省掉租金和管銷費用;二是縮小畫廊空間,成為形式上的存在,將主要精力放在參加博覽會上。”
這正是全會華所面臨的困局,眼下他也不得不做出艱難抉擇。當然,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困境,也是整個臺灣攝影環境發展的困境:一級市場(畫廊)受到二級市場(博覽會)的嚴重擠壓和取代,正急速萎縮。
情系畫廊,抉擇艱難
若對畫廊僅存淡淡之情,全會華的抉擇就不會如此掙扎。
關掉畫廊能大大減輕全會華的經濟壓力,但也會剝奪一個藝術家真正的生存空間。這也是他考慮是否放棄畫廊的重要原因。
1995年,全會華在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美術教室擔任攝影教師,不久,便有喜歡攝影的建筑商朋友找他一起做畫廊,建筑商做大股東出資50%,全會華和鐘永和等幾個朋友出資成為小股東。就這樣,臺灣第一個真正意義上以攝影展覽和銷售為目的的畫廊“臺北攝影藝廊”成立了,全會華擔任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縮寫CEO,臺灣稱執行長)。畫廊的第一個展覽,便是日本攝影師今道子的,當時27幅作品全部賣光。接下來,畫廊還做了安塞爾·亞當斯、愛德華·韋斯頓等名家的原作展,且銷售得都不錯。畫廊剛一開張,勢頭強勁,當然這與全會華有著莫大的關系。
幾乎整個1970年代,全會華都在日本度過。八九年的赴日生活中,他幾乎到處打工,并最終畢業于東京工藝大學(Tokyo Polytechnic University)短期大學部攝影專業。在那段日子,他經常前往東京國際畫廊(Photo Gallery International,簡稱PGI),因此,多年的關系積淀,便成了他日后在臺灣做畫廊的特殊資源。幾乎大部分攝影大師的原作展,都是全會華與東京國際畫廊合作而達成的。
東京國際畫廊是日本第一家攝影畫廊,全會華對此畫廊的背景很清楚,“畫廊的老板原本是賣醫療器材的,由于他經常去美國,而且公司就在經營亞當斯作品的畫廊旁邊,他覺得生意不錯,聯絡好后便回日本開了畫廊,這一開已有三十多年。”
但是,全會華并不把畫廊業績不錯歸功于自己,他談的更多的是臺灣公眾,以及公眾攝影教育的萌芽。他說:“1980年代,從國外留學回來的臺灣人大概是最多的。其中,學攝影的人不少,就像我們這一批人,對攝影非常熱衷。那個時代,對攝影的報道在臺灣慢慢多起來,國外留學回來的人,也認識到了攝影是怎么回事。我們從1993年開始舉辦臺北攝影節,也做了很多與攝影相關的社會活動,再加上藝廊的開業,使得攝影事業在臺灣的發展越來越蓬勃。”endprint
但好景不長,由于臺北攝影藝廊的大股東遇到房地產下跌,致使畫廊在開業2年后面臨倒閉。1999年,全會華拿出自己所有的財產,獨自接手畫廊,并改名為臺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接手后,全會華調整了畫廊的發展方向,開始展出臺灣老前輩攝影師的作品,如“攝影三劍客(鄧南光、張才、李鳴雕)”的作品。展覽過后,臺灣的三大美術館均陸續開始收藏此類作品。
當然,憑借與日本畫廊的友好關系,臺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也展出過日本攝影大師荒木經惟的作品,展覽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趣事,“我的畫廊在展荒木經惟的作品時,警察一個月要過來七八次,主要是有民眾向警局報告,說怎么可以展這些。警局如果接到投訴,是一定要來看看的,但我們沒有在戶外展出,也不違社會風化,因此并無問題。”這是發生在2012年的事情,也從側面反映了臺灣民眾對情色攝影作品的不同認識。
臺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的存在已有15年,全會華曾押上所有家當,兢兢業業地付出十幾年的心血,而眼下攝影畫廊在臺灣的發展正舉步維艱。從商人的角度來說,是否關掉畫廊,決定其實很容易做;但從情感方面來說,這的確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生于攝影,忠于攝影
一定程度來講,作為一個馬來西亞人,全會華對臺灣攝影所投入的熱情和責任感,并不少于臺灣人。1953年,全會華出生于馬來西亞北部,他的父親很小就從海南到新加坡,再北上到馬來西亞,經營餐廳事業且發展得不錯。
一個至今仍拿著馬來西亞護照的人,在臺灣這么執著地做攝影,是出于什么樣的動力?“因為喜歡,而且臺灣人對我很不錯,給了很多支持,因此我要用行動來回饋這個社會。之前在博覽會上,看到攝影只被作為其他藝術形態的陪襯,因此我想自己做來看看,希望能夠改變這種狀況。”
的確,他對攝影的熱情,遠不止專門去尋找一些境內外的攝影畫廊參加博覽會這么簡單,“我還想做攝影圖書館,因為攝影書跟文字書放在一起,其力量往往會被分散,我想把攝影圖書館獨立出來。而且,90%的攝影書都是攝影師買走的,他們需要研究彼此在做什么,但并不是所有的攝影書都可以買得到,因此,成立圖書館的需求就更加強烈。”
其實,在去年的攝影博覽會上,全會華就已經開始實踐這個目標了。在博覽會上,他特地開放了一個攝影書區域,將從各地搜羅來的攝影書陳列在一起,像圖書館那樣展示,不僅教育公眾,還為熱愛攝影的人們提供了思考攝影多種可能性的機會。
全會華對攝影的喜愛,早在初中參加攝影社團時就開始了。這可能與他的父親當初從海南島下南洋一樣。生在海島的人,對外面世界的渴望格外強烈,再加上他對家里的事業不感興趣,所以高三時,他早上參加完畢業典禮,下午便啟程從馬來西亞去了日本,那是1972年,他19歲。到達日本后,全會華再一次表現出了他的叛逆,“父母希望我做餐飲,讓我報與旅游觀光有關的專業,但我自己偷偷報了東京工藝大學與攝影相關的專業”。
在日本呆了近十年后,全會華“落地”臺灣的機會很偶然,僅僅是出于他大學同學的推薦。其實他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到了臺灣,但從此便沒離開過,除了中途有一年,他背起背包在歐洲打工旅行。這一年的歐洲旅行,使全會華堅定這一輩子都要做攝影事業,正是在這一次“找自己”的旅行中,他想通了很多東西,也意識到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那時在法國,剛在日式餐廳辭完職,我決定繼續往前走,離開的前幾天我又回到那家餐廳前的噴水池邊。冬天天氣很冷,但當時我卻感覺到一股熱氣,從腳底慢慢上升,最后‘嘣的一下,從我的頭頂出去了。此后,我看東西就比較明白,好像整個人一下子成長了,頓悟之后,我發現自己是這樣一個人—為攝影而生。”
回到臺灣后,全會華就一直做著跟攝影有關的事情:開畫 廊,舉辦博覽會,在美術館教攝影,跟攝影界的朋友一起籌備臺灣的攝影博物館,等等。在攝影的路上,他一直在嘗試新的東西,尋找新的可能性。
今年5月中旬,全會華將在臺北華山文化創意園區舉辦臺灣人體攝影展,涉及的攝影師領域很廣,從年輕攝影師到老一輩以及資歷更深的攝影師們。“展覽將會從林絲緞開始,她是臺灣第一個人體攝影模特兒。從她開始,來展現臺灣人體攝影的發展過程。”說到目前的愿望,全會華說:“這次的人體攝影展,是從身體到內心的感覺,是一種觀念性的東西,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拿到大陸去展覽”。
但是,臺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到底關閉還是運營,全會華仍然沒有下定決心,但無論結果如何,都無法降低他對攝影的熱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