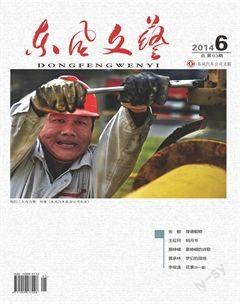去來兮,故鄉鳥語(外一篇)
傅祥友
遙遠的天邊兒,飄來,飄來故鄉的鳥語;
幽幽的故鄉鳥語,帶著泥土的芬芳,春雨秋風一樣,潛入了城中人,我的夢鄉……
時時地,夢歸故鄉——
悠悠碧空下,大朵的白云嫻靜地臥著,入睡如夢了似的;傾聽著童話韻味的鳥語,品嗅著不知名的花香,小小的我度過了雖貧窮卻環保,且歡樂的七彩童年。
如果沒有空中、樹梢、林間、房前、屋后涂鴉著的鳥兒,沒有鳥語在夜空自由的吟唱,我想,我的營養不良的童年又該是另一種的饑餓,另一種呆板的黯淡色調了。
在鳥兒們撲撲楞楞的嬉戲里,唧唧喳喳的晨問里,我們會一骨碌兒下床,喝碗紅薯稀飯,背起老棉布縫制的書包,左鄰右舍吆喝一聲,三五成群雀躍著,嘰喳著,唱著“學習雷鋒好榜樣”,向著三幾里外的學校蹦蹦跶跶而去。
那時,只要是鄉下的孩子,幾乎都是在鳥兒清越的歌唱聲中成長著;對大自然的認識,似乎也是從鳥兒身上開始的。
……對故鄉鳥的別樣的依戀中,我記憶著,也享受著許多的有關鳥的詩詞和成語里的精神食糧。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微微的南來的風中,故鄉的美麗是在此時生動起來,也是在此時進入世外桃源意境的。這是一幅怎樣的清亮的水墨田園!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飄閃的綠絲絳,高遠的藍天,悠然的白云朵,離不開鳥的翩翩舞蹈。大自然的舞臺上,總有著精靈一樣的舞蹈家表演著!
“沉魚落雁”、“燕雀處堂”、“雪泥鴻爪”、“鸚鵡學舌”、“鳶飛魚躍”等等,這些或飛翔著,或小憩著的鳥,在與人的和諧相處中,以彼此特別的情誼,演繹著一個又一個的傳奇故事,孵生著一個又一個的奇聞掌故,譜寫著一曲又一曲的生態文化。
是啊,故鄉的鳥兒,都是大自然時裝的標致模特,勤勉的環保使者。每一種鳥兒,都有著非凡的霓裳羽衣,都扮著繽紛的盛妝;即便在不同的季節,都有著不同的鳥兒鬧枝頭;空中飛翔著的,是不同鳥兒的快樂!
是啊,故鄉的鳥語,都是大自然的天籟之音,帶著花香的清澈的歌聲。她們的每一聲啼鳴,都帶著謎語一樣的玄妙,都長了翅膀般的在鄉下人的耳畔飛翔!
這些宇宙間最為質樸的歌唱家,最為率真的演奏家,它們在飛翔中,在棲息中,合奏著大自然的生命交響曲。
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在故鄉,在遙遠了的故鄉,夢里一樣的故鄉啊,總有著鳥的情結在牽掛中濃郁起來。
故鄉的那些鳥兒,故鄉人不知其學名,卻別出心裁,創造性地依其啼鳴聲而名之——
暖的惠風,從南方裹著性感眩暈般襲來,五月端午便蒞臨,金色沁鍍上村頭樹上的杏兒后,又從滿谷、滿坡的麥尖兒上滾過時,“脫腳兒過河”(布谷鳥鳴)邊在田野上、小河畔歌唱著季節的變換,催促著農人要手腳麻利,割麥、插秧“雙搶”在即。
蒙嚨著幾許憂傷的黃昏時分,“哥哥兒苦”在憂憂地哀訴著,一聲復著一聲,不絕盈耳。這樣的鳥兒,這樣的哭鳴,總讓小小的我們心頭兒莫名地發顫,擔心著她哭啞了嗓子。
聽母親說,“哥哥兒苦”背負著一個凄慘悱惻的傳說。老輩老輩的人說,從前,有窮苦人家的哥妹相依為命,哥哥在地主家打工時被害。多日不見哥哥回來,妹妹便去地主家看望哥哥。地主編造謊言,說哥哥外出,便拿哥哥的肉來招待妹妹。妹妹不知是哥哥的肉,便吃了。心有靈犀,妹妹曉得吃了哥哥的肉,曉得了哥哥的冤屈,便變成了一只鳥,整天整夜地在地主家的上空嘶鳴“哥哥兒苦”,哭得村里人個個潸然淚下。
講完了“哥哥兒苦”的故事,母親紅了眼眶;聽完了“哥哥兒苦”的故事,小小的我們咬牙切齒,恨不得馬上去找地主老財算賬。
是啊,一聲的鳥鳴會給小小的我們上一堂難忘的人生課。
“黃瓜瓠子著點油兒”,帶著與人為善的歌聲,從這一家的房頂唱到另外一家的前院,快樂的,充盈著希望的話語,讓我們感受到了一種溫暖。那個時候的鄉下,食用的油料奇缺,每次炒菜,母親會用瓷調羹勺兒,在祖上留下的瓷罐兒里,輕輕地舀出一勺,小心翼翼地在大鐵鍋里均勻地淋上一圈兒,香噴噴的油沁潤開來時,嘩地聲響,菜下鍋了。
當然,伸著脖兒,盯眼看的我們,口水也就流了出來。
于是,“黃瓜瓠子著點油兒”,形象而又生動的鳥語,總會給鄉下人唱來無限的幸福的企盼。
哦——,還有那年年春天南來的小燕子,剪著雙尾,帶著桃紅柳綠,飛越千山萬水,在農家堂屋梁上安家落戶,很多的時候且飛且語:“不吃米,不吃糧,在你家梁上筑個巢!”這是與我們最為親近的鳥了。
瞧啊,故鄉的山岡叢林,家家的屋前屋后的林子,都是鳥兒的家園。
那時,小小的我們曾爬上樹梢掏鳥窩,摸鳥蛋兒,捉幼鳥兒。大人見了,會嚇唬說,當心下雨雷打人喲——,嚇得我們將紅嘴嫩鳥仔細地放回巢里。我們也曾拿自制的彈弓偷偷地襲擊鳥兒。大人們便指著空中盤旋著的鷹,教訓我們:“老鷹瞅見了,會下來叼走娃子的!”唬得我們將彈弓藏了起來。鄉下人用樸素的近乎迷信的倫理來關愛著鳥兒們。
尤為享受的,是放牛的我們躺在青草上,看頭上的鳥兒忽高忽低地跳著舞,聽鳥兒們時斷時續的歌唱。哎呀,云雀子在空中彈射著,撒下滿坡的歡笑;釣魚郎穿行于河畔的水竹、水草間,清亮的甚至有些尖利的叫聲,仿佛在告訴同伴有怎樣的敵情;“長脖老兒”就顯得低調得多,寡言少語,像個隱士,時而也會獨奏些很古的曲調……
在草叢里打著滾兒。嗅著淡淡的花香,我們想象著自己要是一只小小鳥兒該多好,那樣就可以在藍天白云中飛翔。
事實上,和現在我的背著沉重書包的孩子比來,那時鄉下孩子的童年,幸福得就像那鳥兒一樣,自自在在地飛舞!
后來,我們陸續長大,外地求學,離開了故鄉。
世事更迭,故鄉也在發生著巨變。土地聯產承包后,家家可以作主,對大自然的攫取就難免過度了,顧不得生態環保,拼命地向土地索取。于是,曾經郁郁蔥蔥的山岡成了莊稼地,遠遠地看去,仿佛頭上的癩痢;繞著村子的清亮亮的鄉河,被村人攔截成了幾處,建成了用于灌溉和養殖的蓄水壩,微生物過剩的綠腥腥的水里,小蟲子亂竄,連衣服也不敢洗了。村子里的老樹被砍伐了,兩百、三百元地賣給了小販們,就地加工成粘合板材。就像人沒有了房屋一樣,沒有了可以棲息的家,鳥兒們驚惶失措,四處逃竄。其間,不時有獵槍“啪啪——”地圍追堵截:還有,在城里人指導下由鄉下人獨創的“粘網”,這些別樣的“陷阱”就是專門為單純的鳥兒們準備的。非死即傷的鳥兒們,以環保的野味被城里有身份的人高價吃掉了。
多年后,城里人的我逃也似的回到故鄉。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鳥兒,在故鄉一時竟成了稀罕之物,連那些招人嫌的碎嘴子麻雀兒也不多見,蟲害也多了起來。沒有了鳥語的鄉下,似乎不再是鄉下了。新生代的鄉下孩子,只有在教科書尋找故鄉曾經的鳥兒了。出生在城里的孩子,看到的幾種鳥兒,也是在公園里結識的。他們回到了父親兒時的鄉下,卻沒有見到父親眉飛色舞鼓吹的那些啁啾的鳥兒們。
真的,我不知道怎樣向城里的孩子們解釋。我只能說,我萬分地懷想故鄉曾經的鳥語;我只能說,那時的鳥語才是大自然除了人類的最優美的音樂,它們,那些可愛的鳥兒們,才是最具天賦的歌唱家。
夜月清輝中的溫馨的鳥兒的呢喃,只能在夢里聞見!
突然想到一些有關鳥兒的故事。沒有了生態文明意識的鄉下,終將“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景致留在了古書上了。想想啊,沒有了鶴,沒有了蚌,哪里還有漁翁!
“大鵬展翅九萬里”,“鳳凰涅槃”,“鷹擊長空”,“鸚雀安知鴻鵠之志”,“鶴立雞群”,“鵲橋相會”的故事,成為沒有了實物詮釋的傳說了。那些永遠的有關鳥的掌故里,沒有了活生生的鳥語!
物極必反。鳥的日漸遁跡,也曾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關注。于是,終于“亡羊補牢”,下令收繳火銃,嚴禁捕食。
慢慢地,今天的鄉下似乎有了新的跡象,曾經的鳥兒來了,曾經的鳥語開始縈繞耳際。
呵呵,“咕咕”叫的鷓鴣,淘氣的“毛炸子”,“喳喳”報喜的喜鵲……四處漂泊的游子,相繼歸去復來兮!
可是,它們依然沒有棲息的安全的家。村子里,只有鄉下人種植的經濟樹木,那些速生的白楊,大了,便被販子收購剝皮了。那些山岡,沒有了樹木,在水土的流失中,生長著低產的莊稼。鄉河,也不再像河了,淤泥幾乎填平原來的河道;清靈靈的低頭張口就可以解渴的水,變成了綠嘟嘟的穢濁,里面生長著土腥臭氣的激素魚。是的,無論是山岡上,還是村子里,還是鄉河里,都生長著鄉下人的沒有環保色彩的希望!
更為可怕的是,在城里人腹欲的唆使下,故伎重演,鄉下人又開始悄悄地鋪開了“粘網”,一個又一個的看不見的“陷阱”在等待著歸來的鳥兒們!
是啊,我們可以逃離,逃離曾經貧瘠的鄉下,躋身到城里生活,筑巢繁衍后代。可那些鳥兒們,它們能逃離鄉下到城里嗎?城里的建筑森林,透露著硬邦邦的殺氣;城里人的嘴巴,一直在望著野味吞咽著口水。
鳥兒們,真的無路可逃了?
城市在重污中開始吶喊了。而曾經的鄉下,若不再革命,去徹底改變,鳥兒們真的死路一條!
真的!
古書上記載有“鳳”與“凰”,你見過嗎?沒有!于是,我們總會自我安慰:那是傳說中的一種鳥,一種古人想象的鳥!因為,現實中早已經沒有了這種鳥跡啊!
無論是什么樣的謊言和掩飾,不管是誰的,總歸見不得太陽。這是我回到鄉下和父親聊天說到鳥們的命運時,父親望著光禿禿的山岡時說的一句話。
我的父親是一個布衣文人,親近著鳥兒們,聽到“啪”的槍聲,看到城里人來收購鳥兒,他老人家就會恨恨地罵“個舅子的——”。
我總以為我兒時的鳥語令人懷戀,可父親說及他印象中的家鄉鳥語,那才叫“了得喲——”。父親說,那時的鳥兒幾多的,多到曾與人們過不去,村里每一棵大樹上都盤結著鳥窩,嘰喳喳地集會,或爭吵,或打斗,或調情,或戲耍。最和人鬧不快的,是它們憋不住地隨時隨地大小便,夏天聚在大樹陰下乘涼的村人,有時候不得不戴頂草帽。一個關于鳥屎的故事,父親講了幾遍,我忍不住前仰后合樂了幾遍。故事是關于一個本家老輩人的,那是在一棵老皂角樹下,忙里偷閑的村人說著家常,便有人提醒說小心樹上鳥的屎巴巴,本家老輩人邊說“不會吧”邊抬頭仰望,偏偏不巧,一坨鳥屎從天而降,正好落人老輩人微張著的口里。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老輩人一驚,不好,“啊喲——”,連聲“呸呸——”,村里人知道老爺子“中彩”了,都不由捧腹噴飯。老輩人羞愧難當,又氣又惱,嚯地起身,在地上摸起一塊土坷垃,朝著大樹梢撂了過去:“叫你們使壞——”突然來襲的土坷垃,嚇壞了大樹上的集會者們,先是猛地鴉雀無聲,接著“哄”地四處逃散。“戲弄我?有你狗日的好受!”老輩人仰看著大樹,復仇成功后的滿足可想而知。于是,大樹下的家常繼續熱鬧著。可不久,上面的集會重新開始。不過,大家不再理會,有前車之鑒啊,教訓中積累了經驗,千萬別抬頭喲!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兮,雨雪霏霏。當年,大樹下的聚會者中,隨著我的父親二○○九年底的駕鶴西去,幾乎都不在人世了!我不知道,大樹上的集會者中,它們和它們的后代而今尚有幾許!
生命是一個過程,在這個無法把握的過程中,總會有許多的不可預知的變故。所以,我總在想,故鄉的鳥兒,故鄉的鳥語,也是大自然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的形式和內容。往先前無疑是越來越肥美豐富,往日后無疑是越來越貧瘠枯竭。難道這是自然的不可逆轉和違背的法則嗎!我不知道,現在故鄉的鳥兒、我兒時故鄉的鳥兒、父親年輕時的鳥兒,以及父親的父親時的鳥兒,這種不同時段的變化,是不是在印證著訴說著什么?是的,很多的人聽不懂,卻也有很多人裝著聽不懂啊!大自然的法則,是人定不可勝天!
仰望灰蒙蒙的長天,我也只能在心里歇斯底里:歸來吧,故鄉曾經的鳥語!
小河
老家門前的小河,宛若一條長長的白絲綢,纏綿綿地將村子繞了大半圈兒,而后,曲曲折折、閃閃亮亮一蕩而過。
小河的南岸是青青的山岡,北岸是一洼洼的良疇。很有些“一折青山一扇屏,一彎碧水一條琴”的意境。
小河源于桐柏山余脈,逶迤百里融入襄江。村里風水仙兒巴爺掐著手指說,沒有小河,就沒有我們這村子喲——
遠離老家二十余年,小河的清流在心間依然那么溫柔和甜美,汩汩的水聲依然那么撩人心弦,浮動的暗香依然那么迷人魂魄。感念得久了,揪心的時候,免不了夢落小河。
是啊,無論怎樣的歲歲年年人不同,小河都會生生不息地在我心地里流淌,時時刻刻游蕩在我的眼前。
小河淙淙地流著,也留著我孩提時的美好時光。
春雨一落,積水劃向小河的哪兒一處豁口,不待用網,隨手拿了籮筐,朝生水下猛地一撈,就會捕上撲棱棱、白花花的鯽魚。這時節的小河,處處醞釀著魚兒們的愛情。河套里的花兒,媚眼一樣地忽閃、顧盼,悄然地吐出芳香,將小河徹底地女性化了。隨了梅雨的綿密、緊湊,水竹綽約起來,尖著長嘴的叼魚郎奔走相告著,在一片片的或疏或密的翠綠中忙來忙去。
而緩流寬處積淤的白的小沙灘,成了我們的游樂場,裸腳走在細軟的沙粒里,便有種被什么東西密密地舔吮的感覺。小小的我們忘我地撒起歡來,鷹啄兔子,摔絆子,抱鼓碌。野性十足的游戲,滾爬得渾身是沙兒,不必慌的,跳進清亮的潭里,一個魚躍,便一身清白。即便入了學,小河的夏天依然是屬于我們的,精光光的我們會爬上老柳樹,從蔓開的側枝上“咚”地彈進潭里,扎猛子,捉貓兒,摸魚兒。再不,騎在窄窄的天藍色的石板上,雙腳伸進亮亮的柔柔的水里,由那些作樂的魚兒梭子樣地游來啃嚙腳丫、腳心,那種酥癢時的滿足無與倫比。受不住這美妙的逗弄,一縮腳,或禁不住“吃”地一笑,這些水中尤物就忙不擇路地一竄,不見了蹤影。戲水的快樂,美麗了我們的童年,甚至讓我們忘卻了開學在即。
隨著“唯有讀書高”的呼聲春水一樣高漲,我們不得不疏遠了小河。然而,星期天的小河里又爆起了我們的喧鬧聲,無憂的流水總能流去課堂上積下的重壓。于我們的眼里,小河的上游遙迢,下游深遠。站在南畔最突出的松樹岡上遠望,小河就是一條綠白相間的帶子,深情地依岡繞田,彎彎地伸向遠方。我們總沒有依據地猜想小河流到夕陽的地方才住的腳,夕照下熠熠的河壩,或許就是小河的家吧。
有些神秘色彩的,當數雨后天晴去河里捕魚。下網須在子夜時分。父親說雨后的水營養厚,供魚可食的水草油嫩。等到天擦黑,魚兒們就逆水而上,覓食、嘻戲或尋找愛情。待夜里零點前后飽了肚子,魚兒們就順水而下。父親常在這時帶我們下網,堵住魚的回路。怕錯過下網的最佳時機,我們便在院里打坐,聽父親擺他的“封神榜”。
待月亮、星子移動到一定位置,父親打住古話,站起身說聲“拿網”,我們便連一絲的睡意也沒有了。于是,水乳一樣且柔且亮的月光下,我們向著小河走去。此時的村莊、田野都安詳地入夢了。螢火蟲兒們在稻田間舞蹈著,編織著屬于他們的奇妙童話。而不肯緘默的蟲子們,熱鬧了白晝,又熱鬧了夢一樣的夜晚,像是開家庭晚會。
而當走進小河的懷里,陡然感受到它溫愛的鮮活的呼吸,流水的彈奏聲時疾時緩地傾訴著怎樣溫馨的故事。下網的地方是有講究的,選在河面狹小、落差大、水流急的地方。
第二日一早,從床上跳下來直奔小河的我們,就看到長長的網袋子里擠滿了只能動彈的鯽魚、鯉魚、財魚,有時還有團魚、“咯呀”魚。也有夜間知曉同伴落網而長一智“逃脫”的魚,卻只能躲在水深且緩、草密的地方。不用急的,只將上游壩口封了,待流水小了、淺了,這些自作聰明的魚不得不順水入網,或者臥在潭里待擒了。這些肥美的水鮮,往往成了我們的學費。真正到碗里的魚,總是些賣不起價的“竄條兒”、“石鼓郎片”、“浪里狗”們……
昔我往矣,河水清清,綠柳依依。這便是從前的夢一樣的小河了。
再次認真地面對小河時,村子里豎起了一幢幢的小二樓,以及上游介日地“哐啷”作響的小企業。
岸邊的一處處百年曲柳不見了,初夏盛開的一團團香雪的槐林不見了,南岸的青松岡仿佛禿了頭。黃鸝、“布谷”、“脫腳過河”、“哥哥苦”們,那曾經鮮亮的叫聲絕耳了。幾人深的潭被淤成了泥坑,緩水面的地方被村人營造成了稻田,河套因開墾,水土流失,而襤褸不堪了。河里的魚,也只有生命力極強的“竄條”了。令人痛惜的是鯉、鯽尚未長成,便被人投藥捕捉了。僵硬的、灰脫脫的小河,從岡坡腳兒、田野襟兒下憂憂傷傷七扭八拐地遠去了。
無可奈何花落去。小河的春天就這么過去了。我無法考據小河的歷史,只聽村里老人說,六十年前,小河的上、下游還有原始森林。
于是,每次回老家,我都會執著地獨自一人在朝霞燦爛時分。站在南岸岡頂上,看炊煙纏綿的村鎮,感受日出一樣的生命不可阻擋地到來。也在殘照時分,走進小河的襟懷,面對尚有幾許碎銀閃動的下游河壩,體悟生命的無限滄桑,生出不盡的感傷來。久久不散的情緒,總使我想及那句不可言傳的詩句: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小河的沒落,只能讓我更為珍惜地去尋找那些久遠的感覺和記憶來。
我對它的思念,不只是無名花草的芬芳對我永遠的迷惑,不只是對潭里翻跟頭無愁的兒童和柳下苦讀有慮的少年的追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