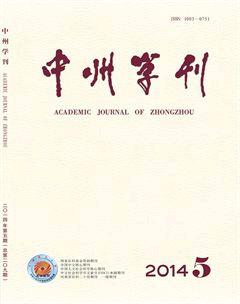民國時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與救治
付燕鴻
摘要:民國時期的“城市病”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城市貧民生活上的貧困是其直接誘因,“民族—國家權威”的缺位是其制度性原因,社會結構失衡與城市管理滯后是引發“城市病”的內在因子。此外,近代城鄉結構二元化對“城市病”的發展也有一定助推作用。由于缺乏對“城市病”及歷史成因的深層認知,民國時期的天津市政當局在應對“城市病”的過程中大多滿足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沒有著眼于謀求根本之解決。歷史雖然無法重演,但其所凝結的歷史經驗教訓則可以警示未來。
關鍵詞:民國時期;天津;“城市病”;成因;救治
中圖分類號:K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05-0139-06
“城市病”主要是指“在城市生存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各種要素之間關系嚴重失調的現象,而且是被大多數人公認為消極的、必須盡力解決的問題。”①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市病”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近年來,有學者從城市化的視角論及近代“城市病”,也有學者分析了農民工與近代“城市病”的關聯性。②然而,從總體上看,學界對民國時期“城市病”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尤其是對其時代特征及其形成的深層次原因還缺乏比較系統深入的研究。本文擬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為例,對其在城市化進程所產生的犯罪、娼妓、乞丐、失業等各種“城市病”及其形成原因進行整體分析,并試圖從救治組織機構的設立、法規制度的制定、社會控制的加強等方面對其救治措施做些梳理。
一、民國時期“城市病”的主要癥狀
民國時期,整個社會動蕩不安,亂象叢生,各種“城市病”日益凸顯,城市社會成為罪惡的淵藪。就“城市病”的表現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1.社會失序嚴重,犯罪活動猖獗
犯罪是一個傳統的社會問題,但在近代天津城市化過程中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發展態勢。據統計,1908年天津市的犯罪案件只有316起。③到1928年則高達9051起,1929年為3686起,1930年為3916起。④后面兩年的數值雖然有所回落,但平均每天的刑事案件也最少在10起以上。就刑事犯罪的人數而言,1924年為7116人,其后人數不斷走高,至1928年前后達到高峰,共有9051人,之后犯罪人數有所減少,但仍處于高峰值狀態。⑤
就各類違警案⑥而言,犯罪人數之多令人瞠目。僅1931年下半年,違警人數就達6192人,1932年增至13167人,1933攀升到21406人。⑦就違警案的具體類型來看,以妨害秩序類最多,其次為妨害交通類,再次為妨害衛生類和妨害風俗類。此外,還有妨害安定、妨害公務、妨害他人財產、妨害他人身體、誣告偽證、湮沒證據等諸多種類。
2.乞討人員眾多,行乞活動職業化
乞丐,俗稱“叫花子”,古已有之。近代以前的乞丐多因生活困難,不得已而為之,在困難解決之后,就會主動脫離乞丐隊伍,自謀生計。民國時期,乞丐遍布天津城廂,南市、大洼東、車站、鐵道外、侯家后等處尤多。⑧據官方統計,僅1934年天津乞丐就有兩萬余人。⑨當時的乞丐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日益職業化。他們一般都有相對穩定的組織、各自的地盤和比較嚴格的幫規。如每個乞丐加入某個組織之前必須“認師拜桿子”。⑩新手上路必須向師傅“獻果拜門”。在“排刀”“打磚”“叫街”“釘頭”“拉破頭”“縫窮婦”等各類乞丐中,以前面兩種乞丐的規約最嚴。凡違犯規約者,輕者開除,重則“砍斃”。不同的乞丐群體,往往有一套自己的謀生之道,說明乞丐正如其他職業一樣,成為眾多貧民維系生存的一種方式。這不僅是個體之不幸,也是整體社會結構及其病態的表征之一。
3.娼妓業泛濫,社會風氣惡化
民國時期的天津工商業較為發達,婦女就業渠道較多,大多從事工人、服務員、醫生、護士、職員、教師、編輯、律師等新式職業,但也有不少婦女淪為從事出賣肉體為生的娼妓。天津娼妓業的迅速發展,尤其下層妓院的泛濫,派生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1860年開埠后,天津南市的娼妓業逐漸興盛。1900年的庚子之變,天津350余戶妓院大部被毀,妓女紛紛逃亡。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天津的娼妓業死灰復燃,妓院數量和妓女人數有增無減。據統計,1926年,天津市共有妓院468家,妓女3594名。1930年,天津有妓院571戶,妓女2910人。1936年,僅“日租界”就有“公娼”妓院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多達1000余人。
娼妓業合法化后,地方政府對“樂戶”和妓女科以稅收,并保護其正常營業,吃喝嫖賭、逼良為娼之風隨之泛濫。
4.經濟萎靡不振,失業問題嚴峻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城鄉經濟萎靡不振,失業問題愈發嚴重。1932年,天津各商號陷于勉強維持的狀態,至當年舊歷年關時,全市商界十有八九“賠累不堪”,以致紛紛歇業,裁汰店員。據統計,僅當年失業店員就有5000多人。另據1932年1月天津市各區失業人口的調查結果顯示,僅第一區就有30790人失業。1932年全年天津的失業人口總數約為10萬人。1936年,《天津市政府公報》公布的天津失業人數為28644人。同年,實業部估計天津市失業工人數為18175人。上述數據還只是官方的保守數字。失業問題往往是與無業問題相伴相隨的。因就業機會少,總有一大批人是無業者。據統計,1928年,天津的無業人口為296763人,1929年增加到379655人,1930年又增加到405779人。
天津在近代城市化過程中衍生出來的“城市病”不獨上述幾種,此外還有自殺、離婚、販毒等問題。因篇幅關系,在此不一一列舉。
二、民國時期“城市病”的主要誘因
從上述“城市病”的主要癥狀來看,就其形成原因而言,顯然有別于西方國家。西方早期城市化過程中的“城市病”是因過度工業化而引發的,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病”的發生發作則有其特殊的成因。
1.城市貧民生活上的貧困是滋生各種“城市病”的直接原因
生活上的貧困往往是導致貧民走上偷盜、賣淫等邪路的最直接原因。就犯罪類型來看,以經濟類型的盜竊案為最多。如天津市社會局統計的1930年全年5802起各類案件中,盜竊案為1848起,占全年各種犯罪總數的32%。又如1932年7月至1933年6月天津市地方法院簡易法庭處理的3691起刑事案件中,僅盜竊案件就有1698起,占案件總數的46%。就犯罪者以前從事的職業來看,以工商從業者為最多,其次為無業游民。如天津市社會局統計的1930年全年5802起犯罪案件中,從事工業者有2321人,占總數的40%;從事商業者有1228人,占總數的21%;無業者1510人,占總數的26%。這是因為工人、店員、伙計等貧困群體收入低微,不足以維持生計,并隨時面臨失業的危險,為生計起見,往往容易鋌而走險,走上犯罪的道路。
“女子做娼妓,大半都是受著經濟的壓迫。”天津市社會局于1929年12月10日起至1930年5月24日,對天津市571家“妓戶”2847名妓女從娼原因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妓女“為娼”的原因以經濟壓迫的為最多,共計1836人,占調查娼妓總人數的64%。因家庭變故,如家長去世、父母病殘、夫死等原因不得已淪為娼妓的也不在少數。失業、自殺等“城市病”等無不與經濟窘迫密切相關。當時《大公報》上關于因經濟原因造成失業或自殺之類的報道并不鮮見。失業加劇貧困,常常成為那些朝不保夕的貧民自殺的借口。
2.“民族—國家權威”缺位是“城市病”日趨加重的制度性原因
“民族—國家權威”的失落使國家權力不僅不能形成應對這些“城市病”的全局性操控,反而成為這些“城市病”日趨加重的制度性原因。
晚清至民國時期,內憂外患不斷,國家局勢動蕩不安。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雖然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統一,但“橫在中國社會面前的整個生存問題,比之三十年以前更是迫切緊張”。財政上的貧困化削弱了政府體系的權威和能量,政府權威的失落又反過來加劇了政府的貧困化。財政上的貧困使地方政府在對相關“城市病”進行救助常常顯得“力不從心”。1928年6月天津社會局成立后,積極籌劃創辦“貧民工廠”,希望根本解決城市貧民問題。為籌措開設貧民工的廠經費,社會局還一度開征“乞丐捐”。然而,由于政府權力式微,在實際操作層面遭遇重重困難,“乞丐捐”的征收并不像當局者想象的那樣樂觀,商戶借故遲交甚至不交,結果導致“抽捐甚微”,故后來當地政府不得不下令取消“乞丐捐”。后來,天津社會局不得不改征附加房捐百分之一,定名為“房捐附加慈善費”。最后,社會局通過舉辦義務戲,收得款項3000多元,才創辦起貧民工廠第一分廠。1929年3月貧民工廠開工,第一批收容乞丐共170余名。相對天津當時幾十萬貧民而言,這無異于杯水車薪。
為防止花柳病傳染,早在1932年1月,天津社會局就計劃設立性病檢驗所,并擬定了具體計劃和檢驗規章,但因缺少經費,一時難以成立。直到1937年前后,天津才重新籌設妓女檢治所。籌備多日的妓女檢治所于1937年4月26日正式啟動,但不久又因全市“樂戶”娼妓均存觀望,期間雖經勸告,一直未有檢治。由于天津政府財政上的貧困,使其政治職能不能盡可能地發揮,也無法有效地對各種“城市病”進行宏觀調控,這更加造成了政府權威的喪失,使它僅有的一點點現代化計劃和努力也無法付諸實施。
3.城鄉結構日益二元化是“城市病”泛濫的重要推手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社會結構由傳統的城鄉“無差別的統一”為日益擴大的城鄉差異所代替,“農村破壞,都市發展,兩者背道而馳,這是現代中國社會變化的方式”。
天津開埠通商后,城市工商業、對外貿易等獲得較大發展,加上便利的交通網絡使得天津的聚集能力迅速增強。城市經濟產生的強大“拉力”,吸引著大量的人口涌入天津。1906年,天津的常住人口還只有42.5萬人,至1928年,就迅速增加到112.2萬人,短短20多年時間增加了60余萬人。到1930年前后,天津已經發展成為僅次于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工業城市。這些增加的人口不僅僅是商人、手工業者、紳士和達官貴人的聚集,更多是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和破產農民。這種農業人口與城市人口的此消彼長,是城市和鄉村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帶來的必然結果。
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天津城市的急遽擴張與廣大鄉村社會的衰退如影相隨。由于戰亂頻繁和自然災害頻發,造成日益嚴重的離村風潮。據統計,1920年左右,冀魯豫三省的離村率達到3%—22.8%不等。到1935年前后,山東省離村最低為西部的夏津和恩縣,約為10%左右,最高縣為南部費縣、莒縣,達60%左右。這些逃入城市的災民、難民在災害過后最初有相當部分選擇返回家鄉,城市只是他們的臨時“避難所”。但隨著近代災害頻仍,戰亂不斷,農村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這迫使越來越多的災民斷了回鄉的念頭,在城市里由“暫避”逐漸變為永久性的“定居”。大量移民源源不斷從鄉村遷入天津后,由于人口遷入城市的速度和規模遠遠快于經濟發展的速度,進入城市的勞動力不能完全被工業部門吸收,造成勞動力滯留市場。這樣,雖然實現了勞動力由鄉村向城市的遷移,但并沒有實現就業結構的根本性變化。眾多移民缺少維持生存的最起碼的“正當”營生,因之淪為城市中的貧民,并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城市病”。
4.城市化進程中社會結構失衡發展與城市管理體制滯后是引發“城市病”的內在因子
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社會結構是一個“士農工商”為主的社會,但是在明代建天津衛時,因軍事而興,居民以軍人為主,此后隨著天津城區的擴大,漕運、鹽業的發展,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城市。據1846年《津門保甲圖說》統計,當時天津城區范圍內共有32761戶,這些人口中,“鹽商”“鋪戶”“負販”等合計17709戶,占當時天津城區總戶數的54.06%。從事商業的戶數如此之高,使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時期的天津是一個比較地道的商業城市。1860年天津開埠通商后,伴隨著西方先進生產方式的傳入,新式交通的興建,天津的工商業、對外貿易獲得較快發展,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傳統的商業城市發展成為一個工業、商業、貿易為一體的近代化城市。
伴隨著近代天津城市化進程的展開,引動了其社會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天津原有的社會階層結構被打破,產生了新的買辦階層、工商階層、寓公階層、知識分子階層、勞工階層、貧民階層等。這些階層中,以貧民階層人數最為龐大。1929年有人發表《貧民與社會》一文,驚嘆天津的貧民數之多:“觸目驚心的本市貧民人數——三十五萬七千多。”隨著天津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貧民階層的人數也是在一天天擴大,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在一天天的尖銳和惡化。凍餒、死亡、娼妓、乞丐、流民、盜匪以及社會上的各種騷亂、暴動、政潮等無不與城市貧民的大量存在密切相關。人數龐大的貧民階層與天津社會結構變化呈現明顯的不均衡發展態勢,貧困人口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社會結構的變動速度,城市承載能力不足,因此,形成了數量龐大的無業、失業人群,這成為引發各種“城市病”的內在因子。
三、民國時期救治“城市病”的主要措施
民國時期,社會危機不斷,貧富懸殊,軍閥混戰,兵匪四處打家劫舍,天津的犯罪、娼妓、乞丐、失業、自殺等“城市病”日益嚴重。為有效遏制“城市病”的蔓延,消弭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確保城市化和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天津當局開始對城市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并有針對性地對相關“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救治措施。
1.成立救助機構,加強“城市病”的有限調控
面對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天津社會局先后設立游民收容教養所、婦女救濟院、職業介紹所等機構,冬天設置“暖廠”“粥廠”等,對貧民實施救濟。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將天津改為特別市,戰后難民流離失所,散兵游勇麕集。為“安輯流亡”,時任天津警備司令的傅作義將軍于1928年11月在河北新大路設立“游民收容教養所”。根據天津市社會局提供的1933年天津市收容機關概況來看,這時期天津全市收容機關主要有10所,即天津市市立貧民救濟院、天津市婦女救濟院、長蘆育嬰堂、戰區難民收入所(6處)、廣仁堂等,其中以天津市立貧民救濟院的規模最大,最多可收容貧民2221人,最少也收容1232人。這體現了天津政府為維護社會秩序,救助底層民眾所做的貢獻和努力。
為救助失業問題,1928年6月天津社會局成立后,積極籌設“貧民工廠”,后經多方籌備,1929年2月28日,第一貧民工廠正式成立。貧民工廠的設立,積極訓練貧民謀生技能,不以盈利為目的,有利于對于解決城市貧民的就業問題。但因政府資金投入不足,加上生產出來的產品很難符合市場的需求,不得不停辦或轉變經營方式,其在救助貧民方面所取的效果并不理想。國民政府企圖通過建立貧民工廠根本解決貧民生計的計劃很快歸于流產,勉強維持到1929年9月,最終宣告停工,被救濟院合并。
在娼妓問題上,天津原來就有“濟良所”等救助機構。1929年,天津市當局決定成立“婦女救濟院”。結果一般受壓迫的婦女大多不再去“濟良所”,而是直接投奔“婦女救濟院”,因為“救濟院規模較大,設備也比較完全,訓育教養,和學校一樣”。再加上“濟良所”管理上混亂不堪。相形之下,“婦女救濟院”不僅經費比較充裕,而且環境較優,待遇較好。到1930年4月,天津當局成立“慈善事業聯合會”(1931年4月更名為“救濟事業聯合委員會”),負責全市的賑濟事宜。并于1931年8月“提出了救濟全市貧民計劃大綱”。可是對于如此棘手的社會問題,“慈善事業聯合會”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許多計劃不了了之。很顯然,近代天津的城市管理體制遠遠落后于城市化進程,“城市病”積重難返,最終制約著天津的整個城市化進程。
2.頒布法規制度,規范“城市病”的有效治理
早在1902年8月天津巡警局就公布《巡警條例》。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總局制定了《違警罪目一百二十五條》,內容涉及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戶口管理、衛生防疫、社會風俗等多個方面。民國時期,天津市政府不斷加強對地方治安的控制。為防治盜匪,維護治安,1931年,天津市公安局特厘定《防捕盜匪獎懲辦法》,規定各區界內發生盜匪案、搶奪案等,限7日內破獲,逾限未破獲者記過,若一個月內未發生匪案者,即給予記功。這些違警條例及其相關法令的出臺,一方面有利于規范人們的行為,防止越軌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也是統治者強化其統治,加強對人們人身控制的重要體現。
在治理娼妓問題方面,雖然早在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總局就制定了《管理娼妓章程》,1910年,直隸“巡警道”發布了《樂戶規則》,但從這些規定來看,政府方面對娼妓業管理尚未做出明確規定,只是對如何懲辦拐賣婦女、逼良為娼及暗娼等做出了一些具體規定。1915年,直隸省成立“警務處”,并兼管“捐務處”。該處對全市妓院核定等級,發放《樂戶許可執照》,按等級收捐;對妓女發放《妓女許可執照》,按所在妓院等級收捐。政府承認娼妓業合法化,妓院持照經營并納捐。1930年的“樂戶捐”和“妓女捐”征收辦法規定:一等“樂戶捐”每月每戶繳納20元,一等“妓女捐”每人每月繳納4元;二等“樂戶捐”每月每戶繳納10元,二等“妓女捐”每人每月繳納3元;三等“樂戶捐”每月每戶繳納5元,三等“妓女捐”每人每月繳納1.5元;四等“樂戶捐”每戶每月繳納4元,四等“妓女捐”每人每月繳納1元;五等“樂戶捐”每排(每15人為一排)每月繳納4元,五等“妓女捐”每人每月繳納0.5元。政府對“樂戶”和妓女科以稅收,并保護其正常營業。“七七”事變后,日軍占領天津,并成立偽政權。他們以繁榮市面、加強稅收為由,公開提出可隨便設立“樂戶”,并于1938年3月制定了《天津特別市公署警察局管理樂戶規則》和《妓女檢治規則》,設立“樂戶公會”,管理窯主及妓女。由于規制的寬松,一些流氓混混也紛紛申請開設妓院,導致天津妓院驟增,娼妓業畸形發展。到新中國成立前,天津仍然暗娼盛行,傳染病嚴重,有關的規章制度形同虛設。
3.加強社會控制,抑制“城市病”的滋生蔓延
社會秩序的建立和維護是靠社會控制來實現的。對于近代天津社會的各種“城市病”,天津地方政府在進行救助調控、頒行法規規制的同時,還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以期抑制“城市病”的滋生和蔓延。
在防治各類犯罪活動方面,20世紀30年代,天津警察依據《違警罰法》,對妨礙秩序、妨礙風俗、妨礙衛生、妨礙他人身體和財產等各類違警案件,實施處罰。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權力全面介入到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之中,不僅標志著國家權力的擴張,同時也代表著城市管理向著近代化方向發展。
在應對乞丐問題方面,天津市政當局認為大量乞丐的存在不僅有礙觀瞻,影響地方治安,甚至把其視為民族恥辱的象征,是國家孱弱的表現,“男女老幼乞丐,凡遇中西人士,鄙言諂語,攔路哀求,百般乞憐。尾隨其后,悲哀討厭之腔,不堪言狀。津地位我國巨埠,華洋雜處,若不設法取締,不但成饑孚之患,貽笑外人,且辱國體而礙警政。”故下令對其逮捕實施或進行強制性收容。尤其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天津市內乞丐的增多,天津當局三令五申,逮捕乞丐,進行收容管制。1923年3月4日,警廳發布的《查禁乞丐之廳令》規定:“飭屬隨時嚴行取締,嗣后遇有乞丐,隨行帶案送廳。”此后,官方不斷加大對乞丐游民的收容力度。1929年2月,天津特別市公安局奉市府令即訓令各區所,限5日內將界內游民乞丐一律送交游民收容所。1936年10月,天津市公安局局長程希賢電令全市公安局各分局所,搜捕男女老幼乞丐,送救濟院收容,限期3天內全數捕盡。然而,因乞丐人數眾多,地方政府常因房舍狹小,財力不逮,無法安插。1934年8月9日,“婦女救濟院”發生的“乞丐大暴動”,就充分暴露這方面存在的問題。暴動雖經彈壓,幸免肇事,但膳宿問題,仍無法解決。對于拘捕的400余名乞丐,“救濟院”方面最終的處理辦法是,除老弱及染有毒品嗜好者外,擇其壯年確能謀生者,陸續準其請假出院謀生,其老弱殘廢及染有毒品嗜好者,撥入“救濟院”的“戒毒”“殘廢”等區,分別戒除留養。政府和社會方面為解決乞丐問題雖然采取了一些驅逐和收容管制的辦法,但無益于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社會問題。
四、余論
近代天津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城市病”,其直接誘因是城市貧民生活上的貧困,其制度性原因是晚清至民國時期“民族—國家權威”的遲遲未能建立,而城鄉二元化發展對“城市病”的發展起著比較明顯的推助作用。此外,天津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結構的失衡與城市管理制度的落后,是引發各種“城市病”的內在因子。多重因素的疊加,致使民國時期天津“城市病”愈發嚴重。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反過來又阻礙了天津的城市化進程,同時也加劇了城市管理者所面臨的窘境。
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城市病”,天津政府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治理辦法,這些辦法就個體而言,確實在急救活命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矛盾,而且對改善城市形象也有一定好處。然而,因“民族—國家權威”的喪失,使得國家對于城市社會的利益調整和控制基本處于缺位狀態,雖然不乏善舉,但畢竟杯水車薪。由于在治理過程中多著力于解一時之困,而未著眼于謀求治本之策,加上缺乏經費,并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城市貧民饑寒交迫的悲慘厄運,“城市病”也因此無法得以根治。
“城市病”不是天津社會所獨有的現象,民國時期的中國城市,尤其是在人口增長較快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天津“城市病”的發生發展歷程警示我們,在城市化進程中,關注社會分層和社會結構的均衡發展,妥善處理好城鄉關系,不僅是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城市病”的化解,必須建構在城鄉社會均衡發展,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保障制度的健全與完善等社會要件相結合的基礎之上。
注釋
①鄧偉志:《當代“城市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9頁。②有學者以近代上海為中心,揭示城市化與城市病的關聯性,參見戴鞍鋼:《城市化與“城市病”》,《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有學者以蘇南為中心,歸納了城市病的十大病癥,以期揭示城市病與農民工向城市集中的內在關聯性,實際行文僅是簡單的列出了十種城市病,而未深入剖析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參見池子華:《農民工與近代中國“城市病”綜合癥》,《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③孫巧云:《清末民初天津下層市民犯罪問題研究——以〈大公報〉為中心》,福建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5月,第20頁。④《最近三年(1928—1930)天津市刑事案件比較》,吳甌:《天津市社會局統計匯刊·社會病態》,天津社會局,1931年。⑤《最近七年(1924—1930)天津市刑事犯人數比較》,吳甌:《天津市社會局統計匯刊·社會病態》,天津社會局,1931年。⑥民國時期的犯罪包括違警罪和刑事罪,違警罪系指妨礙妨害安定、妨害秩序、妨害公務、妨害交通、妨害風俗、妨害衛生、妨害他人身體財產等違反警務的行為,是針對輕微危害社會行為的一種制裁措施;刑事罪是觸犯國家刑法,具有刑事違法行為進行的處罰行為,與近代城市貧民相關的犯罪多屬于前者。⑦內政部統計司:《民國二十年下半年全國警政統計報告(第一類違警犯統計)》,1933年;內政部統計司:《民國二十一年度全國警政統計報告》,1934年,第35頁;內政部統計司:《民國二十二年份全國警政統計報告》,1935年,第32頁。⑧《收容乞丐》,天津《益世報》,1933年11月7日。⑨滌亞:《救濟乞丐》,見上海市社會局:《社會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6頁。⑩《惡丐宜禁》,天津《益世報》1922年8月15日。周利成:《檔案解密:近現代大案實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261—263頁。《社會的下層——平津一帶乞丐的生活》,天津《大公報》1933年1月6日。天津市社會局:《天津市妓戶妓女調查報告》,1931年,轉引自李文海:《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底邊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25—539頁。江沛:《20世紀上半葉天津娼妓業構成述論》,《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衰頹之天津百業凋敝》,天津《大公報》1933年1月30日。《失業人數之可驚》,天津《大公報》1932年1月1日。解敬業:《中國的失業問題》,《社會學雜志》第5卷第4號,1932年9月。《天津市市民職業統計表》,《天津市政府公報·統計》第87期,1936年4月。《滬杭平津失業工人日增》,《實業部月刊》第1卷第4期,1936年7月,第157頁。此有無職業人口數將當時在津的外國人也統計在內,參見吳甌:《天津市社會局統計匯刊·戶口》,天津社會局,1931年。《天津市十九年份各種犯罪比較》,吳甌:《天津市社會局統計匯刊·社會病態》,天津社會局,1931年。天津市政府統計委員會:《天津市統計年鑒·社會類》,1935年,第47—48頁。《天津市十九年份犯罪職業比較表》,吳甌:《天津市社會局統計匯刊·社會病態》,天津社會局,1931年。《上海淫業問題(四三):經濟上的淫業問題》,《新人》1920年第1卷第2期,第105頁。天津市社會局:《天津市妓戶妓女調查報告(1931年)》,轉引自李文海:《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底邊社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50—551頁。《南市元興客棧里二十歲青年因失業自殺》,天津《大公報》1931年9月2日;《窮愁交迫投河自殺》,天津《大公報》1934年11月17日;《西頭茶店口昨發生一家三口投河慘劇》,天津《大公報》1935年4月21日。許滌新:《農村破產中底農民生計問題》,《東方雜志》第32卷第1號,1935年1月1日,第56、52頁。天津特別市社會局:《天津特別市社會局一周年工作總報告(1928.8—1929.7)》,內部資料,1929年,第250、252頁。《貧民工廠計算書(1929年6月)》,天津市檔案館,J0054—2—003316。《函公安局定期開整理乞丐捐會議(1929年6月)》,天津市檔案館,J0054—1—000720。周谷城:《中國社會之變化》,上海書店,1989年影印本,第314頁。李競能:《天津人口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82頁。李文海:《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頁。《津門保甲圖說》卷一,道光二十年(1846年)。鳳蔚:《貧民與社會》,天津特別市社會局編:《社會月刊》1929年第1期(創刊號),第80頁。天津市政府統計委員會:《天津市統計年鑒·社會類》,1935年,第52頁。《濟良所一瞥》,天津《大公報》1930年3月10日。《公安局昨會議決定防捕盜匪獎懲辦法》,《大公報》1936年3月1日。郭鳳岐:《天津通志·公安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156頁。《自動的廢娼》,天津《大公報》1930年3月5日。周利成、王向峰:《舊天津的新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頁。《警廳取締乞丐之訓令》,天津《益世報》1926年8月21日。《查禁乞丐之廳令》,天津《大公報》1923年3月4日。《公安局慎重民命》,天津《大公報》1929年2月11日。《津公安局搜捕乞丐限三日內逮盡》,天津《大公報》1936年10月22日。《天津市市立救濟院函社會局(1934年8月31日)》,天津市檔案館,J0131—1—000654。
責任編輯: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