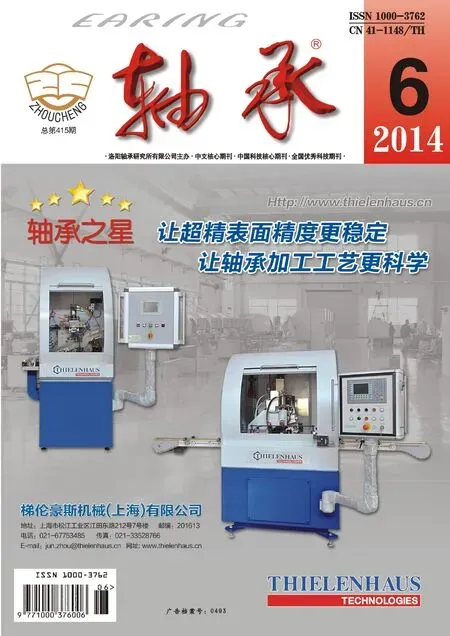高鐵軸承試驗臺內部氣固雙相流內循環(huán)分析
劉永剛,宋黎明,張曉楊,謝金發(fā)
(河南科技大學 a.機電工程學院;b.車輛與交通工程學院,河南 洛陽 471003)
我國雖然是世界上高速鐵路里程最長的國家,但由于起步較晚,高鐵軸承的生產及相關試驗設備和試驗技術仍處于研究階段,高鐵軸承主要來自FAG,NTN和SKF等國外公司,這成為制約我國高鐵發(fā)展的瓶頸[1]。現如今FAG,NTN及SKF公司均擁有相應的高鐵軸承試驗臺,其試驗速度可達550 km/h,而國內當前只能針對200 km/h以下的軸承進行模擬試驗,差距可見一斑。
只有對高鐵軸承進行大量的試驗,通過數據分析和評價,才能為改進高鐵軸承的設計方法和制造工藝提供數據支持。根據高鐵軸承工況條件設計的高鐵軸承防粉塵密封試驗臺,要求軸承在室溫到100 ℃之間工作,同時軸承周邊應布滿粉塵顆粒,以考核軸承耐高溫和耐粉塵的性能。文獻[2]利用Fluent軟件分析了外循環(huán)粉塵箱內部的流場和粉塵顆粒運動軌跡,得到粉塵箱內部流場速度的梯度變化和不同粒徑粉塵顆粒的運動軌跡。文獻[3]通過建立高鐵軸承外滾道的局部傳熱模型,采用熱流網絡法分析了軸承外圈溫度沿軸向的分布情況,為試驗臺潤滑和冷卻系統(tǒng)設計提供了數據支持。文獻[4]給出了高鐵軸承試驗臺液壓伺服加載的總體設計方案,通過建立高鐵軸承試驗臺動力機構的承載流量方程和承載壓力方程,推導了液壓伺服控制系統(tǒng)的傳遞函數。文獻[5]探討了時速300 km/h以上高鐵軸承耐久性試驗臺的設計方案。文獻[6]對高鐵軸承試驗臺主軸進行了模態(tài)分析,優(yōu)化了主軸結構,確定了陪試軸承的位置。
為了給時速350~500 km/h高鐵軸承試驗臺粉塵箱的設計提供理論依據,滿足高鐵軸承的試驗條件,采用粉塵箱內循環(huán)的形式,在粉塵箱內部設置一定數量的風扇,通過研究風扇數量、布局和位置等對流場和粉塵分布的影響,分析粉塵箱內部氣固雙相流粉塵顆粒運動及變化規(guī)律,同時探討試驗臺箱體和軸承壁面的磨損形式。對粉塵箱內部的氣固雙相流場進行仿真分析不僅能對粉塵箱的設計提供一定的指導,更有利于降低軸承試驗臺的制造成本。
1 分析流程
隨著計算機技術和計算流體力學的發(fā)展,計算流體力學(CFD)模擬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可視化能力較強、能提供全流場流動細節(jié)且不受模型尺寸限制等優(yōu)點。采用全隱式耦合算法的CFX軟件被廣泛用于模擬流體流動、耦合傳熱、粒子追蹤、旋轉機械、化學反應和燃燒等問題,其革命性的求解技術克服了傳統(tǒng)算法的反復迭代過程,CFX的計算速度和穩(wěn)定性較傳統(tǒng)方法提高了1~2個數量級[7]。其獨有的基于有限單元的有限體積法既保障了有限體積法的守恒,又吸收了有限單元法的數值精確性。先進的SST湍流模型算法比k-ε在旋轉流體方面更穩(wěn)定、更精確,且CFX在旋轉機械方面有強大優(yōu)勢,非常適合本課題的分析。CFX主要由CFX-Pre,CFX-Solver和CFX-Post共3部分組成[7],求解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CFX求解流程圖
為了利用CFX提供的SST湍流模型對密封箱體氣固雙相流進行數值模擬,需要對高鐵軸承實際運行環(huán)境的流場分布進行分析。實況中高鐵軸承工作狀態(tài)是滾動的,這樣會帶動周圍流場一起繞軸向旋轉,但速度并不同步,因此試驗臺軸承內流場始終處于旋轉狀態(tài)。試驗臺的密封是為了營造良好的測試環(huán)境,高鐵軸承實際運行過程中不可能做到嚴格密封,軸承會受到來自不同方向和不同尺寸粉塵的撞擊。軸承實況流場內的粉塵運動形式主要是圍繞軸向旋轉滑移,同時還有來自軸向、徑向及其他不同方向的滑移撞擊。
本研究雖可以對高鐵密封箱的設計提供一定的幫助,降低試驗成本,但也存在一些缺點和困難:(1)仿真分析的理想化設定與實際工況有略微出入;(2)通過內置風扇模擬高鐵軸承試驗臺內流場的內循環(huán)狀態(tài)有一定的局限性,無法確認最優(yōu)化狀態(tài)下的風扇數量、位置及尺寸;(3)模擬分析花費的時間較長,且對計算機有很高的要求;(4)研究對象封閉,風扇轉動會導致風扇前后產生壓力差,進而產生回流現象,故得到一個理想的軸向速度相對困難。
2 計算模型
2.1 理論基礎
2.1.1 流體力學控制方程
流體流動遵守物理學的質量守恒定律、動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其對流體運動在數學上的描述就構成了流體動力學的基本方程組——N-S方程組,該方程組包括連續(xù)性方程、動量方程和能量方程。不考慮能量方程,N-S方程組可表述為以下形式:
連續(xù)性方程
(1)
動量方程
(2)
μe=μ+μt,
(3)
式中:μe為湍流黏度系數;μ為分子黏度系數;μt為渦流黏度系數;ρ為流體密度;μi,μj(i,j=1,2,3)為速度分量;xi,xj(i,j=1,2,3)為各坐標分量;Fi為體力分量;p為流體均壓力。
對于穩(wěn)態(tài)不可壓縮的流體流動,上述方程組可簡化為:
連續(xù)性方程
(4)
動量方程
(5)

2.1.2 湍流模型
當前用于氣固耦合連續(xù)均相流場變化的數學模型有:基于Euler坐標系的連續(xù)介質模型、基于Lagrange坐標系的顆粒軌道模型和基于Euler-Lagrange坐標系的顆粒軌道模型[8]。本案采用基于Euler-Lagrange方法[9-10]的全隱性湍流模型,其只考慮流體對粒子的作用,不考慮粒子對流體的影響[11],將氣固雙相流視為連續(xù)相來求解N-S方程。計算過程中,將模型分為固定域和旋轉域導入CFX中,固定域、旋轉域用interface面連接、合并作為統(tǒng)一流場進行處理,氣固耦合連續(xù)相采用標準的SST湍流模型。
SST模型綜合了k-ω模型在近壁區(qū)計算的優(yōu)點和標準k-ε模型在遠壁區(qū)計算的優(yōu)點,是將k-ω模型和標準k-ε模型同乘以一個混合函數再相加而得到。流體分布在近壁區(qū)時模型函數的值等于1,相當于在近壁區(qū)采用的是k-ω模型。流體分布在遠壁區(qū)時模型混合函數的值為0,相當于自動按標準k-ε模型計算。其傳輸行為可由包含限制數的渦流黏度方程[7]求得
(6)

(7)
(8)
式中:a1為各向異性張量;k為湍動能;w為旋渦狀態(tài)量;S為應變率的一個定估算值;β′,σω2為符合k-ω模型的常量;ω為角速度;y為到最近壁面的距離。
2.2 模型建立
試驗臺箱體由被試軸承、密封圈、徑向推桿、軸向頂桿、軸承支架等組成(圖2)。被試軸承外徑約為350 mm,在建立幾何模型時統(tǒng)一簡化為直徑350 mm的圓柱;設計試驗臺箱體為直徑750 mm,長750 mm的圓柱;傳動軸簡化為直徑150 mm,長200 mm的圓柱;其他部分影響較小,可以忽略。為方便模擬,現做如下約定:

1—軸承支架;2—被試軸承;3—傳動帶;4—陪試軸承;5—電動機
(1)內流場的空氣為理想空氣,并在仿真過程中不可壓縮;
(2)箱體嚴格密封,內流場是空氣和固體粉塵的耦合相,相之間無物質傳遞;
(3)粉塵顆粒為標準形狀,其粒徑均勻,在10~200 μm之間,平均粒徑為70 μm;
(4)粉塵顆粒運動過程中無形變和碰撞,屬性設定為二氧化硅,密度為2 300 kg/m3;
(5)氣固雙相流具有相同的溫度場。
利用Pro/E分別建立固定域的軸承試驗臺密封箱和旋轉域的風扇三維幾何模型(圖3)。把生成的幾何體存為通用格式IGS導入網格劃分軟件ICEM,修正幾何體建立拓撲結構,指定各部分名稱進行以四面體為主的非結構體網格劃分,并對圓弧邊緣的三棱柱和局部特征進行細化(圖4)。固定域部分大約生成30萬個網格,旋轉域部分大約生成15萬個網格,保存體網格為ANSYS CFX格式,導入CFX進行邊界條件和模擬特性設定,見表1。

圖3 軸承試驗臺3D幾何模型

圖4 網格內部細節(jié)及整體模型

表1 模擬特性
3 仿真分析
為便于表述,對分析默認條件進行如下約定:基于高鐵軸承的轉速及尺寸,設定風扇轉速為60 r/s,順時針旋轉;風扇周徑尺寸為130 mm,扇葉數為3個,扇葉寬為30 mm、葉面傾角為30°;建立流體模型時,軸承端面所處的平面是Z=-400 mm。
3.1 風扇與被測軸承的距離
風扇與被測軸承端面相距250 mm時(圖5),風扇前后形成較大的壓強差,迫使吹出的部分粉塵流體回流來緩解壓強差,在風扇背部與扇葉圓周平面30°夾角方向形成很強的渦旋中心,在軸承迎風端面60°夾角方向形成次渦旋中心,在軸承附近只形成速度微弱的回流和繞流。其原因是風扇與壁面之間沒有足夠的間距,大部分回流被阻擋,只有扇葉附近小范圍的粉塵流體回流到位且速度很急,其他流體在回流過程中遇壁面折回形成另一波次渦旋中心,風扇前后的壓強差并沒有得到有效緩解,負壓繼續(xù)致使更大面積的粉塵流體回流,大部分粉塵流體并沒有運動到軸承附近就已經回流。壓強差造成的回流現象嚴重影響速度的分布,故回流空間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增大風扇與試驗箱壁面的距離,留出足夠的回流空間,可緩解上述現象,同時增大風扇與試驗箱壁面的距離也可有效減小風扇吹出流體運動到被測軸承的行程,使其在回流過程中就能到達被測軸承。

圖5 風扇與軸承間距250 mm時yz平面粉塵速度分布
風扇與被測軸承端面相距150 mm時(圖6),同樣由于壓強差的影響迫使部分流體回流,在被測軸承端面60°夾角方向形成渦旋中心,但此時回流粉塵已基本可以順利回到風扇背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風扇前后的壓強差,并有一部分流體在回流過程中順利到達軸承端面。這說明加大風扇和壁面的距離能有效增大回流空間,減小粉塵到被測軸承端面的行程。對比發(fā)現,留出的回流空間越充分,風扇吹出流體的向前性越好。但同時大部分流體被軸承端面阻擋折回,在被測軸承其他面并沒有出現理想的粉塵速度流場,且風扇與被測軸承端面相距越近擋回的現象越嚴重。為使理想的粉塵流體到達被測軸承背部,風扇吹出的流體需避開軸承端面的阻擋。通過減小其距離來緩解回流空間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在適當減小其間距的基礎上,可考慮增加風扇的數目并改變布局。

圖6 風扇與軸承間距150 mm時yz平面粉塵速度分布
3.2 風扇數目及布局
布置風扇時應盡可能留足回流空間,不能離壁面太近。考慮到箱體有限的空間、回流空間及風扇的尺寸,不宜在傳動軸側布置風扇。
2臺風扇在軸承對面150 mm處上下相距420 mm時的粉塵流場速度分布如圖7所示,雖然在這種狀況下粉塵以較理想的速度到達軸承,但Z=-400 mm平面內形成明顯的渦旋,粉塵繞軸向旋轉不理想,不符合實際軸承的流場分布,且2臺風扇相互干涉嚴重,風扇功效下降,同時軸承周圍粉塵速度分布不均,靠近風扇側遠大于其他側的粉塵速度分布,故此方案不可取。
3臺風扇在軸承對面150 mm處Φ420 mm圓周上互為120°布置時,粉塵流場速度分布情況如圖8、圖9所示。此時,軸承周圍徑向和軸向的粉塵速度及分布均比較理想,在Z=-400 mm的平面內整體形成了理想的繞軸向旋轉的狀態(tài),風扇彼此干涉不明顯,并且流場的整體速度大于圖7,風扇整體功效提高。圖8中被測軸承背風面也有理想的渦流及速度,軸承四周粉塵均布運動,沒有出現明顯相互干涉的渦旋。由圖10可知,在此方案下軸承各面的粉塵運動以繞軸向的旋轉為主,也有來自軸向、徑向及其他方向的撞擊,撞擊之后的粉塵顆粒沿軸承面滑移。分析圖11可知,試驗臺壁面的粉塵運動以繞軸向旋轉為主,也有平行于壁面其他方向的滑移,離風扇最近的3點有來自粉塵顆粒的碰撞,且此處的粉塵顆粒運動速度最快。試驗臺壁面磨損主要來自磨蝕,以繞軸向的旋轉磨蝕為主,也有來自其他方向的滑移磨蝕。

圖7 2臺風扇上下對稱布置時Z=-400 mm平面內粉塵速度分布

圖8 3臺風扇互呈120°布置時yz平面粉塵速度分布圖

圖9 3臺風扇互呈120°布置時Z=-400 mm平面內粉塵速度分布

圖10 3臺風扇互呈120°布置時軸承面粉塵速度分布圖

圖11 3臺風扇呈120°布置試驗臺壁粉塵速度分布
4 結論
(1)實現試驗臺內循環(huán)狀態(tài)相對理想的方案是,3臺風扇互呈120°分布在軸承對面Φ420 mm的圓周上,與軸承相距150 mm。
(2)此方案下,軸承各面流場有較好的速度,試驗臺內流場粉塵顆粒運動以繞軸向旋轉為主,并有軸向、徑向和其他方向的粉塵撞擊和滑移;軸承各面磨損以磨蝕為主,其中磨蝕來自繞軸向的旋轉磨蝕,軸向、徑向及其他方向的滑移磨蝕。試驗臺壁面的磨損主要以繞軸向的旋轉磨蝕為主,也有來自其他方向的滑移磨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