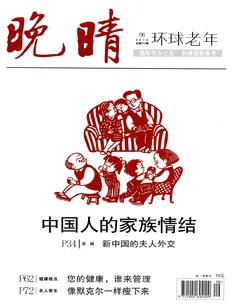中國人60年遷徙熱點地帶
楊佳瑜+劉超玲

南下干部遷徙的現實影響力
在解放戰爭后期和建國初期,四個老革命區的省份——山東、河南、河北、山西,被要求抽調一部分干部南下,接管南方的城鄉。5.3萬名的人數底限也在一次文件中被規定,這是按500個縣計算出來的數字。其中的1.5萬名,由山東包攬。
5.3萬名在后來的發展中演變為十萬名。這些從從北方而來的干部隨后在當地落地生根,編織了南方大部分縣區的基層政權。而現在山東籍高官數量較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這次南下。
當時,山東干部中近乎一半前往浙江。當時劃分的浙江11個地區,其中十個的第一任地、縣級主要領導基本都由南下干部擔任,現在仍有“8000山東干部接管浙江”的說法。而另一部分前往上海的山東人,多為財經口出身,則把上海變成后來支撐新中央政權的最大財源。當時的領隊,是此后廣為人知的經濟學家顧準,他有一個學生叫吳敬璉。
劉向一從山東南下上海,他的孩子在這里出生,名叫劉長樂。劉長樂現在是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另一位南下干部馬陳術則到了海南,他的兒子后來創辦了一個年營業額400億元的公司,名叫騰訊。
新一撥遷徙的終點:前蘇聯援建項目
建國后,為了平衡地區之間資源分布的不均,中央開始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的跨區域遷徙——1954年,中國大陸的人口流動量達到2200萬。于是,隨著北大荒的開墾、對邊疆的支援和各大工業基地建設的展開,人口從城市流向了農村。
主持人李詠、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和導演陸川,他們的父親都在此背景下來到新疆,成為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員。
同時期,“北大荒”開始耕作,迅速成為中國農墾板塊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國土的最南邊海南,則因為農墾部隊的前往,產生了后來長期保持的一島三方行政體制——海南行政區、黎族苗族自治州和海南農墾,這種體系一直持續到1988年海南建省。至今,包括黑龍江、海南等23個墾區仍被保留。
這一次人潮流動的另一個背景,是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 —1957年)的實施。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在全國各地開展,一部分人員被調配至這些工業基地。于是,鞍山、洛陽、克拉瑪依、大慶、蘭州等移民城市應運而生。
因為工業的帶動,這些移民城市在當時發展迅速,也吸引了很多人。出生于遼寧營口的單田芳,在1955年隨一個演出團到了鞍山。那時他寂寂無名,而鞍山已經有了五六十位曲藝家,正是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中,磨煉出了一代評書大師。
現在蘭州街道上的“某某巷”,比如貢元巷、箭道巷、五福巷,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北方的城市多以里、道、弄、路、胡同命名,而巷的說法,實質上是來自南方的移民們留下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別于由城市前往邊疆、農村的2000萬流動人潮,有一小部分人群逆向流動,比如從上海遷往北京。
這其實也是一種“支援”——當時的首都也在建設,但服務業并沒有相應跟上,任務落到了上海。從上海遷來208人、21家服裝店,其中的七家和中央辦公廳附屬服裝加工廠合并組建成紅都,提供了當時及后來領導人的衣著。
運來八萬工人就成了一座城市
1964年,上海人王家駒帶著兒子王小帥前往貴陽。這是建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三線建設。王小帥執導的紀錄片《三線人家》,便是想為父輩留證。
上個世紀60年代,中央出于備戰考慮,將工業基地遷往“三線”——即陜甘川云貴地區。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東林稱,1964—1980年中,一共有2052.68億元被投入到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和王家駒一起,400萬人充實了這些地方。
眾多西部城市在建設者手中“無中生有”,比如十堰和攀枝花。
十堰,早期不過是一個鎮,全鎮唯——家打鐵店就是它全部的工業基礎。后來鎮上來了上海人——上海汽車制造廠的三線援建職工;又來了東北人——從位于長春的第一汽車制造廠調來。他們組成了第二汽車制造廠也是現在央企東風汽車公司的前身,他們來到十堰后。才有了“東方底特律”。二汽的兩名普通技術員李嵐清和王兆國,后來進入了國務院。
1968年,胡錦濤、溫家寶走出校門,分別前往另外的三線重點地區——甘肅劉家峽和酒泉工地。
廣東成為遷出人口高地
最近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也就是“民工潮”。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經濟導向,自發遷徙。l《南方周末》報道說,中國4.2億的農村勞動力中,至少有1.6億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
也正是因為要面對如此多的流動人口,廣東、浙江等地出現了“新移民局”。
不過,據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分析,“經濟移民”已經發生了細微變化。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人口遷徙的重心已經北移——特別是浙江省的崛起,長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成為人口遷入的首個陣地。從廣東遷出的人口正在增加,以268.24%的高增長率居全國首位。
新的遷徙又在路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