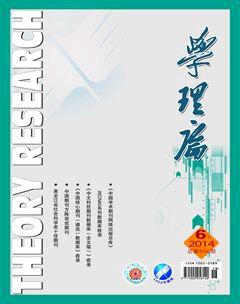對我國“沒收財產刑”的法律思考
韓晗
摘 要:我國刑法中規定了關于沒收財產的制度,該制度作為刑罰體系中的附加刑,已成為懲罰犯罪的一種重要方式。對于該制度的存廢之爭也從未中斷。筆者認為,首先,從刑罰的功能上講,沒收財產刑與罰金刑功能近似,可以實現相互替代;其次,沒收財產刑所沒收的是犯罪人合法所有財產,違背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憲法精神;再次,沒收財產刑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再者,沒收財產刑實質上不利于實現刑罰目的的功能,導致重刑化趨勢。因此,沒收財產刑應當被廢止。
關鍵詞:沒收財產;憲法;罪刑法定;重刑化;廢止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8-0073-02
沒收財產刑作為一種嚴厲的財產刑,在我國刑罰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1979年刑法頒布以來,就一直作為附加刑存在于刑罰體系當中。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沒收財產刑的適用對于打擊嚴重犯罪起到了積極作用。時至今日,沒收財產刑在司法實踐中的弊端也開始顯露,從刑罰的功能上講,沒收財產刑與罰金刑功能近似,可以實現相互替代;沒收財產刑所沒收的是犯罪人合法所有財產,違背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憲法精神;沒收財產刑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沒收財產刑實質上不利于實現刑罰目的的功能,導致重刑化趨勢。
一、沒收財產刑與罰金刑功能近似,罰金刑可以替代沒收財產刑
沒收財產刑是指將犯罪人所有財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強制無償地收歸國有的刑罰方法[1]312。而罰金刑的定義則是指人民法院判處犯罪分子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額金錢的刑罰方法[1]307。從兩者的定義來看,我們可以得出兩種刑罰所具有的一些共性:首先,兩種刑罰所針對的對象都是犯罪人的財產;其次,兩種刑罰都是作為附加刑在刑法中加以適用的;再者,兩者的基本出發點都是通過財產處罰使得犯罪人喪失繼續犯罪的物質基礎。從這些共性可以看出沒收財產刑與罰金刑在功能上都是通過對財產的處罰實現對犯罪人懲罰與報應。
基于對兩種刑罰方法共性的認識,既然兩者的功能如此近似,可以通過提高罰金的數額以及調整其適用范圍來實現對沒收財產刑的替代。
二、“沒收財產刑”存在的弊端
(一)沒收財產刑違背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憲法精神
沒收財產刑所沒收的財產是犯罪人的合法的私人財產。該刑的最大問題就是對于合法的私人財產的沒收。首當其沖的就是沒收合法財產的正當性問題,即是否能取得憲法支持。我國《憲法》第13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犯罪人雖然觸犯了刑法,侵害甚至是嚴重侵害了刑法所要保護的社會關系,但這并不能否認犯罪人的公民權,恰恰相反,對進入訴訟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而言,其公民權的保護應當受到格外重視,這也是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基于此種原因,犯罪人享有屬于個人的合法財產應當視為其基本的公民權利,理應得到法律的保護。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收財產刑與憲法精神相左。
(二)沒收合法財產無異于“財產連坐”
沒收犯罪人的合法財產實際上相當于一種“財產連坐”制度,即因為犯罪人的違法行為使其合法的財產權利受到牽連,而被沒收。這種財產連坐的思維已不適合現代法學發展的基本規律,正如同廢除古代連坐制度所體現的道理一樣,現代刑罰體系追求的是公平正義,實現的是懲惡揚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維護法律的權威。如果對于犯罪人的財產不加以嚴格區分就進行處罰,對犯罪人采取“一棒打死”的做法,那對其刑事責任的追究就顯得毫無意義,因為刑事責任是指“行為人實施違反刑法的行為后,所應承受的來自國家的責難”[1]269。因此,刑罰處罰針對的是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對其財產的處罰也要體現相對應的處罰程度就可以了,不能因為其違法的事實而剝奪其合法的權利。
(三)沒收財產刑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沒收財產刑并沒有明確提出所沒收財產的數量以及計量標準,這本身就不符合罪刑法定的明確性原則,而且這種規定的不明確性也往往會造成司法者在沒收數額以及計量標準上的解釋隨意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如若判處沒收犯罪人的全部合法財產,在此情形下該刑罰亦可被視為一種殘酷的、不均衡的刑罰,是不符合理性判斷要求的。因此,沒收財產刑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
(四)沒收財產刑導致了刑罰發展的“重刑化”傾向
沒收財產刑的一個弊端就是導致了刑罰發展的“重刑化”傾向。“重刑化”具體而言就是指“要有效預防和遏制犯罪,就必須制定嚴刑峻法,對犯罪廣泛地規定和適用重刑甚至死刑[2]。沒收財產刑的處罰方式是將犯罪人所有財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強制無償地收歸國有。就目前而言,我國司法實踐中,“沒收財產刑全部是附加適用,沒有獨立適用的分則的具體罪名的規定,因此它實際上是絕對的附加刑,只能附加于主刑適用,而不能獨立使用”[3]。這就意味著,在對犯罪人實行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處罰后,還要對其合法財產的一部分或全部進行沒收。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在我國目前刑法分則的規定中,規定沒收財產刑的有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共計12個罪名可適用;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涉及1個罪名;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涉及40個罪名;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涉及2個罪名;第五章“侵犯財產罪”,涉及6個罪名;第六章“擾亂公共秩序罪”,涉及6個罪名;第八章“貪污賄賂罪”,涉及4個罪名。也就是說,在刑法分則中,有7章共計71個罪名涉及了沒收財產刑的附加適用。這就意味著如果犯罪人觸犯了上述罪名,且被認定為罪行嚴重,那他的合法財產就有可能被沒收,再加之目前對于該刑的處罰數額和具體的計量標準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這就給司法者留下了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間。假若在實踐中不能夠很好地把握該刑的適用,那將極易造成刑罰適用的過重,呈現出“重刑化”的傾向,這種“重刑化”的傾向不僅不利于法治的發展,相反會削弱法律的權威。
然而,現代刑罰發展的趨勢是“刑罰的懲罰性程度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漸減弱,也就是刑罰越來越輕緩化”[1]286。沒收財產刑的適用顯然不符合這種趨勢的發展。
(五)沒收財產刑不利于刑罰目的的實現
沒收財產刑削弱了刑罰懲罰和預防犯罪的功能,在法經濟學中有一則經典案件可以給予我們啟示。在一段時期內一個地區的搶劫罪的犯罪率較高,當地的司法機關為此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對于搶劫罪的犯罪人一經抓獲便處以極重的刑罰。經過一段時間后,當地司法機關對該地區的搶劫罪的犯罪率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該地區的犯罪率呈現了下降趨勢,但惡性的搶劫罪案件則呈現了上升趨勢,搶劫罪一旦案發,被害人不是被殺就是重傷。司法機關對此進行了深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犯罪人在已知自己可能面臨的嚴重刑罰后,通過對被害人采取了殺人滅口的方式以降低自己的案發幾率。該案件恰恰符合了意大利學者貝卡利亞的觀點:“嚴峻的刑罰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為了擺脫對一次罪行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同樣的道理,如果犯罪人在案發前預計到自己的合法財產將會被沒收,在可能會面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犯罪人可能會更加肆無忌憚地從事犯罪活動以滿足現在的狀態或為逃避懲罰而進行其他犯罪。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收財產刑削弱了刑罰懲罰和預防犯罪的功能。
三、廢止“沒收財產刑”的法律意義
廢止“沒收財產刑”,更好地“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憲法意志,可以實現諸多法益,對于當前法治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一)有利于維護憲法權威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廢止沒收財產刑有利于實現以憲法為最高法律規范,完善以憲法為統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把國家各項事業和各項工作納入法制軌道,實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制度化、法制化。
(二)有利于人權保障
保障犯罪人的合法私人財產權一方面體現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法律價值,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人權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面,保障犯罪人的合法私人財產權并不意味著對犯罪人的姑息和縱容,恰恰相反,對犯罪人權利的保障能夠體現出法律的公平和正義,是一種高層次的人權保障方式。
(三)符合了刑罰發展的趨勢
“刑罰的輕緩化是融入刑法發展的主流,實現刑法現代化的需要。輕緩化刑法進化的世界潮流,也是刑法現代化核心內容”[4]。沒收財產刑的存在違背了這種趨勢,對刑罰理論和實務的發展都起到了阻礙作用。因而從優化刑罰體系,適應現代法學發展規律的角度上講,廢止沒收財產刑正好符合了這個規律。
(四)提高了犯罪人接受刑罰處罰的積極性,有利于刑罰功能的實現
保護了犯罪人的合法財產權益后,使得犯罪人有所“牽掛”,有助于促使其更加積極地接受刑罰懲罰,提高刑罰改造的效率。
(五)有利于犯罪人的“再造”
沒收了犯罪人的合法財產,那就意味著犯罪人回到了社會之后,面臨著“一無所有”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犯罪人重操舊業的幾率大大增加,那刑罰改造的價值將會大打折扣。如果保護了犯罪人的合法財產權益,犯罪人再次回到社會之后仍有一定的“資本”,其進行正常的社會活動也有了物質基礎,這將有利于其社會生活走上正軌,實現犯罪人的“再造”。
參考文獻:
[1]李潔.刑法學(上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2]游偉.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罰模式的選擇[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3(2):95.
[3]李潔.論一般沒收財產刑應予廢止[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3):97-98.
[4]黃華生.論刑罰輕緩化[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