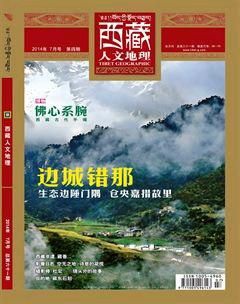藏東石刻
范久輝



昌都地區是西藏吐蕃時期石刻分布最多的地區。探尋這些石刻,似乎是對“唐蕃古道”沿途節點的考證,千年的時光早已讓古道的樣子模糊,但會說話的石頭還在傳遞著吐蕃時期藏東藝術的余溫。它們是漢、藏、印等藝術交流的典范,也是佛教在藏東地區弘傳的一個輝煌的見證。
在昌都地區的一些民間傳說中,文成公主當時進藏的路線有好幾條,而察雅縣的香堆鄉是這幾條路線的交匯點。如在民間傳說中,文成公主是從四川的德格縣進入西藏,經江達縣在貢覺縣的通夏寺短暫停留,在此地用琉璃瓦建了個拉康后,經拉妥鄉的達莫寺到達察雅縣的香堆鄉;另一個傳說是認為她是從云南進藏,經芒康縣的邦達鄉,刻下然堆村的達瓊大日如來造像后到達貢覺縣,后到達察雅縣的香堆鄉。
雖然傳說中的文成公主似乎具有“分身術”,不過這些進藏路線都應是唐蕃古道的藏東段,并與以后藏東段的“茶馬古道”暗合。在古時交通極度不發達的境況中,交通路線也相對不確定,不同方向的路線如蛛網糾結,在一個節點匯合后,再分散,這應是當時交通狀況的寫照。
在清時駐藏大臣的進藏路線中,香堆鄉也一直是個重要的驛站。康熙五十九年和乾隆五十六年,兩次用兵西藏皆取此道:“嶺高懸月小,澗窄受風長。樹樹留殘雪,人人怯早霜。預愁枯宿苦,猶念起行忙。已到乍丫地,何須說里塘。”清代文人黃沛翹在《西藏圖考》一書中留下如此詩句。
香堆的向康大殿
從察雅縣城出發,翻過小山坡,藏東南紅土地的脆弱與壯美一覽無余的展現在眼前。說它脆弱,一個細小的河流,就能把兩岸的山體沖刷出巨大的溝壑,從谷歌地圖看,應是一個永恒的傷痕;說它壯美,近處遠處山體在遠古的造山運動中,在地表深處熾熱巖漿作用下,層層不同色彩的石巖就此點綴在紅色的山體中,令人驚嘆。察雅縣到香堆鄉近百公里的路線中,都是在這種風光中穿越的。
香堆鄉坐落在一個平地上,相對于公路,平坦的它就是一個大平原了。幾千年的重要交通節點,現在因察雅縣縣城定址煙多鎮,變得寂靜了很多。街上,懶洋洋曬太陽的狗比行人還多。香堆鄉政府上方的那一片壯觀到近乎輝煌的廢墟是最容易吸引眼球的建筑。高地之上,廟宇紫紅色土質的框架尚在,雖是斷壁殘垣,但嵯峨多姿,嚴整富麗。遠遠地透過狹長的方窗洞,可見藍天上蟬翼般的薄云。廢墟的背后稍高處仍是廢墟,錯落有序;再遠處,是渾圓的紫紅色山,與全部的廢墟渾然一色一體,壯烈凄慘。
著名的香堆向康大殿位于香堆鄉的中心,其四周的圍墻是一個個的商店,信徒們在轉經同時,也能在這些商店中買到針頭線腦、青菜蘿卜干、干肉等各式商品。8世紀中葉,“七覺士”之一的毗盧遮那被迫流放到康區時,曾在察雅窩額的吐杰降欽寺中譯經。史書中記述的“窩額”吐杰降欽寺是指察雅的香堆殿堂。它是座坐西向東的藏式二層平頂樓。主殿面寬7間,進深5間,中央由2根長柱托起天窗,以便采光、透氣。察雅人叫彌勒佛為“向巴”,向康大殿的主殿內自然主供彌勒佛與八大菩薩。主殿的形式是藏族早期典型的回形走廊式殿堂。信徒在此進行供養時,僧人會在彌勒佛前吹響大海螺。海螺聲渾厚低沉,與昏暗的充滿酥油味道的殿堂一起,構成立體的光怪陸離的虔誠畫面。雖說是吐蕃時期彌勒佛,但在近千年信徒們不斷涂金彩繪下,與大昭寺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一樣,已然沒有吐蕃的韻味了。主殿前面的經堂是1658年擴建而成的,其四壁與彌勒佛的回形走廊上的壁畫也應是當時所繪。文化大革命時,主殿被改成香堆鄉的糧食倉庫,壁畫因此而相對保存良好。
向康大殿的南殿也是一個重要的朝圣場所,里面供奉著大日如來,據說也是吐蕃時期的遺存。大日如來頭面為倒三角形,瘦削、高發髻,只是經重繪已難見其原始氣象,不過還能依稀看到他莊嚴肅穆,悲憫眾生的神情。一個與我同時在殿中朝覲的信徒向我介紹,這個是文成公主進藏時留下的一塊石頭自然生長而成的。文成公主安全到達拉薩后,它就自顯于香堆農田上,護佑察雅縣的蕓蕓眾生。
南殿四周貼有影塑,內容有文成公主進藏出行圖,佛傳故事等內容。其中在佛傳故事的內容里,塑出吐蕃時期的贊普形象,這是參觀南殿另一個不容錯過的精彩之處。
出得大殿大門,大門兩側二個石鼓形的石碑引起我的好奇,那是用廢棄的石磨改制而成。上面刻著漢字,依稀可見是一個個漢族名字。據說是清代末期,趙爾豐在此進行“改土歸流”時,所刻其部下的名字。藏族的寺院門前,用刻滿漢族人名字的石碑做“守衛”,向康大殿是個特例吧。
馬麗華筆下的藏族“令狐沖”與他的角克寺
香堆鄉境內另一個著名的吐蕃時期的遺址——察雅仁達丹瑪摩崖造像及石刻,它是藏東昌都唯一能確定為吐蕃時代的造像銘文,對于研究吐蕃時期昌都地區的政治、宗教、法律、文化及書法雕刻藝術均有重要的意義。該石刻距香堆鄉約三十公里,近年來,國家斥重資修通了到那里的公路,讓想參觀的人免去徒步、騎馬之苦了。
從香堆到角克寺的中點上,有一個曾經是藏東乃至整個西藏最大的尼姑寺角克寺,其最輝煌的時候有近千名尼姑。無獨有偶,寺院的活佛也叫向巴,他的名字在康區藏語里的意思就是彌勒佛。他被認證為活佛還有一段趣聞:向巴原名叫“小羅松”,在年僅十五歲時,已經在昌都地區小有名氣。他的唐卡畫得十分好,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展出過,當時《拉薩晚報》《昌都青年報》等報刊還刊出過他的作品。他的父親羅松西繞是西藏十分著名的唐卡畫家,人民大會堂西藏廳的唐卡壁畫《八思巴覲見忽必烈》就出自其手,還獲得過“珠峰”美術大獎。“小羅松”本名叫平措,別人叫他“小羅松”,就是因為受到他父親影響的緣故。如果不是被認定為角克活佛的轉世,小羅松人生軌跡似乎十分明朗,那就是在他父親的指導下,一步一步走向唐卡藝術的高峰。
雖然在藏族傳統上,活佛的社會地位要比常人高出不少,可是當洛嘉活佛把“小羅松”是角克活佛轉世的消息告訴他父母,并請已十五歲的小羅松到角克寺“座床”及學經時,他父親羅松西繞與母親卻起了很大分歧。父親可能更希望小羅松繼續跟他學下去,繼承他的衣缽,加之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堅決反對小羅松進寺院成為活佛。而母親,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在千百年來形成的宗教觀念影響下,自然希望自己的兒子是轉世活佛。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僵持之下,做出一個十分民主的決定,就是讓涉世未深的“小羅松”自己選擇。
讓十五歲的毛頭小子自定終生,這有點勉為其難。小羅松最后懵懵懂懂地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選擇進寺院當活佛。于是未來可能的唐卡大師成了角克喇嘛,他的名字也從普通的“平措”變成了“角克·向巴丹增”,人們對他的稱謂也從“小羅松”變成了“向巴活佛”或“角克仁波切”。當問及二十五年前的選擇時,已到中年的向巴活佛沒有片刻的思考,脫口說洛嘉活佛對他很好,對他家人也很好。
1998年,馬麗華老師來采訪他的父親羅松西繞,向巴活佛當時也在現場,馬麗華見到向巴的時候,為他帥氣所傾服,戲稱他為藏族的“令孤沖”。大畫家羅松西繞在角克寺重建時,畫了大批精美的壁畫,因是為兒子所繪,自然精彩絕倫。壁畫主要繪于角克寺大殿的二樓,其風格介于藏式傳統壁畫與安多強巴“月份牌”之間。
角克寺聳立于半山上,在它兩側,層層疊疊、密密麻麻沿山勢修筑了無數灰色的小屋。遠處看就像一朵蓮花,角克寺位于最上端,是蓮花的花蕊;而白色的屋就是那層層疊疊的蓮花的花瓣,壯觀而又帶著一絲神圣。白色的蓮花花瓣小房,看上去美觀,可在里面連人身都無法站直。寺院另一個精彩之處,就是保存著一批清代大型的制作擦擦的模具。以立體模具為主,最大的高有四十余厘米,重達五十余斤,很多大寺院如今也很少能保存有這樣精美且數量眾多的模具了。
仁達石刻,文明交匯與融合的拐點
仁達丹瑪摩崖造像位于角克寺上方約十五公里的丹瑪山崖上。由于深藏于遠僻之處,常人難以到達,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被發現之前,一直默默無言。但十分可貴的是,藏漢文史書都曾提到吐蕃時代的這一珍貴遺物。《西藏王統記》載:“爾時,漢女公主同吐蕃使臣已行到鄧馬(丹瑪)巖。曾于巖石上刻彌勒菩薩像一尊,高約七肘,《普賢行愿品》兩部”。《賢者喜宴》說:“之后,公主和主仆在康地等候噶爾時,將《普賢行愿品》卷首及八十幅的佛像刻于巖石上”。從石刻的銘文上看,以上記載與實際勒刻年代有誤,但有佛像和《普賢行愿品》等石刻藝術則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晚期漢文史書也提到這一遺跡,《西藏圖考》記:“仙女洞在官角(貢覺)路旁,千仞石壁中露窗隔形,其下依巖作碉房一間,內有石碣,僅存‘大番國三漢字,余模糊不能讀”。
向巴活佛對仁達石刻的介紹比生硬的資料生動多了。他說,當年文成公主一行跋山涉水,取道察雅地方前往拉薩,曾在風光秀麗的仁達稍事休息,公主喜歡這個地方,遂以非凡的造化與功德,在丹瑪懸崖上顯現出大日如來佛和八大隨弟子像。同時又運用法力,如同西天大圣孫行者那樣,拔幾根頭發往山上一吹,頃刻間在原本光禿的山脊上長出大片森林。當地百姓即采伐森林,按公主之愿望修建了仁達寺,用以供養佛像。
如向巴活佛所言,雖然仁達石刻周邊都是喀斯特地貌的大石山,然而鬼使神差似的在石頭上長滿了綠油油挺拔的云杉。石刻刻在兩條小溪的交匯處,從左側的河流上走,可以到昌都縣城,從右側流往前走,就是貢覺縣城了,在古時,此處應是一個交通要道。在石刻的外面,建有如北京四合院格局的小寺院仁達寺。仁達寺原為角克寺的分寺,其所在的山叫愛邦卡,為當地的大神山,據說在龍年時,轉一圈神山的功德與轉遙遠的岡仁波齊神山的功德一致。不知這里是因石刻而成為神山,還是因神山而鑿刻石刻。
石刻刻在一個相對平整的石壁上,為高浮雕的大日如來與八大弟子。主尊大日如來著三葉高冠,冠葉較為緊湊、圓潤,胸臂、腰腹、四肢比例合度,坐姿穩定,造像讓人感愛到瑜伽禪定者肌體的內在力量,有印度笈多及波羅早期的佛造像風格成分,這種內聚力度是后世造像難以模仿的。蓮座為早期仰覆蓮座,葉蓮寬大,覆蓮僅作為蓮府底邊,以蓮莖支撐,底下兩側為對獅,造型稚拙,極像兩只獅面小狗。背龕為桃尖形,整個主尊造像置于框式龕內。框式龕最上方為漢式金瓦屋檐,檐下垂有用寶石串連而起的寶幔。兩側分列的八大菩薩完全是東印度波羅樣式,都是三葉冠,上身裸露,佩有項鏈、臂訓和瓔珞;下身著彩條褲子,或舒坐,或半跏趺座,分成兩排,豎直的分部于大日如來兩側。其上方各有一與敦煌壁畫中如出一轍的飛天,她們隱于云團中,一個雙手持鈸,一個手中的寶瓶正向下灑水。
僧人見我是漢族,又十分關注石刻的內容,于是十分神秘的帶著我來到二樓,然后打開對著石刻的窗子,指著石刻上的飛天,告訴我飛天邊上有漢字,并要求我告訴他漢字的內容。原來兩飛天邊的漢字是今年他們為石刻上彩時新發現的。我勉強而為之,卻只能分辨出右邊持鈸飛天的銘文“吐蕃僧法歲為父母”,而持寶瓶飛天的字體像個日本字,實在是分辨不出來。
經藏族學者土呷的多次考證,仁達石刻的題記銘文涉及刻經興佛、僧人參政、唐蕃和好、贊普功業、眾生安樂以及號召百姓皈依佛法、保護佛法等內容。漢文部分除新發現的“吐蕃僧法歲為父母”極少數文字外,大多已漫漶不清。而藏文95%都清楚,全文翻譯如下:圣教之意,乃一切眾生皆有識念佛性之心。此心非親教師及神所賜,非父母所生,無有起始,原本存在,無有終了,雖死不滅。此心若廣行善事,利益眾生,正法加持,善修自心,可證得佛果與菩提薩,便能解脫于生老病死,獲無上之福;若善惡間雜,則往生于天上人間;多行罪惡與不善,則入惡界有情地獄,輪回于痛苦之中。故此心處于無上菩提之下,亦有情于地獄之上。若享佛法之甘露,方可入解脫一切痛苦之地,獲永久之幸福。故眾生珍愛佛法而不得拋棄。總之,對于自己與他人之事的長遠利益,則向親教師討教,并閱讀佛法經典,便能領悟(既為《普賢行愿品》卷首)。
猴年夏,贊普赤德松贊時,宣布比丘參加政教大詔令,賜給金以下告身,王妃琛莎萊莫贊等,眾君民入解脫之道。詔令比丘闡卡云丹及洛頓當,大倫尚沒廬赤蘇昂夏、內倫 倫赤孫新多贊等參政。初與唐會盟時,親教師郭益西央、比丘達洛添德、格朗嘎寧波央等為愿贊普之功德與眾生之福澤,書此佛像與禱文。安居總執事為窩額比丘朗卻熱、色桑布貝等;工頭為比丘西舍、比丘 松巴辛和恩當艾等;勒石者為烏色涅哲夏及雪拉公、頓瑪崗和漢人黃崩增父子、華豪景等。日后對此贊同者,也同獲福澤。
郭益西央在玉、隆、蚌、勒、堡烏等地亦為等者為比丘仁多吉。
若對此佛像及誓言頂禮供養者,無論祈愿,何事皆可如愿,后世也往生于天界;若惡語戲罵,即得疾病等諸惡果,永墜惡途;法律也對反佛者,從其祖先親屬起施行,故無論任何人均不得詈罵譏諷!
從銘文上我們可以明確石刻的鑿刻時間為赤德松贊時的“猴年夏”。赤德松贊在位時間為798~815年,其間只有一個猴年,即804年。而文成公主進藏距造像的年代一百五十余年。幾乎可以確定的說,公主與這造像及香堆鄉的向康大殿本身原本沒有關系,然而,眾多藏漢文史及民間傳說也并非空穴來風,藏東漢藏之間的文化交往由于公主入藏而得以加強,漢地敦煌等地的造像風格通過公主入藏而進入康區腹地。
就如仁達石刻所體現的,漢藏銘文,漢式金瓦頂,敦煌飛天,印度造像,它們完美的結合在一起,表明9世紀初漢藏藝術的相互影響已蔚為壯觀,漢人也參與到印度波羅樣式的造像中。也說明了新興的吐蕃王國在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以其雪域高原厚實的胸懷吸收周邊地區的文化發展自己。從這點上看,分布于藏東的眾多吐蕃時期石刻是為當時多文化交匯與融合的見證,說是西藏藝術發展史上的一個精彩的閃光點,我想并不為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