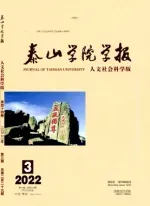早年主題的回旋與變奏:試論穆旦詩作的晚期風格
陳齊樂,陳 彥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234)
穆旦晚期詩作在詩情表達上發生很大轉變,正如穆旦昔日校友、同為“聯大”詩人的鄭敏所察覺的,“一個能愛,能恨,能詛咒而又常自責的敏感的心靈在晚期的作品里顯得凄涼而馴順了”。對此,有論者表達“贊美之后的失望”;亦有研究者認為,正是通過對自我感性體驗的真實表達,詩人才能夠擺脫意識形態話語對彼時絕大部分漢語詩歌寫作的箝制,所謂在晚年變得“凄涼而馴順”的地方,“正是穆旦的現代性所在——只依據個我的內向性原則行事:生活‘在過去和未來兩大黑暗間’,不以廉價的關于未來的許諾撫慰受傷的生命。”
然而,問題尚有值得探討之處:穆旦晚期寫作確實發生很大變化,這不僅表現在詩情上,一位以寫“自我分裂”與“自我駁難”而見長的現代主義詩人似乎回歸了浪漫詩風的抒情性表達;而且,我們不能不注意到,這些抒情性表達指向的是早年寫作不斷復現的主題,雖然此時已經歷了一系列變化——早年主題的回旋與變奏,確實構成穆旦晚期詩作特別突出、卻為研究者忽略不察的現象。“回旋”與“變奏”原本都是音樂術語。回旋曲,是指由相同的主部和幾個不同的插部交替出現而構成的樂曲;變奏曲,則是由主題及其一系列變化反復、并按照統一的藝術構思而組成的樂曲。
穆旦晚期詩作縈繞于一些相對固定的情緒體驗,雖然這些詩作很大可能并非寫于一時、一地,亦非出于有意識的構思、布局,但是文本間確實形成一種交互指涉的關系;而且,在晚期存留的不多詩作中,詩人似乎并非不經心地回旋于早年寫作的題材或經驗,但是這些晚期詩作已經對早期題材進行了特定而豐富的變奏。本文將借用“回旋”與“變奏”概念,嘗試對穆旦晚期詩作一些新的探討與檢視,以期能夠對穆旦晚期詩作獲得更具總體性的理解與認識。
一、回旋:作為主部的“智慧之歌”
穆旦晚期存留的詩作一共有二十九首。進入晚年,詩人確實成為那一類擅于在相同主部與不同插部之間交替往復的作曲家。《智慧之歌》的抒情主體表明自己“已走到幻想底的盡頭”,在這片“落葉飄零的樹林”里枯黃地堆積著三種“歡喜”:青春的愛情,喧騰的友誼,迷人的理想;現在,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還在,并且以它的苦汁澆灌了“一棵智慧之樹不凋”。可以看到,“智慧之歌”關于幻想失落的主部縈繞著穆旦的晚期詩作,在《妖女的歌》、《愛情》、《友誼》、《理想》、《沉沒》、《好夢》等不同插部之間形成一種交替往復的關系,以強化苦澀的“智慧之歌”。
插部1、夢/幻想:我們已無法推測晚年穆旦到底寫過多少詩,而他的詩的復蘇又具體出現于何時。假設我們可以將《妖女的歌》看作其詩歌寫作復蘇的訊號,那么它確實是最有意義的一個表征。穆旦深刻意識到自己是屬于那一類受到招引而迷失的“失蹤者”行列,然而對已知未知的崇山峻嶺的翻越并沒有開啟廣闊的時間與空間,相反是“喪失”成為了幸福、是腳步留下了一片野火,而這一切都源于“愛情和夢想”的招引、對“泥土仍將歸于泥土”的深切領悟,正如“所有偉大的寫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對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創造力戰勝時間的希冀”。于是,“她醒來看見明朗的世界,/但那荒誕的夢釘住了我”。(《“我”形成》)夢/幻想、理想成為穆旦晚期詩作反復出現的主題,并形象化為“一片落葉凋零的樹林”——“我已走到了幻想的盡頭”——這里,“每一片葉子標記著一種歡喜”。(《智慧之歌》)
插部2、愛情:在《智慧之歌》中,抒情主體對凋零的“愛情”、“友誼”與“理想”的感知還是一種比較抽象的認識,到了《愛情》、《友誼》、《理想》中則分別擴展對此三者的認識。在老年詩人的體驗中,愛情已經失去其熱情、詩意的特質,早年在《詩八首》中所呈現的對愛情本質的形而上凝思被冷峭的懷疑與批判所取代。曾經是渴望,“風暴,遠路,寂寞的夜晚,/丟失,記憶,永續的時間,/所有科學不能祛除的恐懼/讓我在你底懷抱里得到安憩——”(《詩八首》)如今是冷峻,“愛情是個快破產的企業,/假如為了維護自己的信譽;/它雇傭的是些美麗的謊,/向頭腦去推銷它的威力。”(《愛情》)曾經是諒解,“再沒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然在我們間定型”(《詩八首》,如今是披露,“別看忠誠包圍著笑容,/行動的手卻悄悄地提取存款。”
插部3、友誼:青年時代,穆旦在詩作中幾乎沒有觸及過“友誼”的主題,詩人幾乎完全置身于一個公共世界中,承受歷史的全部壓力,而抒寫“自我的分裂”與“自我的駁難”,至于作為其心靈宿地的內部空間則是由“愛情”這一親密關系所構建的。但是,在其晚期詩作中,“友誼”成為苦澀的“智慧之歌”中反復交替的插部。值得注意的是,“愛情”帶給抒情主體的只是茫然的消逝感與冷峻的幻滅感,“友誼”帶給詩人的則要溫和、并且重要得多,甚至取代最具私密性的“愛情”關系,成為抒情主體構建其內部空間的重要維度。詩人寫到,死亡已經從我的生活中帶走了許多心愛的人,以致“我的小屋被撤去了藩籬,/越來越卷入怒號的風中”,“但它依舊微笑地存在,雖然殘破了,接近于塌毀,/朋友,趁這里還燒著一點火,且讓我們暖暖地聚會。”(《老年的夢囈》)
可以看到,“友誼”對于抒情主體來說是庇護的“藩籬”,雖然死亡擊打它、狂風搖晃它,但是只要面向友誼敞開,有友誼的信物存在,那逝去的就依然與“我”同在。青年時代,通過“愛情”主體的書寫,詩人審視主體間不可跨越的距離;晚期詩作中,在歷史壓力下極度蜷縮的抒情主體反而在最為內在的層面敞開了,“受到書信和共感的細致的雕塑,/擺在老年底窗口,不僅點綴寂寞,/而且像明鏡般反映窗外的世界,/使那粗糙的世界顯得如此柔和。”(《友誼》)“友誼”構建了一處隱秘而內在的心靈宿地;但是,也正是在此內在而親切的私人關系,“死亡”化身為人形,直接進入與詩人的緊密聯系中,“你永遠關閉了,不管多珍貴的記憶;……永遠關閉了,我再也無法跨進一步/到這冰冷的石門后漫步和休憩”。(《友誼》)
插部4、理想:在《理想》中,詩人對《智慧之歌》中的主題進行反向的強化,之前詩人寫到,“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終于成為笑談”。到了《理想》中,詩人幾乎是以一種奮起的反抗,去抵擋理想有可能變為笑談的虛無感。詩人反復抒發“理想”之于存在的重要性,同時也表明“理想”背后現實的反諷,但是抒情主體卻自有他的確信:“別管的多少人為她獻身,/我們的智慧終于來自于疑問。”(《理想》)青年時代,詩人坦言“我曾經迷誤在自然底夢中”(《自然底夢》),并且認為自己是“從幻想底航線卸下的乘客,/永遠走上了錯誤的一站”(《幻想底乘客》)。在此后的幻滅、希望、再幻滅的自我尋索中,詩人把肉身性的個體自我確立為存在的基石,大聲宣告“我歌頌肉體,因為它是巖石/在我們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島嶼”(《我歌頌肉體》)。但是,在晚期詩作中,已經被“死亡”縈繞圍困的詩人重新登上幻想的航程,“‘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或者和蛟龍在海里翻騰,/凝神的山巒也時常邀請我/到它那遼闊的靜穆里做夢。’”(《聽說我老了》)——這首深心曠野中的真正的自我之歌已經具有與青年時代完全不同的情調。曾經“我底的身體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過林木的嘆息,早晨底顏色,/當太陽染給我剎那的年輕”(《自然底夢》),現在詩人則在自然之夢中呈現出莊嚴、高邁與嚴峻,正如一位真正的老年的勇者。
插部5、現實:于是,一位真正的老年的勇者也必然遭遇更大的困苦。在《沉沒》與《好夢》中,“智慧之歌”的幻滅的痛苦以更為沉痛而激越的筆調被抒發,并且在“死亡”主題的迫近下被強化,“愛憎、情誼、職位、蛛網的勞作,/都曾使我堅強地生活于其中,/而這一切之搭造了死亡之宮”(《沉沒》)。詩人大聲呼救,“我能拋出什么信息到它的窗外?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現在’?”(《沉沒》)詩人不再能夠像青年時代那樣,宣稱“因為我們已是被圍的一群,/我們消失,乃由一片‘無人地帶’”(《被圍者》);相反,因為“死亡”終結了所有的可能性,老年詩人不得不帶著激奮抗辯現實,并且大聲宣告“讓我們哭泣好夢不長”。(《好夢》)這種強烈的親密情感具有一種修辭上的震撼力,詩人不僅沒有變得“凄涼而馴順”,反而顯得“強大并且嚴峻”。
二、變奏:“原野的道路還一望無際”
在穆旦晚期寫作中還有一種富有意味的現象,即詩人不斷復寫早年寫作的題材,甚至有前后期同題詩作的現象。經歷過漫長的生命歷程,同樣的題材在詩歌表達中形成既有對應性、又有對立性的變奏。
變奏1、春:穆旦有過三首以春天為題或者以春天為題材的詩作,分別是作于1942年1月的《春底降臨》、1942年2月的《春》、1976年5月的《春》。前兩首詩的時間相近,但是趣旨卻大相徑庭,這和詩人的心境有很大的關系。作于當年1月的《春底降臨》表現的是一種從嚴酷的冬天中解放出來的欣喜之情。春天在這首詩中象征著不可阻擋的希望和未來——“墳墓里再不是牢固的夢鄉,因為沉默和恐懼底季節已經過去……因為我們是在新的星象下行走,那些死難者,要在我們底身上復生……”。而在作于2月的《春》中,詩人在春天的包圍中所感受到的則是“欲望”、“迷惑”、“渴求”和“火焰”此類完全屬于春天的情感了,春天在這首詩中指涉著詩人自身的年輕生命。
一般來說,我們對于春天的聯想,或者說,春天在文本中和其他季節顯出區別的地方,在于那些春天特有的意象——綠色、小鳥、花朵、春風。在《春底降臨》中,“一個綠色的秩序,我們底母親”,綠色就是春天本身;在1942年的《春》中,綠色是一種可以用火焰來比喻的感情;在《春底降臨》中,花朵是從心的荒原中生長出來的,在1942年的《春》中,花朵則是反抗著土壤掙扎出來的;在《春底降臨》中,燕子的呢喃取代了過去悲哀的回憶,在1942年的《春》中,用土做成的鳥則變成了詩人自己;在《春底降臨》和1942年的《春》中,都提到了春風可以作為一種情感的載體傳播個人的感情。在這兩首詩中,春天帶給詩人的感情完全是正面和舒緩的,春天甚至可以作為詩人本體的象征。
但是這些意象在1976年的《春》中卻發生了質的變化。首先,作為感情載體的春風不見了;這成為穆旦晚年寂苦心態的一個信號。其次,在1976年的這首作品中,花朵和新綠試圖推翻穆旦的“小王國”,為什么要使用“王國”這樣帶有邊界和主權意識的詞來表征自己的精神世界呢?“春天的花和鳥”都對詩人暗含著敵意。光是由這兩句,我們就可以看到詩人和所有可以象征著春天的事物都保持著一種緊張的關系。詩人對他們懷有戒心和敵意,而這種心態借由他的觀察又反射到了詩人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在這首詩中,詩人多次提到“寒冷的智慧”、“寒冷的城”,可以視作對前文中的“王國”的一種補充——詩人“弱小的王國”是一座寂靜、寒冷的小城,這座小城里沒有早年的活力和溫暖。穆旦晚年的詩作雖然以春天為題,但是與以春天指涉生命本體不同,詩人洞悉了人這一主體性存在的有死性,“春天/生命”反而成為存在的悖論。
變奏2、城:穆旦在1948年和1976年分別有兩首詩作處置人與城的主題。1948年《城市的舞》,詩中充滿了擬人化的建筑物、同一的、毫無特征和區別的個體、以及充滿毀滅的生存方式。《城市的舞》是穆旦在還沒有高度城市化的時代下敏銳的探查,這種對于社會的觀察方式充滿了現代性和先鋒意識。而在1976年《城市的街心》,抒情主體的視角從自己腳下發散出去,在他眼中,城市的街道是一條五線譜,而在街上來來往往的車輛、行人乃至不會移動的建筑物都是這五線譜上的符號,穆旦幾乎是用兩句話就把《城市的舞》中對于城市景觀的敘述即寫出來了;然后從第三句開始,穆旦迅速轉向了對自己命運的思考,而這種流動的生命意識又處處出現在了穆旦晚年的詩歌中。1976年的《城市的街心》和《春》在精神層面上有著共通性,城市景觀的“超時間性”依然揭示的是一種“時間性”主題——抒情主體對“年老/衰朽/死亡”的體認,一種對作為時間性存在的生命本質的深刻體驗與洞察。縱觀穆旦晚期詩作,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詩人依然回旋于早年寫作的題材或主題,但是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寫作已經演變為一門關于死亡的藝術。
變奏3、“我”:穆旦寫過三首以“我”為主題的詩,《我》寫于1940年11月,《自己》與《“我”的形成》寫于1976年。從這三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死亡變奏對于穆旦晚期詩作呈現方式的影響。
1940年代的《我》明顯涉及現代個體的孤獨感與疏離感,1976年的《自己》則將自我對象化,以第三人稱敘述視角在自我內部形成一種對話關系,以此呈現主體自我裂變的流動經驗,在經歷各種理想幻滅以及現實變形之后,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在《“我”的形成》中,抒情主體則將“自我”放進與外部力量的沖突當中,不僅呈現巨大的外部壓力對“自我”的箝制與約束,呈現生命形式的固定、以及意義的虛無,同時亦呈現“自我”某種難以掙脫的夢境,“仿佛在瘋女的睡眠中,/一個怪夢閃一閃就沉沒;/她醒來看見明朗的世界,/但那荒誕的夢釘住了我。”——一抒情主體仿佛“中魔者”,一個明朗的世界,一種合理性的生存秩序也不能把它抹除。三首詩中都提及夢境,一種詩意的、幻想性的、甚或是非理性的可能性。但是,與早年關于“我”的抒寫相比,雖然青年時代詩人即有強烈的時間意識,“痛感到時流,沒有什么抓住,/不斷的回憶帶不回自己”(《我》1940年),但是在晚期寫作中,死亡直接進入了詩歌。穆旦對“意義”的固執,使他從青年時代一直到晚年都在不斷抒寫同樣的主題,但是由于生命境遇的變化,對生命有死性的深刻體驗,使青年時代就生成的“意義”尋求發生一種“悲觀”的回旋與變奏——所謂在深心狂野中高唱的自我之歌——在一個主體被踐踏、被摧毀的年代,什么樣的歌聲能比這苦澀的智慧之歌更動人、更真誠呢?
變奏4、冬:穆旦在1934年寫過一首《冬夜》,抒寫少年詩人所感受到模糊難言的冷寂體驗。四十二年之后,從少年時代走到老年,詩人終于可以對冬季/冷寂/死亡表達豐富的觀感。寫于1976年的《冬》從文本形式上來看是非常特別的一組詩作,詩作第一節以第一人稱“我”作為敘述視點,第二節則以隱含的復數性的“我們”作為敘述視點,第三節敘述視點則分化在了不同的“你”身上,第四節則突然脫離開抒情主體的經驗世界,一變而為敘事化的“雪夜夜行”場面。這種同一題材的變奏既給《冬》增添了豐富的魅力,同時也給讀者帶來疑惑,詩人為何在文本中推進一種突然的敘事轉化?如果我們已經洞悉了穆旦晚期詩作的對意義主題的回旋以及所遭遇的死亡變奏,那么就不難看到,《冬》的第四節的敘事化場面對于詩歌前三節構成一種指涉關系。《冬》的前三節分別從“我”、“我們”、不同的“你”的角度反復抒寫主體所承受的“冬天體驗”,第四節的“雪夜夜行”場面則是對人的基本存在境況的總體隱喻。雖然冬夜大雪有著強烈的凜冽之氣,但是詩人并未表現出死亡的哀感,相反面對“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雪夜夜行的人們反而散發著暖意,在短暫的歇息與閑談之后,“幾條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撲進寒冷的空氣。”(《冬》)
關于詩歌閱讀:讀一首詩,與讀一位詩人所存留的全部詩,我們所面對的經驗與所獲得的感受完全不同。小說家帕慕克在談論小說閱讀時說到,“面對一幅大型繪畫,我們因所有事物同時盡收眼底而感到激動并渴望進入繪畫之中。在一部長篇小說之中,我們會因為置身于一個無法一覽無余的世界而感到眩暈的快樂。為了看到所有事物,我們必須不斷將離散的小說時刻轉化為意識中的圖畫。”對小說的總體理解有賴于對無數細節、及其綿密呼應的交互關系的把握。詩歌當然并不像小說一樣具有某種可供我們確定其細節、及其所構成的總體景觀的繪畫性,但是在詩人的全部創作中確實存在由“離散的抒情時刻”(每一首詩)所形成的總體性的關系。因為詩學表達更為切近音樂的抽象性,為了對詩人創作的總體理解,我們或許應該學習小說家的閱讀方法,“我們必須不斷將離散的抒情時刻轉化為意識中的音樂。”于是,我們可以看到,老年穆旦不斷回旋其早年主題,并在特別的壓力中經歷變化,“讓死亡直接進入寫作”。
[注 釋]
①目前,在《穆旦詩全集》與《穆旦詩文集》中對《妖女的歌》的寫作時間存在分歧,前者將之歸為1956年作品,后者將之歸為1975年作品,編者沒有任何說明,此從《穆旦詩文集》。李方編:《穆旦詩全集》,“目錄”,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穆旦:《穆旦詩文集》,“目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亦見易彬:《穆旦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頁。
[1]鄭敏.詩人與矛盾[A].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8.
[2]黃燦然.穆旦:贊美之后的失望[A].孫文波,張曙光,肖開愚.語言:形式的命名[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3]陳彥.穆旦在新中國的詩歌創作及意義[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1,(4).
[4](美)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M].李小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9.
[5](土)奧爾罕·帕慕克.天真的與感傷的小說家[M].彭發勝,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92.
[6](美)愛德華·薩義德.論晚期風格[M].閻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