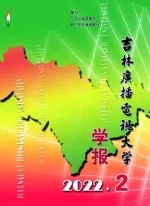漢賦之司馬相如賦的寫作視野
劉璐瑤
(東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024)
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也就是說,賦的最鮮明的兩大特征: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作為文體的賦是形成于我國戰國末期的一種文學形式,是在騷體的基礎上孕育和發展起來的。班固《兩都賦序》稱:“賦者,古詩之流也。”《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最早以“賦”名篇的要追溯到戰國時代那位提出“性本惡”的著名思想家荀卿,他的《賦篇》今存《禮賦》、《知賦》等五篇。但這種形式的出現并不為那個時候的人所注意,直到漢代,賦才成為一種特定的文學體制,尤其是漢武帝時候,稱為漢賦。雖然荀卿《賦篇》第一次以“賦”名之,但到漢代才特別盛行,并且影響到其他文體。后人因此將賦與楚辭、唐詩、宋詞、元曲等并論。賦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與散文的性質。古往今來,寫賦者甚多,無論是被稱作:“兩漢騷賦作家之首”的賈誼,還是其后的枚乘,他們仍停留在騷體賦階段,而真正大刀闊斧向新體賦前進的卻是西漢時期的司馬相如——這位生活在西漢最鼎盛時代的大家,體驗了國力強大、社會繁榮昌茂,也由此豐富其賦的題材,不僅物化到山川河流,鳥樹魚花,更有其聲勢浩大到岌岌將動,煒煒欲燃。體制宏大,語詞富贍,結構完整,使賦在漢代盛極一時,絢麗奪目,超凡脫俗。
一、超然脫俗的審美藝術視野
“知人論世”在了解一個作家及其作品內涵時顯得尤為重要。司馬相如,字長卿,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司馬相如賦一共有二十九篇。但對今人來說,我們只能遺憾地欣賞到《天子游獵賦》《大人賦》《哀二世賦》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這三篇,和《長門賦》、《美人賦》,二者分別記錄于《文選》、《古文苑》中。在這些賦中,充分體現了司馬相如深層次的美學思想——審美視野的擴大和深化。在司馬相如的賦中,這種審美對象的主體化被置于審美觀察的中心。。正如肖統所說:“自茲以降,撅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政游則有《長揚》《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云草木之興,魚蟲t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文選序》)在他的筆下,賦等同于富。豐富琳瑯的意象,以小見大,以個別體現一般。尤其是在《子虛賦》和《上林賦》中,這種奇景異象,鳥獸珍奇、鱗次櫛比,皆見諸于筆端。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審美意識的對象化也不失為是體現人主觀支配欲和自信心的一種方式。萬事萬物都受我支配和占有,這也是以強盛國力和雄霸內心為支撐的一種豪氣和浩然。對于他視野中的一切,無論遙遠的山川怎樣雄奇,河流怎樣湍急、虎獸怎樣兇猛、草林多么茂密。亦或是天上神秘魔變的諸神,也都為我所任意驅遣。這是何等的自信和何等瀟灑的情懷。而恰恰是這種情懷也正好體現了司馬漢賦一個突出的特點——整體觀和大氣為美的審美特色。
司馬相如就是用這種大而和的宏觀整體,以獨特的藝術審美視野支配自然于筆端,一反以往寫景只為烘托主人公情感的細膩逶迤的抒情方式,大開大合揮斥高山大河于文中,體現一個藝術家在盛世中所能抒發出的萬丈豪氣和支配自然地信心和造化。所以說,作為辭賦大家,司馬相如不僅在數量上力壓群雄,而且審美意象和審美視角上也有著非常獨特見解,也提出了自己比較完整的文學主張。因此,韓昌黎在《答劉正夫》這一文中稱“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構之最”。
二、氣象恢弘的鋪排藝術
提到漢賦,就不得不說起賦的主要特點之一;鋪采摛文。司馬相如之所以稱之為漢賦大家,也正是因為其在鋪陳排比藝術上的無可比擬的藝術功底。所謂:“賦莫如司馬相如”,長卿最主要的是以氣制勝。這種氣勢,不單單是指虛伐的句式,而是從精神上的大氣磅礴。劉熙載曾在《藝概·賦概》中提到,“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也不暢,暢無或竭。”鋪排就其本身來說,是要求押韻對稱美的,而美不單單在于整齊,也在于有序。在司馬的《子虛賦》、《上林賦》之中,這一特點體現的淋漓盡致。他在文中努力營造出一個時空交叉的整體感,使文章既有空間順序,又不乏時間規律。例如司馬相如在《子虛上林賦》寫到美不勝收的云夢之山時,先以“方九百里”總概述云夢山的方圓寸領,然后再分別以質地分言山、土、石,以方位來區分東南西北這四個方向,而且南北兩處又加以微妙區分高燥與埤濕環境、上下共有四層,一番描述下來對云夢的地理環境作了全角度、多方位的概述。文中的“其東……。其南……,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西則有涌泉清池,……鉅石白沙。……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橘柚芬芬。”,這些句式呈現一種完整無缺的立體空間思維,將所要表達的客觀物象一覽無余。既明白又對稱,這也與古代四方、六合等特殊的思維觀念有莫大的關系。不光如此,作者敘述段與段之間的結構鋪陳時,也要以排比的形式增加氣韻,增強氣勢。其中不乏有萬千生靈在此繁育生命,自然一派安定祥和,景色大不同。時間空間仿佛對稱般的存在。例如《子虛上林賦》描寫司馬鋪陳上林苑囿的盛世豪華,天子畋獵的聲勢浩大,離宮別館的金碧輝煌,一口氣接連十個排比段,皆以“于是乎”開頭。
當寫到上林河里的魚鳥玉石:于是蛟龍赤螭,……當又描述山川巍峨之雄大時:于是乎崇山矗矗,,南山峨峨。當宮殿見諸筆端時隱時現:于是乎離宮別館,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長途中宿。……賦中的鋪排要明顯地表現出來,需要超高的駕馭語言的本領,必然要語言豐富,辭藻華麗。我們再觀賞歌舞的聲色犬馬:“于是乎游戲懈怠,……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司馬大家用一連串對偶句加上氣勢磅礴的排比句生動形象地寫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充滿了壯志豪情。“這種勝利使文學和藝術也不斷要求全面地肯定、對自己生存的山川江河種滿了信心和希望、這些種種栩栩如生的意象,都生動的存在在自然和人們心中,此時此刻,人這時不是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而完全溶化在外在生活和環境世界中,在這種琳瑯滿目的對象化的世界中.”
在大多數司馬相如的賦中,有很多詞語都描寫了聲勢浩大的游獵場景。文中充斥了運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以動賓短語結構為主,句式不等,這樣的句子在文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如描寫天子的游獵場面:“生貔豹,搏豺狼,…………,弓不虛發,應聲而倒。”作者有能力一次鋪陳出形態各異的不同意象和人物形象,十八種形態各異的人物形象都發揮其不同特色的魅力.司馬相如在《子虛賦》、《上林賦》中,時空變換、動靜結合兼有虛實相生、變幻莫測的同時而又詳略得當,把大自然的萬事萬物羅諸筆端,躍然紙上。以事物的強大的邏輯順序構成事物發展順序。縱橫捭闔,有詳有略而不失豐富描寫和鋪排,為文章增添強烈的氣勢和韻律,使司馬相如的賦讀起來朗朗上口。除此之外,對于具體意象來說,虛實結合而又詳略得當,為漢大賦的創作《子虛賦》《上林賦》又增添的一抹新的亮色。可以說是既有條不紊的進行意境創作,又不缺少應景而生的各種描寫,可謂雙管齊下,收獲頗豐。
最后,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賦》中如他寫各國的狩獵情況,使楚國、齊國和天子都各有各的藝術形象特色。南國風情在楚王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而北國的剽悍粗獷之風又毫無保留的展現在了齊王的身上,而其中最高貴、最不可褻瀆的當是悠悠然然的天之驕子,其高貴、和無限風姿,非其他諸侯小國所能比擬的。天子狩獵本來就該是有天之驕子的偉大風范,而對其他諸侯的寥寥數筆,則是和天子威嚴形成了強烈對比和差距。由此可見,司馬相如在其《子虛賦》《上林賦》中的鋪陳手法和排比手段在當時不可謂不登峰造極,司馬相如以其超凡脫俗的大幅度對偶和排比,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和視覺沖擊。他這種獨具匠心的表達方式,也對后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朱玲.漢字“賦”的語義系統和賦體語言的美學建構[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
[2]王思豪.論司馬相如賦層進式的創作方式——兼談西漢人“不可加”之心態追求[J].滁州學院學報,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