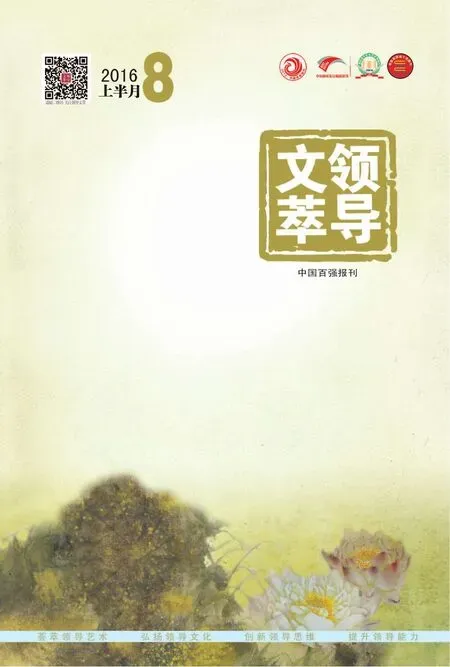再看閻錫山
余世存
考察閻錫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學史家曾概括19世紀末以來中國文化的關鍵詞,有“焦灼”“心碎”“嫉羨”等等。因為中西文明的沖撞,在西方的強勢影響下,中國從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見絀。連孫中山都作激憤語:“中國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
閻錫山作為一省大員,沒有這種“時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國社會落后情形的。
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么?”
閻答:“是中。”
泰戈爾問:“什么是中?”
閻說:“有‘種子雞蛋的那‘種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這個‘中。”
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上海、天津、北京,為什么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跡?”
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們想要找,去鄉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一般以為,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儒家傳統影響他的一生,在他人看來是一個局限,但在閻錫山那里,未必不是一筆財富。
閻錫山在列強環伺里能夠自立自強,并非遺老遺少的冬烘先生可以比擬。他確實有中國的根和中國本位,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中的句子。他反復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閻錫山表達出一個中國本位的現代進取人格,這種集思辨、事功于一體的人格,常被一般論者忽略。在蔣介石之外,這個現代中國的政要也留下大量的日記,他的日記特點是多記理、少記事。
閻為鄉村學校捐錢,不遺余力;抗戰爆發,他又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87萬元捐給前線;他還摒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黨人,使山西成為陜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許多愛國志士。
閻錫山很少說套話,對他有啟發的思想,經過他的一番思考,就能轉換成他自己的語言說出來。比如“財產是身外物,易于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當重技能”“大錯成于漸,大病成于微,大患成于細,大富積于零”“恭維我者,有損于我。責備我者,有益于我。積損則兇,積益則吉”。既說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說明他的信念堅持。
閻錫山的自信,正是因為他善于學習。
跟民國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是一個小字輩,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說他在袁世凱面前緊張得要命,他也一度對實力派俯首。但他風云際會,抓住時勢,也成全時勢。
他的同學程潛說,閻錫山“在日本留學時成績平常,土氣十足,誰知回國后,瞬間馳名全國,是日本留學生回國后在政壇上表現最為輝煌的人物”。
不僅如此,他后來以一省之力,敢跟蔣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論者看來,蔣介石之所以能統一全國,閻錫山的功勞最大。他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渡過數次危機。他跟張學良一樣明白,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
1934年,閻錫山給蔣介石寫信,幫蔣出主意,說了很多個人感悟。他說,你是元首,所以我對國家大事的認識,應該告訴你。對當時的“異端”學說,如共產主義,他也能夠吸收其長。他的理論研究會,可以談共產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成員在家里翻譯《資本論》。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因為他說得很干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并確定了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閻錫山曾經與共產黨合作,在國民黨內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臺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后,新軍加地方團共約15萬人同時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還有人暗示說,閻錫山是國民黨垮臺的“禍首”。
(摘自《大民小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