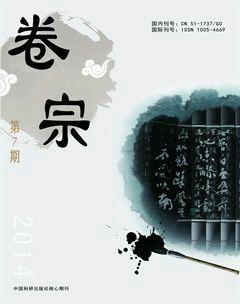淺析老子之理想社會與柏拉圖的“烏托邦”
劉子寬 朱孟苗
《老子》相傳為兩千四百多年前老聃所著(關于《老子》一書的作者和具體著書時間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議,在此采用較為廣泛之說法),后世從西漢末期楊雄開始,又稱《老子》一書為《道德經》。《老子》全書中有三分之二的章節在談論或涉及到政治。從某種角度上看,《老子》一書就好比西方哲人柏拉圖之《理想國》,同是在提出相關理論的同時在理論基礎上構建一理想的政治社會藍圖。對于老子之理想社會,簡而言之,“小國寡民”也。當然,“小國寡民”只是老子之理想社會諸多表現中比較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一個,在此以“小國寡民”代老子之理想社會。
在這一理想社會中亦存在其統治者,即老子所謂“圣人”。《老子》一書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第十七章)由此可知,老子將統治者按不同的情況分為四種不同的等級。其中,對于最正確的統治者,人民是不知道他的存在的,而最差的統治者是被人民所輕辱的。處于兩者之中的統治者或是被人民親近贊美,如儒家所謂統治者;或是被人民敬畏,如法家之所謂統治者。老子認為,最好的統治者,即圣人,管理社會之方式是“無為而治”,很少發號施令。圣人循道治世而人民不知,其政治權利絲毫不會逼臨于人民身上。“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人民不會感覺到國家作為一集體的存在,如果統治者、政府或國家集體被人們“察覺”其存在,那就非“循道”,非“無為”。而圣人治理下的社會,民風淳樸,生活安定,人民結繩記事,無勾心斗角之嫌,無爾虞我詐之弊,人人都會回到如嬰兒般之純真狀態。
此便是老子之理想社會。若與其相較,西方哲人柏拉圖之理想社會“烏托邦”之治國方式則幾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在柏拉圖之理想社會中,亦存在其統治者,即柏拉圖所謂“哲學王”。“哲學王”好比老子之“圣人”,皆悟“大道”之人(以柏拉圖之意,乃透過現象把握“理念”者也)。但“哲學王”管理下的社會卻與“圣人”的幾乎完全相反:①圣人“無為而治”,反對政府對人民的過度干預;以哲學王為代表的政府幾乎參與到人民的所有生活中,甚至連“家庭”作為一社會基本單位也被取消,由國家建立公共托兒所撫養兒童。②在老子之理想社會中,人民是無法察覺到“集體”之存在,不知“集體”之概念的;在柏拉圖之烏托邦中,“集體”則代表了一切,集體利益高于一切,個人必須服從于集體。③在老子之理想社會。人們結繩記事,人的“智力”處于一種被抑制開發的狀態,人人都如嬰兒般純樸無知;在柏拉圖之烏托邦中,對智慧的開發是沒有限制的,反而鼓勵人們學習并開發智力。尊重智慧、熱愛智慧被廣泛接受并成為一種美德。④作為老子之理想社會中唯一的有智者——“圣人”,又因循道而處于一種“無”的狀態,“不知有之”。甚至竊以為,圣人不應在老子之終極理想社會形式中作為一客觀的實在,因若其存在,則非“不知有之”,則非“循道”,則非“無”。故“圣人”在老子的理想社會中不應是實際存在的,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被賦予人之特性,而并非具體到某“個別人”(當然,不排除在實現理想社會的過程中存在“某個別”圣人)。雖圣人是不存在的,但人人又皆為圣人,因人人皆“無知”,人人皆“無為”,故人人皆“循道”,在這里“圣人”又具有一種廣泛的含義。所以,在老子之理想社會中,人人又都是平等的,作為統治者的圣人只是一種名義上的存在,在此社會模式中是非客觀存在的。退一步說,即使我們假設圣人是“實際存在”的,但其又“不知有之”,不存在馬克思主義所謂“階級對立”之含義,故老子之理想社會的終極形式乃一平等之社會;在柏拉圖之烏托邦中,社會等級、社會秩序十分明確,由哲學王等“精英”和其“輔助者”構成國家的統治階層和管理階層,而廣大勞動者則處于被統治的地位。同時,有利用“金屬的神話”這一“尊貴的謊言”來使人們相信自己的出身并接受現實——你的階級由你不能控制的外界因素所決定,以此來達到消弭反抗、維護秩序的目的。
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東西方兩大哲人之理想社會模式的差異之處。但造成此諸多差異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筆者本人傾向于“社會環境影響說”,即兩位哲人之理想社會模式都受到了其所處社會背景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其理想社會模式是對當時社會模式反思后的產物。
雖然當前學術界對老子所處的年代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但大致推測應處于春秋戰國時期。該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的大變革時代,政治動蕩、社會混亂,各國王侯你爭我奪,紛紜擾攘;課稅徭役繁重,戰爭爆發頻繁,百姓生活極不安定;由于各國均竭力使自身在激烈的斗爭中獲得優勢地位,“崇才尚賢”之風興起,由此導致“貴貨”見“可欲”,智謀巧取之士奔走于諸侯之間,一時眾心紊亂。故老子對此進行了反思,提出“無為而治”,反對政府的過度干預,使百姓生活得以安定,故“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第三章),抑制智慧開發以安民心。而在柏拉圖所處之希臘雅典,在當時已開始走向衰落,持續二十七年之久的伯奔尼撒戰爭終以雅典之失敗、斯巴達之勝利而告終。斯巴達在雅典建立寡頭政治集團,大肆破壞民主制度,雖終被推翻,但雅典的民主制度已徹底淪為黨派殘酷斗爭的工具,政客蠱惑民心,民眾道德下降,皆從私欲的滿足中獲得快樂,民主政治已徹底墮落為暴民政治。公元前399年,雅典民眾法庭以不敬神罪和蠱惑青年罪判處蘇格拉底死刑,使身為蘇格拉底弟子的柏拉圖對雅典的民主政體徹底失望。面對秩序混亂的暴民政治以及個人日益膨脹的私欲,柏拉圖在反思的基礎上參考斯巴達城邦之體制,著書《理想國》,描繪了一個等級秩序嚴明,國家集體利益至上的社會。
兩者相較,各有千秋。兩位哲學巨匠所繪理想社會藍圖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都對各自東、西方之政治與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然竊以為,老子之理想社會藍圖無論是從縱向還是橫向來看,都更具有一種獨立于時空之外的永恒思想價值,更值得我們對當代社會進行反思,并借鑒某些東西。
參考文獻
[1]教育部《中國傳世經典叢書·道德經》[M].遠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2]古棣,關桐 《老子十講》[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3]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M].商務印書館,197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