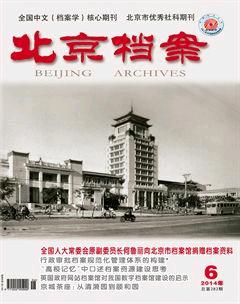口述歷史中的李清
楊紅軍
“二次長征”中險丟一條命
1944年11月,李清隨359旅南下,任南下支隊政治部秘書。路途遙遠,環境惡劣,他除了和戰友們一樣背負行裝外,還要身背部隊用的很多銀元。每次部隊行動前,他總是跟戰友說“我先走一步”,就先于大部隊出發去打前站。當時部隊沒有統一的被服,沒有布鞋只能穿草鞋,行軍打仗,翻山越嶺,山路曲折泥濘,鞋子穿得很費,所以大家一遇休整間隙都抓緊編草鞋。在一次緊張的長途急行軍中,不知什么時候李清的草鞋跑丟了,腿上還生著疥瘡,帶的備用草鞋也穿光了,只好打赤腳,有個戰友熱情地給了他一雙草鞋。就這樣,1945年8月底,南下支隊抵達廣東省南雄縣。在南雄縣,李清既從事部隊工作,也從事地方工作。當南下支隊進入五嶺山區,與前來接應的東江縱隊僅距百里之遙時,他們從繳獲的報紙上得知日軍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南下支隊待命行動。蔣介石糾集了15萬兵力對南下支隊圍追堵截。敵眾我寡,為避其鋒芒,南下支隊轉入八面山的崇山峻嶺中。8月29日,中央電令南下支隊,為避免內戰回師延安。在返回延安途中,南下支隊經歷了眾多艱難險阻。在湘南、贛西、粵北地區及井岡山周圍,部隊減員甚大,許多同志壯烈犧牲。李清奉命返回湖北大悟山,留在新四軍五師,參加部隊和地方工作,先后任鄂東地委秘書長、宣傳部副部長、教導隊政委、團政治處主任等職。李清隨南下支隊轉戰于陜、晉、豫、鄂、湘、贛、粵、隴八省,路經百余縣,沖過無數封鎖線,參加大大小小的戰斗300多次。
在危險的敵占區,李清經歷過一場與敵人的遭遇戰。當時戰斗異常激烈,敵強我弱,你死我活,戰斗呈現白刃化態勢。上過戰場的人都知道——遭遇戰遭遇戰,慫包軟骨準完蛋。狹路相逢勇者勝。李清不顧警衛員的勸阻,勇敢地帶頭沖上前線,手榴彈在身邊不時爆炸,密集的槍彈呼嘯著,塵土碎石散射四方。就在他勇猛殲敵時,突然飛來的子彈掠過頭頂,彈片炸傷他的頭部,流血很多,昏死過去。警衛員小彭冒著槍林彈雨把“李政委”搶背出來,使他撿回一條命。自己是怎么負的傷,又怎么死而復生的,這些都是李清事后從警衛員嘴里知道的。一個甲子后,我采訪他時,他頭頂受傷部位還能摸到拇指大小凹陷的坑,問他負傷那么重當時一定很疼吧?他笑笑說:“那會兒一點沒覺得疼,只感覺頭猛地震了一下,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啦。”據了解,警衛員小彭寫的搶救李清的經過,現在仍然完好地保存著。
后悔婉拒周恩來的挽留
1946年,李清正在宣化店養傷,適逢周恩來同志前來調處中原戰爭。周恩來提出:需要幾個人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幫助工作,要宋平推薦人選,并要求盡快到位。
宋平與李清在延安馬列學院是同學,對李清非常了解,知道他系統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懂得我黨關于革命戰爭的政策和策略,工作適應性好,進入角色快,便首先推薦了他。很快,組織上找李清談話,通知他調往南京中共代表團。任務緊急,在談話的第二天,李清就出發前往南京報到。在代表團里,他與龔澎、廖承志、經普椿、喬冠華等同志合作共事,緊張而愉快。周恩來同志特別關心部下,心又細,即使在紛繁復雜的調處工作中,還專門找李清了解工作和思想情況,問他在代表團工作適不適應,今后有什么打算,希望李清留在代表團。周恩來和藹可親,就像拉家常一樣,李清毫無顧忌地傾訴了自己的想法。他覺得做好調處工作需要高水平的人,對外發表新聞講話不僅要外語嫻熟,還要具備許多領域的知識,而自己外語不是強項,其他方面的知識也不夠,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愿意回延安繼續學習。就這樣李清婉言謝絕了周恩來的挽留,撤回延安。
過后,李清常為這件事后悔,直到晚年他還多次遺憾地說:“周恩來同志這么關心我,挽留我,我還非要走,真不該喲!解放以后我到了交通部,去人民大會堂開會見到總理,我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總理的記性特別好,有時還主動跟我打招呼。總理真是尊重別人的意愿,待人特別溫厚寬容。”
升官不發財的“老十級”
1952年春至1995年,李清一直在交通系統工作。解放初期,為了改善國內水運行業狀況,他請蘇聯專家傳授當時世界最先進的運輸技術,在長江上搞“一列式拖帶”實驗。剛開始拖船總是弄不好就撞,搞了多次總不過關,蘇聯專家搖搖頭聳聳肩,用帶著卷舌音的漢話說:“船-忒-重!”李清與我國技術人員和船工交流,摸清底數,再與蘇聯專家磋商解決辦法,大膽探索“頂、推”等專業技術,終于成功地開拓了內河運輸的新方式,極大地提高了水上運輸效率。中央非常重視這件大事,專門搞了攝影和紀錄影片。蘇聯專家高興地一手拍著李清的肩膀,一手舉著軍用的大搪瓷缸子說:“能喝酒啦!”一連喝了四大缸子。李清不勝酒力,他儒雅地微笑著陪客泯酒,蘇聯專家不依不饒地追問:“紅軍都是能喝酒的,你是老干部,怎么會不能喝酒哇?”
1957年,交通部要調有經驗有能力的干部去武漢海運工程學院領導工作。可是,“有經驗有能力的干部”范圍局限性大,符合條件的人不多;況且,誰愿意離開北京去外地赴任呢?李清毫不猶豫地去了。這個學院名不副實,校園很小像個中專。李清到任后,許多事情等著他辦,他覺得頂頂重要的是選址建校,建設一所全新的大學。李清跑遍了城里城外,把校址選定在空間較大的郊區。他帶頭開荒辟地,大興土木,還讓夫人趙若蘭帶動家屬義務勞動。學校建成后,針對“三材”缺乏的實際,他跟教職員工說:“缺人才不能等著國家派,缺教材不能等著外校給,缺器材不能等著資金買,咱們要自己多想辦法。”比如,李清把本校優秀畢業生送到北京、上海全國最好的大學培訓,受訓回來的同志都成了院校的骨干。有了建校辦學人才,就不愁教材,就有更多的途徑解決器材緊缺的問題。幾年后,外省市的大學來校參觀,由衷地贊美:“這所學校可真大,設施齊全哪!”
在交通部,李清幾乎轉遍了各個業務職能局,深入基層考察,親歷親為。他代表新中國與越南簽署了第一個國際航海協議,第一個引進蘇聯運輸先進技術,參與了轟動世界的打撈“阿波丸”的領導工作,在改革開放中首提“貨暢行流,人便于行”的目標……
盡管李清創造了我國交通運輸史上若干個“第一”,卻28年一直當局長。好朋友調侃他“領導重視你,器重你,就是不重用你”,聽到這話,他心里很平靜,淡然一笑而過。李清的工資幾十年沒調整過,還是解放初期供給制改薪金制時定的標準。當時,按照國家政策規定,像李清1951年任長沙市委副書記職務的,完全可以定為行政九級,而他自報自定十級,自覺地放低了一級。后來在國務院六辦時有機會上調一級工資,他主動推讓了。直到1982年,他任交通部部長、黨組書記,職務升了,官當大了,工資卻沒有變,與他同等資歷的老同志絕大多數八級、九級,而他依然十級,因而被交通部機關的同志們戲稱為“老十級”。
生命坎坷身世如迷
李清之父陳子安,河北省寧河縣蘆臺鎮人,祖上務農。他住的村莊離鐵道很近,聽說正太鐵路招錄火車司機,就去應考。人家看他長得人高馬大,憨厚壯實,回答問題不慌不忙,不怯場也不張揚,還多少有點文化,就錄用了他。陳子安頭腦清楚活絡,守本分不惜力,愛幫人好交友,說話干脆,辦事利索,很得上司喜愛,逐步由司機晉升為鐵路職員。慢慢地,他積攢了一些錢,娶妻李氏,把家安在石家莊。
夫婦倆過了幾年無子嗣,特別盼望有后。經介紹他們想方設法找到人販子“高四”,隨高四一口價收養了一個女孩,取名陳寶琴;過了兩年,又收養一個大約4歲的男孩,起名陳寶琦。陳家將姐弟倆視為己出,到了該上學的年齡,就送他們到鐵路開辦的扶輪小學讀書。
陳寶琦生來愛學習,媽媽忙家務時,他就在旁邊不聲不響地拿本書看。有一次,看書時間長了,他竟然抱著書睡著了,等書掉在地上才驚醒。夫婦倆看寶琦這么好學,越發地喜歡這個孩子。父親愛寶琦愛得深沉,常鼓勵他男孩子要膽大,要仁義,常講些《三國》、《水滸》、《楊家將》的故事,使他受到扶貧濟困、愛國為民的英雄主義的熏陶。母親愛寶琦愛得細膩,對他百般溫存,照顧得格外周到,生怕有閃失,上哪兒都帶著,就連打麻將牌也拉在自己身邊。她識字很少卻接受新事物,有經營思維,考慮孩子大了用錢的地方多,就把日常節省下來的錢存入銀行,給姐弟兩人每人存了200塊銀元;另將些微富余積少成多,在城鄉結合部冷清不繁華的地界買下幾間房子,預備用錢時賣房變現。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全國愛國熱潮高漲,扶輪小學也舉行抗日演講活動。學生代表的演講稿由老師寫好,讓學生代表上臺去念。不少同學爭著當代表,老師們商定由陳寶琦演講。11歲的陳寶琦個子不高,身子瘦弱,老師們連拉帶抱地把他弄到臺子上,他聲音清晰響亮地進行了演講,贏得臺下一片掌聲。學完小學課程,陳寶琦轉到北平大同中學讀書,在此期間,受進步思想影響,積極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當他和同學們喊著口號游行到王府井時,遇上警察鎮壓,結果他們被水槍的猛烈噴射沖散了。通過學生運動的實踐,他更加關注社會發展、關注國家命運、關注民族生存,也開始思索人生道路。
1937年離開家去山西那天,父親把陳寶琦叫到跟前,語重心長地囑咐他好好念書,將來要為老百姓、為國家做點好事。媽媽的話還沒說已經淚如雨下,她輕輕地撫摸著陳寶琦的手,哽咽著叫他常來信,說咱家就你這么一條根,走遠了媽掛心。話剛一說完她就背轉身跑回里屋去了。父親也別過臉,雙肩微微顫抖地揮著手說:“你走吧,走吧。”父親山一樣的背影,母親紅腫的淚眼……一家人都不曾料到這是最后的別離。
到延安后,陳寶琦改名為李清。李即母親的姓,改姓李是為了報答媽媽的養育之恩,清即表達了個人對清白、清風、清靜、清明的崇尚之意。
在戰爭年代,李清也時常思念父母,但烽火連天阻隔了家書,得不到家里任何音訊。直到1952年春,李清奉調武漢途經石家莊時,順道看望父母,才知道雙親早已過世。鄰居說:兵荒馬亂的,陳李氏時刻都為兒子擔心,沒有別的法子,她就天天吃齋念佛,一日禱告好幾遍,求佛祖保佑愛子平安,盼著兒子早日歸來。李清為沒有機會再報答父母的恩情而深感愧疚。他終生感恩于養父母,每當家人談起或媒體采訪,使深情地憶及兩位慈善厚道的老人。
然而,爹不是親爹,媽不是親媽,姐姐也不是親姐姐,四口人本不是一家人,李清的出生日期1920年2月26日(陰歷正月初七),竟然也是養父母推算確定的。這真像樣板戲《紅燈記》,戲里的李奶奶、李玉和、李鐵梅祖孫三代本不是一個姓。這戲劇性的現實,是1968年交通部軍管會去他家鄉搞外調發現的,李清是組織找他談話后才知道的。
那么,“親生父母是誰?他們在什么地方?我何年月日出生?是怎么到了高四手里?”這一連串疑問像一團亂麻纏繞著李清,他多么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啊!在“文革”后期,他到家鄉尋找過高四,可這個唯一的知情人不在了,這讓李清的身世成了個迷。有人說李清的相貌似廣東人,也有的說李清的普通話地道像北京人,李清自己曾做過這樣的分析:石家莊是南來北往的交通要道,可能哪個粗心的旅客把孩子丟在候車室或站臺上,被高四拾到后轉賣了?可能高四就是借鐵路便利專做幼兒買賣的,不然陳家怎么能經他手買來姐弟倆呢!但是,這全都是推測和猜想,李清的身世是個永遠無解的謎。
作者單位:北京市檔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