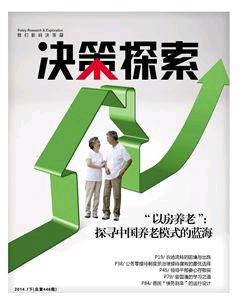混合居住模式:助推流動人口從“寄居”走向“安居”
楊菊華
流動人口居所與本地市民居所隔離性強
住房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個人財富與社會地位的凝聚與物化,也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體現。對中國人而言,“人以宅為家”,住房被視為“安身之所”,有房才能穩定扎根,無房始終寄居漂泊。而現實情況是,流動人口的住房擁有率極低,居住穩定性差。據2013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東、中、西部8個城市的調查結果,在16878個樣本中,分別僅有0.22%、0.43%和0.14%的流動人口享受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或已購政策性保障房;在流入地購買商品房或自建房的流動人口分別占8.20%和0.42%。其中,購買保障性住房的人主要為市內流動人口;購買商品房的人主要為城-城流動人口,跨省鄉-城流動人口的住房擁有率更低。相反,約2/3的流動人口租住私房,往往居無定所,常常搬遷。
流動人口居所的舒適性和安全性差。2013年,34.80%、19.44%、10.59%和9.01%的流動人口分別居住在農村社區、城鄉接合部、未經改造的老城區及城中村或棚戶區;居住在城市中商品房社區的流動人口僅有13.15%。即便流動人口居住在商品房社區,其居住面積也較為狹小,室內設施破舊,且工作場所常為居所。總體而言,流動人口住房普遍存在著建筑密度大、容積率高、通風采光條件不理想、配套設施少的問題,公共衛生“臟、亂、差”的現象突出,并存在用電、用火等安全隱患。
流動人口的居所與本地市民居所隔離性強,僅有1/4的流動人口的鄰居主要為本地市民。在不同流入地區、不同戶籍類型和不同流動跨越區域間,隔離程度的差別較大:在東部地區,不到兩成流動人口的鄰居主要為本地人,遠遠低于西部地區的45%以上;與城-城流動人口相比,鄉-城流動人口的鄰居為本地人的比例更低;與跨省流動人口相比,省內跨市、市內跨縣者與本地市民為鄰的比例明顯更高。這些數據說明,東部地區的流動人口、鄉-城流動人口以及跨省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的居住隔離更強,凸顯出戶籍及其衍生制度和結構性要素的制約。
居住隔離制約了流動人口進一步發展
居住隔離是人口遷移流動初期不可避免的過程和現象,可幫助初來乍到之人形成新的社會支持網絡,提供生活互助,獲取新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信息,使其較快地適應流入地的經濟社會生活。但是,隨著流動人口在流入地逐漸立足,隔離性的居住就會制約流動人口的進一步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第一,強化了貧困世襲化或加劇貧困分化。在農村社區、城鄉接合部或老舊城區,人口結構較為單一,或多為本地農民,或多為層次較低的流動人口;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缺乏、質量較差;社會管理水平較低。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缺失或不完善,既會降低相應群體的生活質量,又會擠壓居民向上發展的空間。
第二,減低流動人口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這種二元分割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流動人口的“低檔”社區與本地市民的“高檔”社區隔離,減少了流動人口和本地市民之間交流的機會。因朋友式的互動是增強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社會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重要途徑,而居住隔離強化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故將阻礙本地市民對流動人口的包容與接納,進而延緩流動人口對本地社會的認同,嚴重時還會引發相互之間的敵視情緒與矛盾沖突。
第三,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同質性較強的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可能進一步強化他們之間的聯系,形成更為牢固、難以突破的社會關系網,與本地市民“高檔”社區強烈對比下產生的不公平和剝奪感不斷累積,甚至可能形成偏離主流社會的、扭曲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可以說,流動人口住房的邊緣化不僅形成了該群體與城市市民的居住隔離,也進一步導致了他們在政治上的邊緣化和弱勢化,使其滋生對社會的仇視心態,給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埋下隱患,并可能成為極端事件的導火索。
混合居住可促進人群交融
市場因素和政策缺位是導致居住隔離的根本原因。不同社會階層的居民基于各自經濟實力選擇住宅,經濟社會地位較好的居民對空間資源的競爭和支付能力較強,會逐步占據城市中較好的空間區位,而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則由于競爭力不足必然被局囿在城市中較差的空間區位。多數流動人口因收入低,往往只能租用本地市民置換下來的廉價老舊房屋:本地人搬走了,流動人口搬進來,形成主要由流動人口構成的聚集社區。
集中居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為隔離。一方面,針對貧困人口的公共住房政策的集中分區規劃,盡管解決了包括極少數流動人口在內的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居住問題,但客觀上強化了人群之間的居住隔離。另一方面,企業出于管理等原因,往往為流動人口提供空間小、設施簡陋的集體宿舍。這樣的宿舍往往靠近廠區、遠離居民區,在空間區位上邊緣化和孤島化,在規模上大型化和集中化。這種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的模式,也人為地加劇了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的空間區隔和社會隔離。
主流人群“逃離”也起到助推作用。“白人逃離”理論主張,種族集聚影響居所選擇。Denton在2006年提出,因黑人子女的輟學、單親、失業、犯罪率高,且黑人子女占比較高的學校總體成績往往遠低于標準平均成績,故當一個特定地點的黑人數量達到一定比例后,白人就會逃離該區域。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我國:在流動人口較多之地,有條件的本地市民往往會搬離此地。
針對居住隔離的種種弊端,歐美學者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探索混合居住的理論。混合居住模式基于尊重城市人口的自發和自我多樣化的考慮,主張將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居民在鄰里層面結合起來,比鄰而居,形成相互補益的社區。對主流群體而言,混合居住有助于他們經常性地接觸異質人群,既可擴展自身的社會交往圈,又可增強對弱勢群體的理解、包容和接納;對弱勢群體而言,與主流群體的互動有利于自身及下一代的縱向社會流動。國外經驗表明,混合居住是破解人群隔離、防止區隔融合、推動人群之間真正互動交融的重要途徑。在中國,從隔離式居住走向融合式居住亦是促進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縮小階層分化、實現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由之路。
如何推動流動人口的“安居”生活,將其“留”在流入地為當地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是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最難破解的瓶頸,也是對流入地政府社會治理實踐的一個巨大考驗。破解這一難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有效改善流動人口的居住水平,使居者有其屋,租者安其屋,讓他們能夠真正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切實推動實現從“寄居”到“安居”的轉變。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