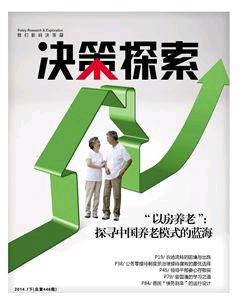淺談當今語文教育分科的利害關系
趙偉
1951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秘書長的胡喬木,在第一次全國中學教育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語言與文學教育分開”的設想,經1954年2月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批準,中學語文實行漢語和文學分科教學的做法從1956年秋開始正式實施。然而由于政治原因,此次語文教育改革到1958年3月便被中央宣傳部叫停。時至今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語文教育分科的問題依然是關心語文課改的教師和社會各界熱心討論的話題。筆者在此謹對文學教育從語文教育獨立出來之后衍生的問題作一淺顯的探討。
文學教育獨立后必須進行轉型,以還原文學的藝術本性。與語言和文字不同,文學屬于藝術的范疇,這一點是被我們語文教育長期忽略掉的。王國維在《教育雜感》中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由此可見文學教育的重要性。而目前語文教育中遭人詬病最多的,莫過于文學教育。關于現今語文教學中文學教育部分的弊病,薛毅發表在1997年第11期《北京文學》上的一篇文章《文學教育的悲哀》早已分析得鞭辟入里,此不贅言。上海大學的葛紅兵教授認為,“目前的所謂‘文學教育完全不適應當代中國文化產業化發展的需要”,是“把文學當作意識形態時代教育體制的遺存”,“文學教育應有獨立學科地位,應確認其作為藝術教育學科的本質品格”。轉型后的文學教育將完全脫離現有的語文教育模式,具體內容可以包含文學欣賞、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三大板塊,力求讓真實的文學作品鮮活地呈現在學生面前,以實現師生與文學作品之間靈魂上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激發,進而使學生具備一定的專業文學欣賞能力和文學寫作能力。文學教育雖然不以培養作家為己任,但是藝術的本質和人文的屬性是絕對不能忽略的,正如音樂教育并不一定要培養出音樂家一樣。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思和教授說:“文學不是一門職業,但是,它對于人們認識自身感情世界的豐富性、洞察人性的復雜性以及學習美、感受美、傳播美,進而提高人的整體性修養,有著根本性的意義。”
把文學教育請出去之后,剩下的語文課是不是就變得空洞無物、沒什么可講了呢?遠遠不是。有的研究者說,應該在現有語文教育的基礎上增設文學教育課,或許也是出于上面的擔心吧。其實,沒有了文學教育,語文課還有語言和文字兩大板塊的內容,只不過正如1956年的分科改革一樣,“語文”課就要更名為“漢語”課了。也有人提出可將“語文”課更名為“語言”課,這是沒有厘清語言學和文字學關系的緣故。著名語文教育家葉圣陶在《關于語言文學分科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漢語課包括如下的內容:語音、文字、詞匯、語法、句讀、修辭、篇章結構。其中語法的教學時間最多。”他對漢語課程內容的這一界定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語音”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漢語拼音的教學,語言學中和語音相關的方言學、訓詁學,甚至是音韻學都應包括在內。“文字”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識字教學和一般的字形分析,其他如古文字學、漢字的發展史、六書理論、漢字的整理和簡化、書法藝術等也應該請進漢語課堂,這也正是漢語課與英語、俄語、日語等其他語言課最根本的區別所在。西方的拼音文字教學僅僅要求學生掌握聽、說、讀、寫四項基本技能就可以了,漢語不是,因為它的語音、字形甚至字義都是一門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的學問,它不僅是中國燦爛文明的載體,其自身也是我們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總之,我們要充分利用中國語言文字的寶貴遺產和中國語言學、文字學的相關研究成果。
當然,漢語課不能上成語文知識講座。如前所述,漢語課要充分利用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相關研究成果,但并不是說漢語課的教材就只有知識講述,沒有課文。這主要牽涉到漢語教材的編寫問題,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運用,而語言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正如葉圣陶所說:“語言和文學一分開來,并不是彼此就不相干了,兩科之間的關系還是十分密切,必須緊密地聯系起來。”因此,漢語教材中必定要有文學作品,只是這里的文學作品成了分析語言和文字的素材,在甄選上與文學課里的作品有著完全不同的要求。除此之外,漢語教材中還應該有一些權威學者介紹語言和文字的課文,比如黃伯榮關于漢語方言分析的介紹、裘錫圭關于漢字整理和簡化的介紹等。
文學教育與漢語教育并行,會不會大大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呢?這樣的擔心有一定道理,然而卻是不必要的。興趣之所在,工作雖多亦能自得其樂、陶醉其中。反之,只能讓人感到索然無味,最后草草應付了事。葉圣陶在分析這一問題時指出:“語言文學分了科是不是會使學生負擔過重,問題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適當不適當上,不在兩科分不分上。”從1956年分科教學中廣大師生的一致好評來看,上面的擔心也是大可不必的。不僅如此,針對文學教育和漢語教育不能涵蓋的內容,還應該增開一些選修課或者配備一些課外讀物。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臺灣國文教育的經驗。臺灣的國文教材分為三類:標準國文教科書、選修教材和課外輔助讀物,三種教材各有側重,相互為用。比如“文法與修辭”“國學概要”“應用文”及“書法”等都是臺灣國文教育中的選修科目,并配有專門的教材。所以,文學教育獨立之后,相應的課程設計都需要作出有針對性的改革。
另外,語文教師的培養模式必須轉變。教師如何教,不僅關乎到學生負擔的輕重問題,也關乎到語文教育的成敗。文學教育和漢語教育分科之后,對語文教師的專業素養和教學水平的要求將會大大提高,照本宣科式的教書匠注定是要被淘汰的,這就涉及到語文教師的培養問題。1956年分科時,各地教育部門曾經對中學語文教師展開一系列突擊性的專業技能培訓。分科終止后,這種有針對性的培訓也就不復存在了。目前的中文專業師范類教育基本上是在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的基礎上增設一少部分的心理學、教育學等課程,這就造成語文教師教學技能的先天不足。常言道,文史不分家,在語文教師培養上,不能只偏重中文類的專業課程,有關歷史學、哲學方面的課程一定不能忽視,同時,目前教育學的比重也必須得到加強。在這方面,港臺的中文師資培養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定的借鑒。比如臺灣師范大學,師范生需修滿普通課程(含通識課程)20 學分以上、教育專業課程 26 學分以上、專業課程(任教科目)30 學分以上,據統計,其國文系開設的選修課程多達116門,除語言文學專業之外,也包括很多哲學、歷史類的課程,如“西洋哲學史”“邏輯概論”“中國佛學史”“魏晉玄學概論”“六祖壇經”等;香港中文大學為了培養中文師資,特設置了5年制的“文學士及教育學士(中國語文教育)雙學位”制度。語文教師只有掌握了文史哲及教育學各學科領域的牢固專業知識,才能勝任分科后的語文教學。
2013年12月7日,教育部在《中國教育報》第1版發布了《教育部高考制度改革方案》,明確指出:“外語科目實行社會化一年多考。”緊接著,北京市宣布外語高考分值將降至100分,而語文分值升至180分,并提出高考語文命題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考查。中華書局也已正式引進臺灣高中必選課教材《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并在此基礎上修訂出版《中華文化基礎教材》,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我們母語教育的重視。與此同時,筆者認為文學教育獨立和語文教育分科問題也應該重新提上議事日程。在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語文教育的改革也一定能夠以此為契機取得重大突破。
(作者單位:鄭州廣播電視大學)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