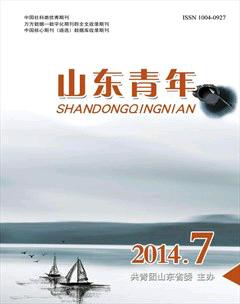論莎劇《李爾王》的復調敘事特色
李爽
摘 要:《李爾王》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李爾王》的復調敘事成為繞不開的話題,所謂復調敘事就是作者將自己內心的矛盾沖突化為敘述者與故事人物角色(大多是故事主人公)之間的矛盾,這二者總是存在不和諧的聲音,在《李爾王》中,莎士比亞的內心的矛盾演化成莎士比亞與李爾王之間的矛盾沖突了,這實際是莎士比亞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沖解內心困惑的一種藝術手段。
關鍵詞:莎士比亞;《李爾王》;復調敘事
《李爾王》作為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其獨特的人文關懷與超乎時代限制的沖破封建束縛精神,給當時的文藝復興運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李爾王》的復調敘事成為繞不開的話題,所謂復調敘事就是作者將自己內心的矛盾沖突化為敘述者與故事人物角色(大多是故事主人公)之間的矛盾,這二者總是存在不和諧的聲音,即作者自我的感受與故事角色之間的矛盾沖突已經背離了一種理性式的文學構述了,在《李爾王》中,莎士比亞的內心的矛盾演化成莎士比亞與李爾王之間的矛盾沖突了,這實際是莎士比亞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沖解內心困惑的一種藝術手段。
本文將以《李爾王》中復調敘事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復調敘事的時代內涵來研究莎士比亞筆下《李爾王》的復調敘事特色。
一、復調敘事的具體表現形式
莎士比亞始終將復調敘事的模式貫穿于《李爾王》的始終,相較于復調小說,戲劇更需要這種模式來構述全文。須知,戲劇是需要人物角色的對話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激化故事矛盾,吸引讀者,那么莎士比亞內心的矛盾勢必會演化成作者與角色人物之間、角色與角色之間的沖突了,這其中的每一次沖突都是作者靈魂深處的相撞,在這種沖突中,莎士比亞以求尋得一個合理解決沖突的方法。復調敘事的具體表現形式主要分為:人物內心獨白與角色之間的獨白。
所謂人物內心獨白就是人物在內心深處存在兩種聲音,這兩種聲音各自宣揚著彼此向左的觀點,這種價值觀的對立極為清晰明白地展示了人物自身的矛盾沖突,將一個立體可感的人物形象展現在觀眾面前,讓觀眾可觀可感,另外這種雙重或者多重的價值觀對立也勢必會影響到故事的發展走向,也注定會激化人物之間的矛盾,將故事情節推向高潮。如在第二幕中,李爾王的侍從被他兩個女兒蠻狠地撤走后,在李爾王的內心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是無法言表的悲痛,這種悲痛是一種無可奈何地接受,于是在他的內心深處中出現了卑微和怯懦的聲音:“那么天啊,給我忍耐吧,我需要忍耐!神啊,……叫我默然忍受吧”這種懦弱的聲音是對女兒野蠻粗暴的妥協;與此同時,在他的內心深處也發出了另外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同樣悲慟,但是是一種力求維護自我王的尊嚴一種悲慟,這是一種反抗:“讓我的心里激起了剛強的怒火,別讓婦人所恃為武器的淚點玷污我的男子漢的面頰!不,你們這兩個不孝的妖婦,我要向你們復仇”。這兩種相左的聲音在李爾王的內心激烈的搏殺,讓李爾王處在了妥協與反抗,放棄尊嚴與堅守尊嚴的尷尬境地。
另外一種復調敘事的表現形式是角色與角色之間的沖突,這不僅包含雙重對立的角色沖突,也包括了多重角色沖突的對立,《李爾王》中,角色之間的對白中有著極為鮮明的對話色彩,這種色彩不僅代表著對他人的觀點的一種反駁,同時也是對自我立場的一次宣明,這種對話就有了雙重的指向性。我們不難看出,前一個沒有是女兒對李爾王的拒絕,那第二個沒有則是李爾王對小女兒不聽從自己的一種反駁,宣泄著自己的不滿,宣揚著自我的權威,暗示著自己的女兒,如果依舊漠視著自己的話語權,那么她將一無所有。
毫無疑問,這兩種復調敘事手段給《李爾王》添色不少,對于人物塑造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李爾王》的復調敘事手段不僅給觀者讀者創造出一個個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而且讓觀者讀者能夠了解到當時莎士比亞的內心狀態。
二、復調敘事的時代內涵
莎士比亞用這兩種復調敘事手段貫穿著全文的故事情節發展當中,成為沙劇的一大藝術特色, 那么它的意義在于它具有極為鮮明的時代內涵,一方面它展示出莎士比亞等文藝復興家在資本主義啟蒙時期的復雜心態,另外一方面它給我們展示出了封建制度沒落下的上層建筑的消亡。
莎士比亞賦予了人物矛盾的心理狀態,以及人物與人物之間的矛盾狀態,在這種復調敘事的情景下,《李爾王》中的悲歡離合實際上就是莎士比亞在面對舊有制度走向衰落的一種復雜情緒的展示,它人物內心的獨白代表這莎士比亞的內心沖突,差別在于莎士比亞作為俯視者的身份去審視著自己內心發生的一切,在這種情景下,他沖破內心枷鎖的束縛,但是沖破枷鎖后的可能性就是另外一個枷鎖,所以在舊有制度下,莎士比亞讓李爾王在衰落的制度下去憧憬,去構想,最后他筆下的復調敘事又讓李爾王的幻想偏離了讀者想象的角度,《李爾王》代表了莎士比亞在面對人文主義精神,宗教信仰,制度構想中存在著矛盾,在舊有的價值觀與新現的價值觀下,莎士比亞難以取舍。
好的戲劇的真正魅力在于作者能將有限的對話勾勒出一個個豐富飽滿的人物形象,推動者故事情節的發展,而復調敘事的藝術手段是人物形象更加立體真實,同時也豐富了戲劇本身的文化內涵,表現了作者的價值取向。毋庸置疑,《李爾王》作為一部流芳百世的優秀戲劇作品將這種復調敘事手段運用地爐火純青,這也是成就莎士比亞文壇巨匠的重要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威廉·莎士比亞.李爾王[M].朱生豪,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
[2]羅益民.從動物意象看《李爾王》中的虛無主義思想[J].北京大學學報(外國語言文學專刊),1999:128-136.
(作者單位:湖南省雅禮中學,湖南 長沙 4100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