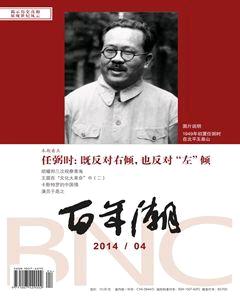鄧小平的健康秘訣
傅志義 明紅
1980年8月15日10時,解放軍總醫院領導和保健辦公室負責同志找我談話,決定派我到鄧小平身邊做專職醫療保健工作,并說次日就把我送過去。聽到組織的這個決定,我又驚又喜,同時又感到責任重大,深恐力不從心。領導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勵我說:“放開膽量,試試看。”
我給鄧小平當保健醫生時,他已是76歲高齡了。讓我驚奇的是,盡管他年事已高,又歷經坎坷,但仍紅光滿面、精力充沛,身體非常健康。
鄧小平從不吃補品,唯一算作“補品”的,是每天吃幾丸大粒維生素。我在他身邊工作三年,竟從沒見他患過感冒,也很少見他吃藥。記得最清楚的“病”,是他的血脂一度偏高。我們讓他服草決明汁治療,草決明汁又苦又澀,他端起碗,嗅了嗅,仰起脖子,一飲而盡。并風趣地說:“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嘛!”
每天早晨8點,鄧小平一般就會醒來,按響電鈴,值班護士進去給他測量血壓。洗漱后,就在書房兼辦公室里喝杯牛奶,吃根油條;接著就是一邊喝濃茶一邊批閱文件。他杯子里的茶葉放得很多,待全部泡開,要占杯子的2/3。他喜歡喝四川、安徽出產的青茶,有時也喝西湖龍井茶。鄧小平的辦事效率很高,一般在10點鐘左右就會將秘書們送來的各種重要文件處理完畢。之后,如有會議或外事活動,便乘車外出;沒有,就坐在沙發上看看書報、打打橋牌,活躍活躍腦子。
鄧小平的生活很有規律,早餐8點半,午飯12點,晚飯6點半,幾十年不變。他吃飯從不挑東揀西,廚師做什么,就吃什么。他最愛吃四川家鄉風味菜肴回鍋肉、扣肉、粉蒸肉、大肥肉等,還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蘿卜絲等。他家有個規矩——不浪費,剩菜剩飯一律下頓做成燴菜、燴飯接著吃,就是燉菜剩下的湯,都要留到下頓下面吃。鄧小平曾風趣地說:“湯最有營養。不會吃剩飯的是瓜娃子(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鄧小平健康的身體得益于運動。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他總要抽出時間,在自家的院里散步。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來回走動。他散步的習慣是在1959年養成的,那時他的腿骨折,為了恢復腿的功能開始鍛煉。之后幾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他對待散步像對待工作一樣認真,不偷懶,不取巧,不抄近道,不拖泥帶水。他家的院子最大外緣約140米,鄧小平每天固定走18圈,散步時目不斜視,步履堅定,沉默無語,不用別人提醒,絕對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鄧小平還愛好游泳,且從不到人造的游泳池里游,而是愛在大海里暢游。他說在大海中游泳自由度大,有股氣勢。在大連、秦皇島等海濱城市療養、視察時,他幾乎天天都要下海一游。他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機會,天再冷,浪再大,他都樂此不疲。甚至下大雨,他也要下海去游。我們工作人員從安全的角度進行勸阻,他笑著說:“你們不懂,水里是暖和的,雨天游泳才舒服。”他每次下海,采用的都是蛙泳姿勢,頭從來不潛入水中,一個姿勢要游一個多小時。他游泳的時間、水平,讓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自嘆弗如、望塵莫及。每次游泳,岸上都有人專門掌握時間,時間一到,便搖小紅旗通知“撤退”。有一次,游到中途下起了大雨,岸上搖起了小紅旗,催他上岸。鄧小平說:
“他們搖早了,還不到時候。”他游興未盡,仍勇往直前。
鄧小平在家也好,外出視察也罷,習慣于星期六午休后洗一個熱水澡。我們常常在他的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漿,這樣做對老年人干燥的皮膚能起到較好的養護作用。
抽煙是鄧小平多年來不曾改變的嗜好。我作為保健醫生,當然知道抽煙有害無益,但具體問題應具體對待,像他這樣有著多年煙齡的“老煙槍”,如果一下子戒了,反而會引起機體平衡失調,危害更大。況且他當時在抽煙問題上已經做了最大克制。平時在家辦公基本上不抽煙,會見外賓或參加重大國事活動,也盡量少抽煙。有時,我見他一邊跟外賓談話,一邊習慣地從茶幾上拿起一支煙,在手里轉來轉去欲吸又止,最后還是又放下了。后來,他徹底戒了煙,時間是1989年退休后。
鄧小平的健康長壽曾引起世人的極大關注,國內外許多報刊做了不少文章。《中國紅十字》雜志載文說:在世界政壇享有崇高威望的鄧小平,每天晚餐時飲兩小杯用純中藥浸的補酒——長壽長樂補酒。這種補酒,對鄧小平的身體健康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長壽長樂補酒是純天然滋補強壯劑,醇酒浸良藥,借助酒力將藥力通達四肢經絡血脈,調節陰陽氣血,平衡人體機能,從而使人延緩衰老。
據我觀察,鄧小平健康的秘訣主要有三:一是生活很有規律,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分配得很合理,飲食上不暴飲暴食;二是心態平和,對任何事都有自己獨立的思考,情緒從不受外界干擾;三是富有天真心,并喜歡和孩子們在一起,樂趣多多。
人們常說隔代親,鄧小平也不例外。每天上午10點左右,他會放下手中的工作,一邊舒展筋骨,一邊走到“老祖”(夏伯根老太太,鄧小平的繼母)的房間,看看住在那里的小外孫女羊羊(鄧榕的女兒,當時只有兩歲多),與咿呀學語的羊羊說上幾句話,問吃問喝,并拉著她的小手逗玩一會兒,樂趣融融。
鄧小平的家是四世同堂,上有“老祖”,下有孫子孫女,老老少少十幾口人,照民間的說法,真可謂兒孫滿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飯,是一大家人相聚最齊的時間。10多個人分坐兩桌,子女們邊吃飯邊聊天,從國家大事說到社會新聞,很有一些“信息交流中心”的味道。大家七嘴八舌,但鄧小平卻從不發表意見,只是默默地吃飯。他喜歡這種輕松活潑、民主融洽的氣氛。有時飯桌上少了幾個人,大家說話少了,他就會說:“哎呀!今天怎么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見哪個孫子,他也會關心地問:“到哪里去啦?”
鄧小平是舉世矚目的偉人,他的身體狀況特別受到公眾的關注。我在他身邊工作的日子里,經常看到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外新聞媒體捏造他身體狀況的報道。有一年夏季,我們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下午,警衛處張寶忠拿來一張報紙給鄧小平看,上面刊登著外國記者捏造的“鄧小平遇刺,被貼身保鏢護救,保鏢已身亡”的消息,而張寶忠就是這條消息中所說的“保鏢”。鄧小平看后微微一笑,不屑一顧,什么也沒有說,我們也覺得很可笑。
當時,我不知道鄧小平在想些什么。幾年后他才說:“我歷來不主張夸大一個人的作用,這樣是危險的,難以為繼的。把一個國家、一個黨的穩定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問題。”我還注意到,鄧小平在會見客人時,曾談起新聞媒體又有兩次謠傳:一次是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李政道教授時提到:“最近香港傳說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場波動。這說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一次是1990年5月13日,鄧小平在會見埃及老朋友穆巴拉克總統時提到:“前兩三天香港報紙說我已經不在了,我很高興你見到的是一個活人。”
許多回憶領袖的文章都愛用“通宵達旦、日理萬機”等詞語來形容領袖們的工作態度。我卻發現鄧小平是個非常注重工作效率,也特別善于處理工作與休息關系的偉人。
鄧小平曾對外國朋友說過:“我的工作方法是盡量少工作。”美國記者華萊士采訪鄧小平時,問他每天工作多長時間,他伸出兩個手指頭:“兩小時。”華萊士聽后,頗為吃驚。作為他的保健醫生,我計算過,如果不包括會見外賓、開會及外出視察,他每天8點至10點坐在辦公桌前,工作也就兩小時左右。
然而,他的工作時間遠遠不只坐在辦公桌前的這部分。據統計,我在鄧小平身邊工作的3年時間里,他先后會見外賓187次,接受外國記者采訪7次,參加各種重要會議61次,追悼會7次,與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會見黨外朋友21次,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負責同志談話5次。還有10次離京到全國23個城市視察,以及一些無法統計的事務,比如在北京市區參加植樹活動等等。如果把這些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話,是相當驚人的。這些數字,對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摘自《真相——中共風云人物錄(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