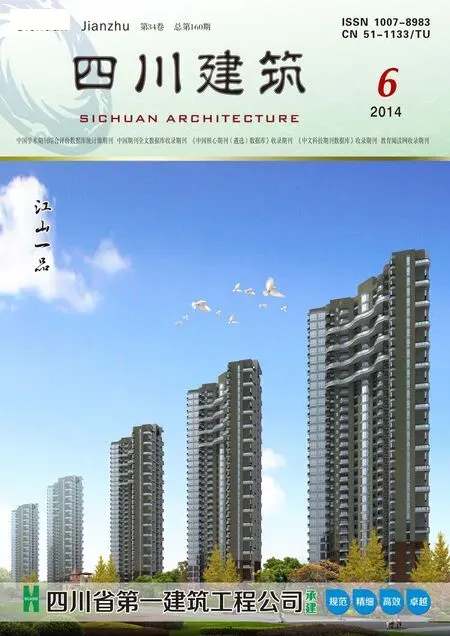自閉癥兒童康復花園園藝療法初探
張加軼, 郭庭鴻
(西南交通大學建筑學院,四川成都610031)
自 Kanner(1943)提出關于自閉癥(Autism)的相關概念以來,關于其成因與治療方法的研究一直在進行。隨著在遺傳學,行為學等領域的研究深入,針對于自閉癥的治療也逐漸形成。目前,自閉癥的成因仍不明,現階段治療方法以自閉癥兒童的三個發育障礙(人際互動發育障礙、語言溝通障礙、行為刻板)作為治療研究的出發點,主要通過教育介入法(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從身體機能、思維模式以及交流方式的訓練中矯正患兒相應能力[1,2]。目前相應的干預性教育訓練,均有或多或少的積極療效,但是在能力綜合性應用上的局限性亦很明顯[1]。康復花園是起源于醫療環境的園林景觀類型,強調應用自然元素多途徑促進人體恢復。園藝療法是從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治療、理療、職業訓練的方式,通過人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促進人體恢復,尤其強調對患者的生理與心理共同調試的治療方法[3]。本研究綜合多學科分析的方法,理論結合實踐,嘗試將康復花園園藝療法作為自閉癥兒童干預性治療措施,以期對兒童自閉癥的治療作有益探索。
1 自閉癥兒童的訴求分析
兒童自閉癥矯治的根本目標是促使其生理機能的發展以及心理的正常社會化,并且獲取自理和社交的技能[4]以此為目標,可將自閉癥兒童的訴求歸結為兩類,一是,針對自閉癥兒童自身基礎行為能力的康復需求;二是,最終實現自閉癥兒童內在世界與現實世界溝通和適應。前者的實現是后者實現的基礎,后者則進一步促進前者的康復過程。患兒之間生理心理的發育層次差異性較大,不同時間階段能完成的活動的類型不同,需根據個體差異將不同類型個體和康復階段的康復活動類型分步進行[5-7]。
2 兒童自閉癥干預性治療的康復花園園藝療法
園藝療法是對于有必要在其身體以及精神方面進行改善的人們,利用植物栽培和園藝操作活動,從社會、教育、心理以及身體諸方面進行調整更新的一種有效的方法[8]。康復花園園藝療法,是在康復花園中進行的園藝療法。20世紀70年代,凱戈爾博士等人的研究強調了在自然的教育環境中進行自閉癥兒童的訓練的重要性,并促進了“自然教法”在幼兒自閉癥治療中的長足進展[9]。郭庭鴻整合了康復花園的醫療特性,并從自閉癥兒童的康復訴求的角度,提出康復花園借助自然和人工景觀的手段作為患兒干預治療的理論可能性[10]。諸多研究表明園藝療法對于自閉癥患兒的社會交往障礙有顯著的干預效果[11]。
康復花園園藝療法為自閉癥兒童干預性治療措施提出新的假設,提出康復花園的靜態助益與園藝療法的動態助益相互促進增進康復功效的可能性。
2.1 康復花園及園藝療法康復理論介紹
園藝療法的康復理論和康復花園康復理論之間有很大的共通性,在一定程度上園藝療法的康復效果是在建立在康復花園之上的,即園藝療法是以康復花園為載體的主動的康復過程。
2.1.1 注意力恢復理論(The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
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發現,人類的意識是有兩不同種類型——定向意識(Directed)和自發意識(Spontaneous)。Kaplan等人發現人們在無定向刺激,或刺激物在可控范圍的場所易產生自發意識(Spontaneous)。不同于定向意識(Directed),人們在無意識的狀態下進行的自動的反應機制,使得人們的精神從壓抑機制中解脫出來;精力得到恢復[12-14]。
2.1.2 情感美學理論(Affective Aesthetic Theory (AAT))
AAT認為不同的視覺刺激與人類的幸福、冷靜、減壓的相關心理與生理反應直接相關聯[15-17]。并且定義壓力是一個由外部和內部不利刺激引起的人體生理和心理上的反饋過程;人們只有通過調整自身行為和生理功達到身心的平衡。情感美學理論認為,一個恢復的過程是一個場景引起的舒緩的平和與幸福感。這個理論亦受到生命假說和心理進化理論的部分觀點的影響。受到水、綠色植物等自然界的視覺刺激,使人們產生本能的情緒放松的反應,而這都是源自于進化起源中生存與安全的基本認知。
2.1.3 機械論-分形(Mechanistic Theories_ Fractal Dimension)
機械論[18-21]研究分析了圖案的分形特征和這些圖案被感知到的視覺質量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圖片自身的分形維數(D)為變量,得到人們的美學偏好為D=1.3。而這個分形維數值在自然環境中經常出現,這個結論同時解釋了人類在自然界的進化,視覺偏好就被“設定”在了D=1.3(Aks & Sprott)。當分形刺激D=1.3時,誘導最大的腦電圖反應變化,對應最大α反應在額葉區和最高的β反應在頂葉區域。這樣的研究結果能部分解釋D=1.3與人類的偏好、幸福和自然之間的關系。
2.1.4 大腦的機制和心神寧定理論(Brain Mechanisms and Tranquillity)
神經機制和寧靜平和的景觀刺激,與自身的身心健康之間存在關聯性[22-23]。心神寧定的心理特征是冷靜和自我反省,這樣的心理狀態更可能發生在平和寧靜的環境中。安靜環境下的環境調節效應,在聽覺皮層和內側前額葉皮質之間的有效連接形成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實驗結果表明,場所與主觀內心的寧靜之間的聯系可以從聽覺皮層和內側前額葉皮質之間加強的連接得出結論。這一理論在神經生物學的層面上得到了理論支持,即肯定了自然對自我反省和心神寧定的精神狀態的影響。
2.1.5 彈性理論(Resiliency Theory)
“彈性”是一種從挑戰和困境中反彈恢復的能力[24],是在多種境況下處理事情的穩定狀態,態度和方法。通過對個人能力的強化可以促進個體對生活控制能力的感知,對自身的感知,從而對自身重新定位;由此產生意志去克服困境;社會的支持同時也會在逆境中起到緩沖作用。
2.1.6 沉浸理論(Flow Theory)
沉浸是一種身心體驗[25],在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處境包含符合他能力可以完成的機會和挑戰的時候產生。當挑戰的難度與挑戰者自身能力相近或者略高時,挑戰者樂于擴展自身的能力去學習新的技能,有助于提高他的自尊心,以及社會適應能力。
總的來說,不同的學說和理論都驗證了進入人工綠化場地和自然環境對人們的身心健康不同方面的重要性,以及人們從事園藝活動中的狀態對人們健康的助益。康復花園成為具有治愈作用的特別是:有助于學齡前兒童提高注意力(M?rtensson等);增強身體活動的時間與功效 (Thompson Coon等,Maas 等);減少暴力情緒(Kuo & Sullivan);提高自信心和自尊心(Barton & Pretty)[26]。
2.2 康復花園園藝療法活動作為自閉癥兒童干預性治療的特性
根據山本寬的相關研究[27],結合自閉癥兒童相關治療特性得出本表格(表1)。

表1 園藝療法活動作為自閉癥兒童干預性治療的特性
2.3 康復花園園藝療法作為自閉癥兒童干預性治療分析
康復花園的醫療特性:整合性(Integrity)、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兼容性(Compatibility)、自然性 (Nature)[10],使其成為絕佳的園藝療法活動的承載體。康復花園作為園藝療法的運行環境,不只是階段性的助益條件而是一個持續的助益過程。
園藝活動多樣可以滿足不同治療階段患兒的康復需求,并且步驟簡單明確易于理解與操作。作為一個半開放性的康復構架,園藝療法易于吸收當前兒童自閉癥典型療法的原理與方法,并根據具體情況做出靈活調整。同時,園藝療法活動步驟與產生的社交活動都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關;不但有益于恢復患兒的生理功能,同時提高職業技能,并增強社會適應能力。康復花園園藝療法成為形成自閉癥兒童與社會之間的緩沖空間。通過園藝治療過程潛移默化的影響,促進患兒與社會的雙向溝通與銜接,促使患兒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康復體系下恢復自身與社會的關聯性,以此實現在外界有限的幫助下自理生活的目的。
康復花園園藝療法整合康復花園與園藝療法,形成由靜態助益與動態助益、自然助益與人工助益組合的面向患兒與社會雙向開口的互相理解的平臺,以及幫助自閉癥兒童克服身心障礙的康復空間。患兒的治愈效果的保證。
3 自閉癥兒童康復花園園藝療法應用實踐
成都市“小星星兒童心理康復中心”是一家致力于自閉癥兒童康復訓練和研究的非營利民間機構。“小星星”與靚園康復療養會所合作,嘗試建設自閉癥兒童園藝療法花園于會所的康復療養環境之中(圖1)。
并與自閉癥兒童NGO組織遙遠星球的守護者志愿者聯盟(The Guardiannof the Distant Stars Volunteers Alliance),豆苗計劃志愿者聯盟(Beans Plan Volunteers Alliance),以及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Angel Heart Family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合作形成跨專業團隊,組織五位患兒參與為期三個月(2012-9-15至2012-11-10)每周一次每次3~4 h,以大田種植、收獲,以及樹葉拼貼畫活動并行的園藝療法活動(圖2~圖4)。

圖1 靚園康復療養會所平面

圖2 園藝療法活動-大田種植

圖3 園藝療法活動-收獲

圖4 園藝療法活動-樹葉拼貼畫
研究者采用質性研究法通過對患兒的參與式臨床觀察,與家長以及專業人士一對一的半開放型深度訪談,初步驗證了在共同注意力以及社交技能的康復提高。
4 小結
自閉癥兒童康復花園園藝療法綜合了醫學、景觀設計學、特殊兒童教育等多學科的治療手法,對于拓展和深化相關學科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通過借鑒、優化、整合康復花園、園藝療法以及兒童自閉癥各種治療模式的特點及基本原理,嘗試建立一種的自閉癥兒童康復花園園藝療法模式,提出探索自閉癥兒童療法的新思路。同時,作為實驗性的應用嘗試,相關的研究尚有待深化。
致謝:本課題研究得到了成都市小星星兒童心理康復中心的技術支持,豆苗計劃志愿者聯盟(Beans Plan Volunteers Alliance)、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Angel Heart Family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以及遙遠星球的守護者志愿者聯盟(The Guardiannof the Distant Stars Volunteers Alliance)提供志愿者服務。案例資料由立昂設計(www.dongleon.com)提供,特此致謝。
[1] 徐大真,侯佳.兒童自閉癥治療技術與方法的研究進展[J].消費導刊,2008,(12):188-190
[2] 徐大真,侯佳,孔存慧.自閉癥治療理論與方法研究綜述[J].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09,(2)
[3] America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sociation Definitions and Positions[EB/OL]. http://ahta.org/sites/default/files/DefinitionsandPositions.pdf
[4] 華煒.兒童自閉癥干預新路向-整合治療模式[J].社會工作,2011,(12):37-40
[5] 王純.自閉癥兒童的感覺統合訓練療法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6,(5)
[6] 蔭山英順,徐光興.自閉癥兒童的精神統合療法[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4,(1)
[7] 王靜,王敏.人際關系發展干預療法(RDI)及其對自閉癥兒童訓練的啟示[J].教育教學研究,2011,(1):132-133
[8] 李樹華.園藝療法的起源與發展[J].農業科技與信息(現代園林),2013,(4)
[9] 黃偉合.現代行為心理學對幼兒自閉癥的治療及其效果[J].中國行為醫學,2001,10(4)
[10] 郭庭鴻,董靚.兒童孤獨癥康復花園輔助療法初探[J].中國康復理論與實踐,2013,(2)
[11] 郭成,金燦燦,雷秀雅.園藝療法在自閉癥兒童社交障礙干預中的應用[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12]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s. 1& 2). New York: Holt.
[13] Kaplan, R., Kaplan, S. & Ryan, R.L. (1998). With people in mind: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everyday nature. Washington: Island Pr
[14] Kaplan, S. & Talbot, J.F. (1983).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 wilderness experience.Human Behavior &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 Research 6, 163-203
[15] W?hrborg, P. (2009). Stress och den nya oh?lsan [Stress and the new disease scenario]. 2. ed.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16] Ulrich, R. (1983). Aesthetic and affective respon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6, 85-125
[17] Wilson, E. (1984). Biophilia: The human bond with other spec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ISBN 0674074424
[18] Mandelbrot, B.B. & Blumen, A. (1989). Fractal Geometry: What is it, and What Does it do [and Discu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423(1864), 3-16
[19] Pentland, A.P. (2009). Fractal-based description of natural scenes.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IEEE Transactions on (6), 661-674
[20] Aks, D.J. & Sprott, J.C. (1996). Quantifying aesthetic preference for chaotic patterns.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arts 14(1), 1-16
[21] H?gerh?ll, C.M., Laike, T., Taylor, R.P., Küller, M., Küller, R. & Martin, T.P. (2008).Investigations of human EEG response to viewing fractal patterns. Perception 37(10), 1488
[22] Herzog, T.R. & Barnes, G.J. (1999). Tranquility and prefere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2), 171-181
[23] Hunter, M.D., Eickhoff, S.B., Pheasant, R.J., Douglas, M.J., Watts, G.R., Farrow, T.F.D., Hyland, D., Kang, J., Wilkinson, I.D., Horoshenkov, K.V. & Woodruff, P.W.R.(2010). The state of tranquility: Subjective perception is shaped by contextual modulation of auditory connectivity. NeuroImage 53(2), 611-618
[24] Fine. S. B. (1991). Rcsilience and human adaptability: Who rises above advers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45.193-503
[25] Csikzentmihalyi, M.(1990).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Brooks/Cloe
[26] Annerstedt M. Nature and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Promotion,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D]. 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lnarp :Faculty of Landscape Planning Department of Work Sciences, Business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2011
[27] 李樹華.園藝療法概論[M].中國林業出版社,2011:82-83
[28] 張文英,巫盈盈,肖大威.設計結合醫療——醫療花園和康復景觀[J]. 中國園林,2009,(8)
[29] 章俊華,劉瑋.園藝療法[J].中國園林,2009,(7):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