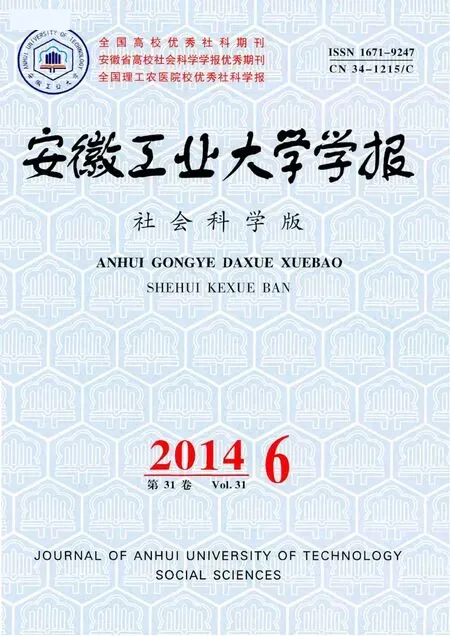中式英語的社會身份解讀
徐麗麗
(馬鞍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教師教育系,安徽 馬鞍山 243041)
?
中式英語的社會身份解讀
徐麗麗
(馬鞍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教師教育系,安徽 馬鞍山 243041)
摘要:中式英語是跨語言影響的產物,但對其作為語言學符號的社會身份存在疑義。中式英語的新發展表明,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增長的信心正在轉換為對中式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學符號的社會身份合法性的再評估。
關鍵詞:中式英語;跨語言影響;語言學符號;社會身份
作為語言學中的一種奇特現象,中式英語通常被認為是不符合標準英語的一種不正確的或畸形的英語。長期以來,英語教學研究者對是清除它還是接受它作為標準英語的一種變體爭執不斷。近年來,中式英語最新的發展動態再度引發人們對其社會身份的關注。
一、中式英語的新發展
語言學者瓊·皮卡姆(Joan Pinkham)指出,平實的英語以動詞為基礎,它簡潔、有力且不失其首要特征——清晰。中式英語(Chinglish)則基于模糊、籠統而抽象的名詞,它復雜、冗長,呆板而晦澀。[1]這些語言常沒有什么意義,或者顯得滑稽可笑。然而,據人民網2014年4月18日報導,網絡熱詞“no zuo no die”(不作死就不會死)被美國在線俚語詞典UrbanDictionary收錄。此前,2013年8月,《華爾街日報》專門使用“Dama”(大媽)這一源自漢語拼音的單詞,關注中國中老年婦女引領全球黃金價格的上漲。[2]同年,同樣源自漢語拼音的“Tuhao”(土豪)一詞也頻頻在西文媒體中出現。據媒體報道,《牛津英語詞典》的編纂者甚至考慮在2014年把它收錄進詞典。[3]2011年7月,南京市政府把“Day Day UP”作為2014年青奧會6句候選口號之一,就曾經引發熱議。
實際上,十多年前,一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式英語就逐漸被關注并接納。例如,漢語中的“guanxi”(關系)一詞被英美國家的商學院教材RulesandNetworks收錄。近年來,在海外媒體的報道中,取自漢語拼音的英語單詞不斷增多。如指未婚男士的“guanggun”(光棍),把激進的年輕人譯為“fenqing”(憤青),將海外的中國消費者譯作“chinsumer”。類似的例子還有諸如:shuanggui (雙規),chengguan (城管),don’train (動車),geilivable (給力)等。
全球語言監測機構(GLM)的數據顯示:1994年以來加入英語行列的詞匯中,中式英語貢獻了5%~20%,超過任何其它語言來源。互聯網上中式英語支持者的數量在不斷上升,中式英語的新變體也不斷涌現,大量的漢語詞語成為英語新詞最主要的來源。這些新造的中式英語多是把兩個英文單詞巧妙嵌合,符合英語的構詞規則,同時具有相關中文或英文的諧音,既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熱點,又蘊含著中國網民特有的幽默感。[4]難怪連部分外國人都覺得中式英語“韻味十足”,“有趣、甚至有意義。”
從“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的幽默搞笑,到諸如“no zuo no die”,“Long Time No See”被英文詞典正式收錄,再到網絡流行語諸如:“土豪”(Tuhao)、“中國大媽”(Dama)等被英文媒體廣泛接受,中式英語正在使英語發生深刻的變革,中式英語的新發展促使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現象。
二、作為跨語言影響產物的中式英語
英國語言學家Alexander指出,“由于受母語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式英語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外語學習中的一種普遍現象。”[5]有資料顯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學英語人口。同時,每天還有不斷增長的說英語的人加入大陸幾百萬個中-英雙語的群體中。[6]如此龐大規模的學英語和說英語的人群自然會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英語變體。
一般而言,中式英語具有幾大語法遷移的特征,也稱之為跨語言影響。由于缺乏從周圍環境或本族語教師和相關人士那里高質量的語言輸入,那些從未走出國門僅在學校學英語的中國人尤其會受其影響。[7]首先是語音維度的遷移。例如:漢語中沒有[] 和[θ]這兩個音,因此,中國人通常用同它們相近似的[z]和[s]代替,把mother ['m→]讀成[['mz]],thought [θ: t] 讀成[s: t]等。
其次是語法維度的影響。學習者通常依賴母語語法模式以彌補他們對目標語掌握的欠缺。對于龐大的說外語群體來說,這種遷移的結果導致把英語的基本形式同漢語的某些語法特征結合在一起,產生一種“中介語”(interlanguage)。[8]弗吉尼亞·易卜(Virginia Yip)在研究了大量中國學生的口頭和書面語材料之后發現,漢語和英語之間關鍵的差異在于漢英兩種句子結構突出的重點不同。前者強調“主題”(topic),而后者強調“主語”(subject)。例如:這棵樹葉子很大(this tree leaf very big.)與“This Tree, (its)leaves are very big”。中國人傾向于把主題信息“This Tree” 放在突出位置,而不是主語信息“leaves”。[9]
中國學生在說英語時也常常按照同樣的規則,例如:“My little sister, everybody likes her.”這樣的句子。此外,中式英語還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即把副詞短語置于句子的主語之后。
第三是語用維度的影響。社會語言學研究認為,中式英語是與英語說話規則存在語用差異的產物。漢語對英語的跨語言影響意味著源自漢語影響的英語話語同對說話者的價值評判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例如,相對于中式英語的稱謂,弗吉尼亞·易卜更傾向于使用“漢語-英語中介語”(Chinese-English Interlanguage)這一專業術語,以表明中介語形式是學習者在達到流利程度之前產生的一種暫時的語言學的表述,而非語言體系的一種永久特征。
有人把跨語言影響看作是英語的中國式變體自成一體的、相對穩定的特征(稱為中國英語)。這種變體可作為一種實用的本土語言,是世界英語的一種本土化形式。但是對于中式英語這一稱呼,他們并不認同。[10]紐瑞·維達奇(Nury Vittachi)認為,有些中式英語的短語不僅在漢語言系統中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值得期待。他以“How to spell?”為例,盡管這一短語不符合英語語法,但是卻常常引出對話中的重要信息;在拼寫與讀音不完全匹配的語言學語境中,這種提問特別有用。[11]
金斯利·博爾頓(Kingsley Bolton)把中式英語(特別是香港英語的變體)放在英國人首次同中國接觸更廣的歷史背景中來考察。他發現香港地區英語的獨特性扮演著保持香港獨特的身份的一種工具——尤其在香港回歸后。他所描述的香港英語的語用規則直接指向要給這種變體提供一定的“空間”。[12]從此種意義上來說,中式英語實際上被看作是在不斷變化的政治環境中一種新型社會語言身份認同的工具。
三、對中式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學符號的疑義
中式英語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但迄今對其并無準確的界定。研究者分別用中國英語(China English)、中國式英語(Chinese English or Chinglish)、漢化英語(Sinicized English)等詞語來稱呼這一特殊的語言現象。在長期給中式英語糾錯的背景下,中國學者通常把出現在中國的英語變體稱之為“中國英語”,而把“中式英語”當作是一個由英文單詞Chinese與English組合的不受歡迎的混成詞,含有輕蔑和貶損的社會涵義。中式英語被疑義的語言學符號的社會身份主要源自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在西方的語言等級制觀念中存在一種假設,認為只有熟練掌握主流語言(標準英語)才代表著完美的文化能力和社會聲望。反之,非標準語言被解讀為不是缺乏天賦,就是標志著未接受良好的教育。[13]中式英語的前身是洋涇浜英語。有學者指出,洋涇浜英語在詞匯和語法方面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支離破碎、似通非通、笑話連篇、洋相百出。洋涇浜這個詞含有特定的含義,以至于一提到它,就令人想起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舊中國。[14]洋涇浜這種稱謂無疑把種族的烙印和它所代表社會和文化身份聯系在一起。
第二,中式英語產生于對媒體、教育機構和人們日常交談中的話語的一種大眾化的闡釋。厄瑞克·亨利(Eric Henry)認為,同語言學研究不同,判斷母語為漢語者所說的英語是否為中式英語并不僅僅依賴于這種語言的符號特征。相反,這種判斷主要根據漢語為母語者同外國聽眾之間主體間的動力(intersubjective dynamic)。中式英語的標記可以以多種方式附屬于話語上,而且意味著多重的后果和涵義。[15]在中國,英語受不同的權力關系的影響,某些人憑借這些權力(老師、本土語者、語言學家)擁有評判他人話語的權威。各種語域的社會價值可以共享,但是有權把某種話語貼上屬于某種或另一種語言形式標記的人只能是那些專業人士,他們通過掌握特定的符號資源(擁有大學文憑、有海外學習生活經歷、同國外保有聯系等方面)能夠獲得解釋他人話語的權力。
背離了公眾普遍接受的平實而清晰的英語被聽眾認為是不正確的、難懂的,因此指責說話者不能合乎邏輯地表達事物。這常常同說話者明顯的困惑所暗含的吸引力和幽默同時發生。希爾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指出,“對于‘充滿真理’的標準英語來說,以不同于本族語規則表示的英語的形式沒有什么意義。某種語言變體的價值實際上代表了人和他們各自的階級和地位關系,轉喻為代表說話者本身的社會價值。”[16]因此,不管根據什么分類標準,對中式英語的判斷同它的內容無關,重要的是說話者和評判者之間主體間的互動關系,特別是后者的權威性、專業性和社會資本的相關水平。
第三,中國的英語學習者無疑也存在一種精英身份認同的情結:即說好用好流利地道的英語不僅是一種溝通的需要,更是著一種身份的象征。厄瑞克·亨利在中國沈陽地區進行調查,采訪對象包括:中外英語教師、學校的管理者、學生家長和學生本人,“中式英語”是他們普遍的擔憂。教師和學生都把這個詞貼上貶義的標簽,認為它是指非標準的、受漢語影響的畸形英語。[15]這種認同公開把中式英語解釋為會造成理解障礙,暗示著對說中式英語人的負面的價值判斷。
四、結語
把中式英語和英語截然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如今,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推動并確保了普通大眾參與到現代化和全球共同體融合的進程中。中式英語的傳播既具有幽默又具有規范性的效果,這決不是巧合。在某種意義上,外國人對可能消失的中式英語的情有獨衷,其實也是在哀嘆為它提供支撐的專家意見的結構和西方在語言領域內的主導權正在遭受侵蝕,是對中國在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主要是英語國家)關系中不斷增強的話語權的矛盾情感的流露。從最初示人的幽默搞笑,到中國“Dama”與“Tuhao”所表達的“中國概念”,中式英語近年來的新發展表明,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增長的信心正在轉換為對中式英語作為一種語言學符號的社會身份合法性的再評估。
參考文獻:
[1]Joan Pinkham.Thetranslator’sguidetoChinglish[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170.
[2]張意軒:中式英語幽默風靡全球 卓越語言貢獻彰顯國力[EB/OL].[2014-04-05].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8/28/c_117118832.htm.
[3]Michelle Florcruz.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Considers Adding “Tuhao”, A Chinese Slang Term in Future Edition[N].InternationalBusinessTimesNov.20, 2013.
[4]蒲曉燕.中式英語前景觀[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24):124-126.

[6]D.Crystal.Two Thousand Million? [J] .EnglishToday, 2008(24): 3-4.
[7]Susan Gass & Evangeline Varonis.Input, Intera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Production [J].Studies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 1994(16): 283-302.
[8]Larry Selinker.Interlanguage [J].InternationalReviewofAppliedLinguisticsinLanguageTeaching, 1972(10): 209-231.
[9]Virginia Yip.InterlanguageandLearnability:FromChinesetoEnglish[M].Amsterdam: John Benjaminis, 1995:75.
[10]Wei Yun & Fei Jia.Using English in China [J].EnglishToday,2003(19): 42-47.
[11]Nury Vittachi.From Yinglish to Sado-Mastication [A].in Kingsley Bolton ed.,HongKongEnglish:AutonomyandCreativity[C].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29-56.
[12]Kingsley Bolton,.The Sociolinguistics of Hong Kong and the Space for Hong English [A].in Kingsley Bolton ed.,HongKongEnglish:AutonomyandCreativity[C].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2:31.
[13]Holger Kersten.America’s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Pidgin English”[J].AmericanStudies, 2006,51(1):75-76.
[14]張南達,劉雋姬.洋涇浜英語 [J].中國科技翻譯,1992,5(3):44-45.
[15]Eric Steven Henry.Interpretations of “Chinglish”: Native Speakers,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Enregisterment of a Stigmatized Code [J].LanguageinSociety, 2010, 39(5): 669-688.
[16]Michael Silverstein.Monoglot “Standard” in America:Standardization and Metaphors of Linguistic Hegemony,”[A].in Donald Brenneis & Ronald Macaulay eds.,TheMatrixofLanguage:ContemporaryLinguisticAnthroplogy[C].Boulder: Westview , 1996:9.
(責任編輯文雙全)
AnInterpretationoftheSocialIdentityofChineseEnglish
XULi-li
(The Teacher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Ma’anshan 243041, Anhui, China)
Abstract:Chinese English is a product of inter-language influence. It remains to be unclear of its social identity concerning it's being a type of linguistic symbol. It shows i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glish that the growing confidence of China around the world leads to re-assessment of Chinese English as a reasonable type of linguistic symbol.
Key words:Chinese English; inter-language influence; linguistic symbol; social identity
中圖分類號:H31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47(2014)06-0090-03
作者簡介:徐麗麗(1980-),女,安徽和縣人,馬鞍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教師教育系助教,碩士。
基金項目:馬鞍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14xjkyxm05)
收稿日期:2014-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