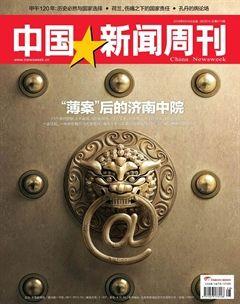鄧小平:中國不會輸出革命
吳興唐

1980年代中期,我任中聯部新聞發言人。有幾次,在新聞發布會上,多位外國記者問及中共同亞洲國家特別是同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關系。
我回答:“我國同世界各國包括亞洲國家的關系,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黨與黨的關系,遵循‘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黨際關系四項原則。我們一再聲明,我們決不干涉外國黨的內部事務,同時,也決不利用與外國黨的關系去干涉這個國家的內政。大家知道,我國同亞洲國家的關系都是睦鄰友好的。”
當然,有的外國記者還想深入問下去。于是我回答:“這是一段歷史過程。在新聞發布會這樣的場合,三言兩語是說不清楚的。如哪位外國記者對此感興趣,可以同我約時間進行交談。”
但是,沒有一個外國記者來約談。盡管如此,我還是做了有關“功課”。我想,現在來對這個問題作一歸納、比較全面地將之講清楚,也是一件好事。
斯大林提出“分工”的建議
在中國的解放戰爭時期,斯大林對中共和毛澤東并不是完全信任的。但隨著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斯大林改變了對中共的某些偏見,在對待亞洲共產黨的一些問題上,也重視并征求中共的看法。
1949年6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問蘇聯,斯大林提出了國際共運內部“分工”的建議。斯大林對劉少奇說,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承擔一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就是說要分工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國今后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多擔負些幫助的責任,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及其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能被它們參考和吸取。
中共接受了斯大關于國際共運“分工”的建議,在新中國成立后,將支持和幫助亞洲國家共產黨進行反帝和民族解放與獨立斗爭,作為中共對外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成立于1951年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簡稱中聯部)受中央委托,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具體工作。其主要形式有:
第一,協助亞洲國家共產黨制訂綱領和政策。這項工作原由蘇共負責,之后根據斯大林的意見,由中共出面進行。
在這項工作中,中共始終處于協助地位。對于這些黨的綱領,不論在斯大林生前或逝世之后,總是中蘇兩黨共同討論和制訂的,而且最后都由蘇共拍板。
比如,在1950年代,中共同蘇共一起,幫助日本共產黨解決內部糾紛,基本結束了日共中央的分裂狀態。中共還協助蘇共,為日共制訂綱領和政策。1958年7月,日共召開七大,從政治上、理論上和組織上鞏固了黨的統一、團結,為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61年7月,日共八大通過《日本共產黨綱領》。這是日共第一次獨立自主地制定綱領。
第二,提供信息,分析國際形勢和地區形勢。這些亞洲國家共產黨,有的處于地下活動狀態,有的活動范圍較小,因此信息不太靈通,迫切希望中共介紹和分析有關情況。
第三,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主要采取短期干部培訓的方式。其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即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在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局的領導下,在北京召開了亞洲、澳洲工會會議。中國、蘇聯、日本、朝鮮、印度、越南、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工會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國際性會議。會議確定,在北京建立世界工聯亞澳聯絡局。在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將中國革命道路概括為“三大法寶”,其中特別強調了武裝斗爭及建立革命根據地。
援助越南抗法戰爭和國家建設
中共支持和援助亞洲地區共產黨,還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和人員支援。其中最典型的,是對越南的援助。
越南民主共和國于1945年9月宣告成立,但此后便處在殘酷的抗法戰爭中,沒有固定的首都,更沒有獲得國際承認。1950年1月,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共產黨在一段歷史時期中的名稱)中央主席胡志明,赤足步行17天進入中國地界,秘密訪華。胡志明同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進行會談,請求中共援助越南人民的解放斗爭。中越兩黨就中國援助越南的具體措施達成協議。
應胡志明的請求,中共中央先后派出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團,赴越南幫助其進行軍事作戰和經濟建設。為了更有力地支援越南抗法斗爭,經兩黨中央商定,1950年7月,陳賡作為中共代表,赴越協助邊界戰役和處理有關援南問題。同年8月,韋國清率中國軍事顧問團抵達越南。9月中旬和10月下旬,越南采納陳賡和軍事顧問團的建議,發動了“邊界戰役”,殲敵近萬名,掃除了中越邊界地區的法軍據點,打開了中越邊境的通道。1951年12月,中國援越顧問總團成立,任命原中共中央駐越共中央聯絡代表(當時中共和越共互派聯絡代表)羅貴波為總顧問。
中國顧問團為越南抗法戰爭和經濟建設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顧問團協助越南黨中央制定了土地改革法。1954年5月,在中國軍事顧問團的協助下,越南發起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大獲全勝,為結束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奠定了基礎。中國顧問團還協助越南在黨建、統戰和經濟建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9月,中國開設駐越南大使館,任命羅貴波為首任大使,并向越方建議逐步撤銷政治顧問團和軍事顧問團,改派少數專家技術人員到越南協助工作。1956年初,中國援越顧問團的工作全部結束。
中共支持亞洲國家共產黨的原則與做法,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歷史局限的一面。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同一些東南亞共產黨就有聯系。新中國成立后,東南亞國家共產黨都從道義上聲援了被西方國家封鎖、孤立的新中國。中國支持它們是理所當然的,也是國際義務。這是其積極的一面。
從歷史局限性來說,有以下幾點:一、替別國黨制訂黨的綱領和政策是不適宜和不妥當的,并不能符合別國的國情;二、對亞洲國家共產黨,雖然也講了統一戰線,但過分強調武裝斗爭;三、雖然講了各國共產黨應把馬列主義同本國實踐相結合,但強調了中國革命道路對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爭具有普遍意義。
毛澤東:革命不能輸出
1953年朝鮮停戰之后,亞洲形勢開始發生變化。
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達成越南南北分治的協議。同年,周恩來訪問印度和緬甸,中國同印度和緬甸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政黨關系要服從于國家關系,中共隨之調整了對亞洲國家共產黨的政策。
1954年12月1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他說:“(一個國家)靠外國的幫助,靠外國輸出革命,而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就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不能輸出。”他還說,中國決不會在云南邊境組織軍隊打進緬甸,而且教育在緬甸的華僑服從僑居國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裝反對緬甸政府的政黨取得聯系。中國在華僑中不組織共產黨,已有的支部已經解散。中國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這樣做的。
1955年12月,毛澤東同泰國代表庵蓬等人談話時說:“我們也不在你們國家講共產主義,我們只講和平共處,講友好,講做生意。我們不挑起人家來反對他的政府。吳努總理害怕我們挑起緬甸共產黨來反對吳努政府,我們說,我們只承認你們一個政府,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有兩個政府。你們國內也有共產黨,我們也不去挑起他們來反對你們的政府。”
東南亞國家共產黨大多成立于1920年代或1930年代,都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下成立的。除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1921年7月成立)之外,還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印尼共,1920年5月)、印度共產黨(印共,1920年10月)、越南共產黨(越共,1930年2月)、馬來亞共產黨(馬共,1930年4月)、菲律賓共產黨(菲共,1930年11月)、緬甸共產黨(緬共,1939年8月)、泰國共產黨(泰共,1942年12月,前身是1930年創建的暹羅共產黨)。
在走和平道路還是武裝斗爭的道路上,東南亞國家共產黨與西方國家共產黨不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西方國家共產黨奉行“和平過渡”的政策,放下了武器,加入當地政府,開展議會斗爭。但東南亞國家共產黨所走的道路,卻曲折反復。
以緬共為例。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國重占緬甸。1945年7月緬共制定了以和平方式爭取緬甸獨立的和平發展路線。緬共領導的抗日武裝萬余人中,3000人編入英軍控制的緬甸國防軍,其余交出武器就地復員。
1946年2月,緬共中央批判了和平發展路線,決定開展武裝斗爭。1948年月4月緬甸宣布獨立,成立自由同盟政府。緬共發動全國大規模罷工斗爭和農民運動,自由同盟政府宣布緬共為非法。1955年11月,緬共發表聲明,愿與政府和談,政府未同意。
對此,中共、蘇共建議緬甸等國家共產黨,在條件成熟時,以合法斗爭代替武裝斗爭。
1956年春,毛澤東和中央中央決定停止幫助其他國家共產黨制訂綱領和政策。1956年6月6日,劉少奇會見古巴等拉美國家政黨領導人時指出:外國黨的意見總不能像本國黨那樣正確,只有本國黨最了解自己國家的情況,問題只能由自己解決。1958年6月,毛澤東在外交部務虛會上說:“對兄弟黨,不要代人家起草綱領,他們起草好,拿來給我們看看提些意見可以。我們過去也給人家起草過綱領,那樣是行不通的。”
新時期
從1960年代“中蘇大論戰”開始后,中共對外工作受“左”傾思想影響,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轉向。
1962年,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提出的中國對外政策,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少援助亞非拉人民斗爭)的“修正主義國際路線”,受到批判。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又稱《二十五條》),重新樹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幟,提出要堅決支持亞非拉反帝革命斗爭。同時,批判了蘇共以及意共、法共等的“和平過渡”思想。
這一時期,康生主管中聯部,實行“支左反修”的政黨對外關系的方針。“反修”的結果,不僅同蘇聯共產黨(蘇共)中斷了關系,而且同將近70個贊成蘇共觀點、主張中蘇和解的共產黨中斷了關系。“支左”,主要是指支持從“修正主義黨”中分裂出來的“小左派”。
在這種背景下,中共開始重新強調武裝斗爭。在向外國共產黨介紹中國革命經驗時,都著重介紹中國通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經驗。并且,重新開始支持東南亞一些共產黨的武裝斗爭。
但是,當時中國處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濟處于困境,沒有能力去真正支持這些國家的武裝斗爭。同時,受國際共運大論戰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東南亞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幾經分裂,政治力量和影響正在逐步消失。因此,所謂“支持”也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已開始著手糾正對外關系中左的傾向。
1975年,緬甸領導人奈溫來訪。11月12日上午,鄧小平與他舉行會談,稱:“我們一向認為,任何國家的革命采取外國的樣板,不可能解決問題。根據自己的情況去處理,這是各國的內政,是各國自己的權利,中國不干預。”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對外工作“撥亂反正”,打開了政黨外交的新局面。
首先,擯棄了“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為時代的主題。第二,明確了政黨外交是“總體外交”的一個部分,重新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
1978年,鄧小平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會談時,李光耀表達了對中國支持東南亞共產黨活動的擔憂。鄧小平強調:中國不會輸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謀求勢力范圍;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問題是這些國家的內政,應由這些國家自己處理。
根據這一原則,中共跟“修正主義政黨”恢復了關系,同第三世界國家政黨和西方國家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以及保守黨發展黨際關系,對“小左派”則逐步中斷了聯系。
對東南亞國家共產黨,也相應進行了調整。不再提亞非拉是“世界革命中心”,積極發展同東南亞國家民族主義政黨,包括執政黨和主要反對黨的聯系與交往。
對于當時仍留在中國的少數東南亞國家共產黨成員,則進行了妥善安置。大部分人員都回了國,或去了歐洲國家。希望留在中國的,則請其不要進行政治活動,安排其從事教學或社會工作。
10多年前,我去法國訪問,曾在一家泰國餐館就餐。餐館老板會中文,我們就交談起來,交談中發現,原來這是一位定居法國的泰國人,現在生意不錯。大家相談甚歡,心照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