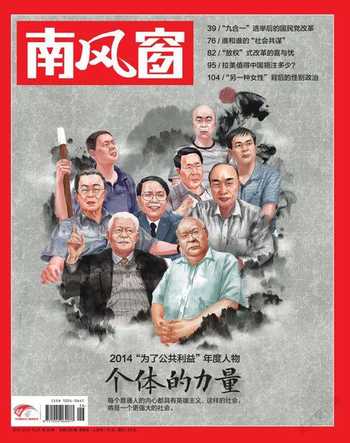臺灣:變化社會中的政黨重建
鄭振清

馬英九主持的新一波國民黨改造出現了新問題。
從2000年春季到2014年冬季,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地區走過了一個跌宕起伏的歷史周期。國民黨先是丟失臺灣“執政權”長達8年,到2008年才推出一代政治明星馬英九奪回政權,但到今年11月29日,又在“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再遭慘敗—甚至被臺灣媒體稱為國民黨自1949年以來最大的潰敗。“九合一”選后國民黨在全臺22個縣市中僅僅守住6個縣市的執政權,所轄縣市人口不到全臺的1/3,而且失去了具有關鍵指標意義的臺北市長職位。
2000年3月國民黨剛剛敗選之時,大批因失望而激憤的藍營群眾包圍了位于臺北市中山南路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李登輝下臺”的呼喊聲響徹臺北繁華市區的上空。臺北市長馬英九趕到現場后,發現無力安撫憤怒的人群,只好答應去敦促李登輝辭去黨主席。但是,這次“九合一”慘敗之后,在八德大樓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卻人影寥寥,令人驚訝。據了解,很多藍營支持者對慘敗的國民黨已經失望透頂,連抗議的激情都沒有了。幾天后,馬英九在一片愁云慘霧中宣布辭去黨主席職務。他在辭職聲明中說:“人民對國民黨的期待,比國民黨改革的腳步還快。”
關于國民黨這次慘敗的原因,很多觀察和評論指出,在臺灣經濟停滯和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的時代背景下,馬英九不少民生公共政策連接失誤,引發民怨,再加上國民黨推出的多位地方縣市候選人不適當,終于釀成了此番惡果。不過,另一重要因素隱藏在這些現象之下:近年來,國民黨的政黨形象遠非正面,政黨認同度大幅下滑,不僅其“鐵票部隊”日益萎縮,而且對新生世代基本毫無吸引力。
可以說,今天的國民黨,在政黨形象、政綱與領導團隊等方面都面臨極大的危機,如果不及時推動有力的改革,找回臺灣人民的認同,那么離徹底崩潰也就一步之遙。在國民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回顧該黨在臺灣民主化時代的改革歷程,分析其現實挑戰,探討其發展方向,尤有必要。
國民黨遷臺以來60多年,推行過多次規模不一的黨務改革。其中,對今天的國民黨組織體系影響最深遠的是從蔣經國時期到李登輝時期的本土化改革,其次是最近十多年來連戰和馬英九推行的民主化改革。
蔣經國在197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本質上是一種人事政策本土化,亦即將臺灣本省籍的新生代精英吸納、甄補到國民黨的體制中去。這波改革在有限范圍內緩解了掌權的外省籍精英和臺灣本省籍民眾的矛盾,重塑國民黨在臺統治的合法性,塑造了整整一代的臺灣本省籍政治精英,例如李登輝、林洋港、連戰、吳伯雄、蕭萬長等。到1980年代后期,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亦即臺灣化,已經成為一種明顯的趨勢。
李登輝執政后,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高歌猛進,但是國民黨本身的黨內民主并沒有多少進步。作為百年老黨,國民黨帶有濃厚的封建文化和官僚習氣,黨內等級森嚴,黨機器運轉僵化。國民黨的地方和基層黨部也是長期功能不彰,組織萎縮,只會“綁樁”。各級黨工們平時除了勤跑紅、白喜事之外,很難及時有效地反饋民意。
在社會思潮多元化,選舉民主成為基本游戲規則的臺灣,國民黨居然可以保持威權主義的體制和如此保守僵化的作風,無疑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乃是,李登輝黨政合一的龐大權力既已形成,又擁有政治體制和認同本土化的“加持”,就不愿輕易放權,由此封殺了黨內任何重大民主改革的路徑。
不過,隨著1997年臺灣縣市長選舉之后民進黨的快速發展,大批自由知識分子和本土工農群眾成為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社會基礎,國民黨領導層開始感受到本黨龐大的歷史包袱和各種既得政經利益的壓力。根據臺灣《財訊》月刊出版的《拍賣國民黨—黨產大清算》一書披露的資料,到2000年,國民黨已成“全球首富政黨”:當時國民黨主控的事業多達66家,轉投資300多家,總資產逾6000億元新臺幣,堪稱全臺最大財團,也是全球首富政黨。如此龐大的黨產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利于開展選舉動員和利益輸送,另一方面也引發普通民眾和中小企業的強烈不滿。后者日益凸顯,嚴重挫傷國民黨的形象,每逢選舉都會被民進黨拿來做大做文章。雖然連戰、馬英九時期推行剝離黨產、實行信托的改革,但直到今天依然尚未解決黨產包袱問題。
2001年3月,連戰開啟了國民黨黨主席直選的先例。雖然這次是同額選舉,但開辟了國民黨黨內民主的新時期。在野時期的國民黨,沒有了沉重的執政壓力,沒有了權力帶來的傲慢姿態,卻得到了喘息、反省、改革與創新的空間。在黨內改革方面,連戰著手精簡人事,改造龐大而僵化的黨務機器,同時積極培養中生代骨干,讓馬英九、胡志強、郝龍斌、吳敦義、朱立倫等地方實力派精英進入黨內領導層,而王金平也利用“立法院”平臺努力經營,培植勢力。
在兩岸關系方面,連戰于2005年4月底勇敢地邁出“破冰之旅”,與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實現國共兩黨自1945年重慶談判以來的首次領袖會晤,帶來國共和解,達成5項共同愿景。從此,國、共兩黨合力推動兩岸關系走向和平發展軌道。
根據臺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國民黨的民眾偏好分布(約可看成社會支持度)自2004年春季開始反超民進黨,到2005年底達到一次小高峰,超過90年代的最高水平。這就是連戰推行國民黨改革的漂亮成果。2005年7月,馬英九、王金平競選黨主席,當時競爭激烈,選情緊張,國民黨的活力卻重新煥發了出來,社會支持度一路走高,到2011年初達到臺灣政治民主化以來最高峰—39.5%。與此同時,受陳水扁系列貪腐弊案和“臺獨”鬧劇的拖累,民進黨的社會支持度一直在25%左右低迷徘徊。
從2005年到2012年,馬英九本人的良好形象和國民黨改革的正面效應產生了誘人的紅利,不僅馬英九贏得兩次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勝利,而且一批國民黨中生代精英也在地方縣市長和“立法委員”選舉中占據優勢。
不過,馬英九主持下的新一波國民黨改革卻出現了新問題。由于先天的外省籍身份包袱,馬英九在推動國民黨新一輪本土化—政黨建設本土化之時,刻意討好親綠的本土選民,卻忽略甚至不惜犧牲傳統藍營支持者的利益。而且,馬英九對法治思維和民主觀念的過于刻板的迷思,促使他全力推動國民黨朝著美國式民主政黨的方向改革,試圖把歷史悠久、結構復雜的國民黨改造成單純的選舉機器,推行簡單化的“以黨輔政”。結果,短短幾年,催生出一匹左右迷失、動彈不得的“四不像”來。
首先,畸形的本土化改革,讓國民黨支持群體的利益受損,感情受傷,逐漸失望。2005年7月當選黨主席后,馬英九以“重新建立國民黨與臺灣社會的聯結”為志,努力挖掘國民黨與臺灣有關的點滴歷史,迎合臺灣本省人和原住民的本土認同觀念,卻刻意忽略國民黨曾經積極經營海峽兩岸的宏偉篇章,其結果是馬英九和一大批國民黨人基本走不出狹隘的臺灣本土利益觀,在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上缺乏宏觀思考,缺乏主動引導臺灣民意的戰略能力。最近兩年來,馬英九加碼老農津貼的同時,卻降低軍公教人員的優惠存款利率,取消其年終慰問金,引發藍營“鐵票部隊”的失望和反感,最后在“九合一”選舉中“含淚不投票”,終釀國民黨敗選的惡果。
其次,過度理想化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國民黨原本僵化的黨務機器自廢武功,更加無力動員社會,進一步削弱了輔選能力。國民黨在臺灣長達半個世紀的一黨執政,長期壟斷各種政經利益,形成了復雜的利益結構,養成了官僚化的組織作風。馬英九依據單純的法治和民主理念,以美國式選舉型政黨為理想模板改造國民黨,簡化中央、地方和基層黨部的工作體系,并大幅精簡黨工。但由于缺乏那種以價值理念為號召、召之即來的大批基層和網絡義工的有效支持,國民黨傳統的組織優勢削弱了,但新的動員模式又沒有完全建立,輔選和組織工作十分脆弱,在臺北都無力動員中間選民和新興世代青年選民的支持,在地方縣市只能更加依賴地方派系和大小“樁腳”。
再次,近年來,國民黨高層重新形成家族化政治經濟格局,這些家族一方面獲得大量兩岸經貿交流的紅利,另一方面控制黨內選舉提名,阻礙普通黨員的發展通道,使得國民黨政黨形象極差,幾乎失去整個年輕世代的認同。在兩岸經貿交流中,國民黨內部確實有幾個主要家族得到大量政治經濟利益,連帶分利于一些臺灣大財團大企業,而中南部不少中小和小微企業卻得不到好處,大量由于經濟下滑和薪資停滯而受損的弱勢群體更感受到嚴重的“相對剝奪感”。
國民黨內部的封建文化、官僚習氣、權力斗爭、大佬排場一直存在,馬英九本人雖然也很厭惡,但是沒有足夠魄力去改變。馬本人一度寄希望于新設立的國民黨“青年團”能夠帶來一些新鮮空氣,但是“青年團”與“青工會”關系模糊,力量分散,加上內部爭權奪利,根本無力爭取年輕世代的民意,無法幫助國民黨適應網絡世界、新媒體和自媒體世代的政治傳播。
縱觀2010年臺灣“五都市長”選舉、2012年領導選舉和2014年“九合一”選舉,不難發現公共政策領域的民生問題—而非意識形態色彩強烈的統獨問題—正在塑造臺灣的政黨選舉進程與結果。可以說,近年來臺灣的主要社會矛盾,正在由過去的省籍認同矛盾轉向貧富分化和階級利益矛盾。
在臺灣貧富分化和民進黨中生代推動政黨轉型的背景下,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逐漸走上“中間偏左”的政治路線。最近兩年來,筆者在臺灣的多次調研都發現,民進黨智庫和從政精英并不諱言民進黨試圖把政黨競爭的主軸定位為“左右之爭”,亦即建立以重經濟增長(“右”)和重社會公平(“左”)為兩端的公共政策空間作為選戰的舞臺。在這個政策議題空間中,民進黨自我定位為“中間偏左”政黨,著眼“分配”層面的社會公平問題,并試圖將馬英九和國民黨打成只在乎“經濟增長”的“右翼”政黨。
到了2014年,臺灣的經濟狀況依然低迷,貧富分化有增無減,催生了激進的社會運動。3月份的“太陽花學運”未必受民進黨或蔡英文本人的領導或策劃,但是從學運分子的很多言論中,可以辨識出民進黨近年來“中間偏左”路線和論述的痕跡。“九合一”是“太陽花學運”和年輕世代走上政治舞臺后的第一場選舉,他們把國民黨當作自身利益與命運的敵對方來看待,給國民黨的改革發展帶來更棘手的問題。
可以說,馬英九之后的國民黨,正面臨前后夾擊、左右為難的歷史性困境。歷史遺留的黨產問題尚未解決,僵化的官僚習氣延綿不斷,畸形的本土化思維銷蝕戰略能力并扭曲公共政策,過度民主化改革自廢武功……這些問題在民進黨與新興社會運動和年輕世代的夾擊之下愈發尖銳。而且,“右翼”政黨的帽子又給國民黨帶來不堪承受之重。
2015年以后新的國民黨主席和領導層,可以有很多具體的改革措施,但是一條根本之道應該是重新樹立民生主義為重的政黨旗幟和政策綱領。在組織重建上,應該積極培育能有效動員臺灣社會的政黨組織能力和政治傳播能力,而沒有必要動輒學歐學美。
就現實的緊迫的政治競爭而言,國民黨應做好2016年初雙直選再輸一半的心理準備,置之死地而后生,通過強調兩黨政治的力量平衡對于臺灣政經健康發展的重大意義,爭取廣大中間選民的支持,比如,可以考慮爭取臺灣選民的“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通過保證在“立法院”的席次優勢而為今后改革發展的政治監督和全面改革積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