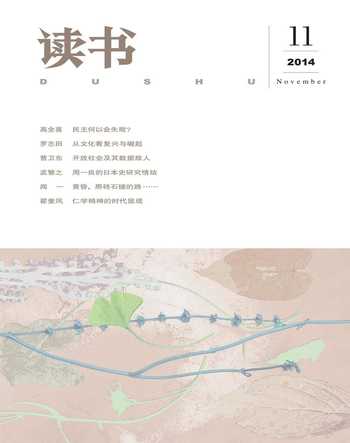作為冷戰小說的《日瓦戈醫生》
所思
今年四月,美國媒體刊文,依據新近解密的一百三十余份檔案,證實中情局全面介入了《日瓦戈醫生》兩種俄文本在蘇聯以外的出版、印刷、發行和推廣。由中情局蘇聯處具體執行,局長艾倫·杜勒斯監管,而且要求:“美國政府之手……不得以任何形式暴露。”美國人制定的行動指南,甚至細致到指導情報人員如何鼓勵西方游客與蘇聯人談文學,“《日瓦戈醫生》是一個絕佳的跳板,可將與蘇聯人的談話引向‘共產主義對抗言論自由’”。
在文化冷戰中,《日瓦戈醫生》是西方完勝的一場戰役,由于彈藥來自蘇聯內部,其戰果或許比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農場》有過之而無不及。《日瓦戈醫生》事件,從出版到作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蘇聯一敗涂地,歐美贏得了輿論,贏得了利益,也贏得了歷史。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地覆天翻,這部小說成為控訴“十月革命”的暴力如何毀滅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作,并因作者被諾貝爾文學獎加冕而籠罩著超越時空的“世界名著”的光環—事實上,這種印象正是不折不扣的冷戰產物,是這場戰役勝負的延續,它雪藏了歷史上失敗者的聲音,也掩蓋了這部長篇小說藝術上的缺陷。
帕斯捷爾納克完成《日瓦戈醫生》后,無法在蘇聯出版,手稿被悄悄傳遞到意大利,一九五七年底出版,很快有了各種譯本。一九五八年作者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遭到蘇聯官方的嚴酷迫害,被迫拒絕領獎,但他堅持留在祖國,不愿流亡—這大概就是我們對“日瓦戈事件”的通常印象吧。但如果仔細閱讀帕斯捷爾納克的傳記,他的妻子季娜伊達、情人伊文斯卡婭等人的相關回憶,就會發現,事件的經過要復雜得多,蘇聯方面也并非毫無作為。
一九五五年底,帕斯捷爾納克基本完成了《日瓦戈醫生》,打印了幾份后送往《旗》與《新世界》編輯部。他最初想必對出版這部小說抱有希望。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召開,社會環境在松動。在文學界,以愛倫堡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小說《解凍》為標志,五十年代有所謂“解凍文學”的潮流。事實上,一九五四年,《旗》已經刊出了《日瓦戈醫生》所附的部分詩歌,并向讀者預告小說即將收官。
小說送到雜志社后,詩人遲遲沒有收到回音。《新世界》的退稿信寫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信件落款日期),由主編西蒙諾夫起草,費定等幾位編委聯署,否定了這部小說,但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獎后兩天,發表于《文學報》)。
在此之前(同年五月),莫斯科對外廣播用意大利語報道了小說完成的消息,并稱該書即將出版。這引起了意共黨員安捷洛的興趣,他也是意大利出版商費里蒂涅里的駐蘇代理,他拜訪了帕斯捷爾納克,詩人把一份打印稿交給了他。也就是說,書稿是在《新世界》尚未給出正式答復的情況下外流的。
得知稿子給了外國人,詩人的妻子和情人都覺得不安。伊文斯卡婭找蘇共中央文化部部長波利卡爾波夫商量。這位官員的意見是,《日瓦戈醫生》必須先在蘇聯出版,再在國外面世。帕斯捷爾納克應該設法從意大利人那里索回書稿。“我們必須追回書稿,萬一有些章節我們不發表,而他們卻發表了,那不太合適。”“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在國內決定小說的命運,并且為此做出一切努力。”(據伊文斯卡婭的回憶)他還建議詩人和國家文學出版社的社長談一談,并當即給出版社打了電話。
一九五七年一月,國家文學出版社與帕斯捷爾納克簽訂了《日瓦戈醫生》的出版合同,指定的責任編輯斯塔羅斯金“是帕斯捷爾納克創作熱烈而又細心的崇拜者”,他說:“我要讓這部作品為俄羅斯人民增光。”(據伊文斯卡婭的回憶)雙方著手商談出版時間和修改意見。
一九五七年二月,國家文學出版社致信意大利出版商費里蒂涅里,要求對方在蘇聯九月推出俄文版之前,不要出意文版。費里蒂涅里回函做出承諾。
但是,《日瓦戈醫生》的出版還是擱淺了。其原因,有人認為是蘇聯方面與費里蒂涅里交涉失敗,未能索回書稿,甚至動用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做說客也遭到了拒絕—費里蒂涅里為出版這部書,退黨了。當然也不排除對這部小說的否定意見占了上風,蘇聯當時處于變動時期,文學界的分歧和爭論可以想見。而伊文斯卡婭認為:“在這件事情上犯有過失的與其說是他(帕斯捷爾納克)的政敵,倒不如說是他的文學界對手,而首先是蘇爾科夫(蘇聯作協負責人)之流懷有嫉妒心的人物。像黨中央文化部長波利卡爾波夫這樣一些真正的政治家卻很想制止這日益激化的事態,希望小說能以稍微可以接受的文本在我國出版發行,并不愿意釀成一場丑聞……”
帕斯捷爾納克被要求發一封電報給費里蒂涅里,阻止意大利文的出版。根據安捷洛的回憶,詩人對此發了脾氣,不過,“最后,帕斯捷爾納克相信,人家是不會相信電報的,而且也不可能阻止事情的發生……電報就這樣發了出去”。
一九五七年十月,隨蘇聯代表團訪問意大利的蘇爾科夫在米蘭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獲悉《日瓦戈醫生》將違背作者的意愿出版。“冷戰滲透到文學中來了。如果這就是西方所理解的藝術自由,那么我必須申明,對此我另有看法。”這位作協領導人的話表明,蘇聯官方已經明確把這部小說視為冷戰的工具。
同年十一月,《日瓦戈醫生》問世,先是意大利文本,隨即是俄文本。在半年內差不多就出了十一種譯本,兩年內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在西方得到了大量的宣傳,非常轟動。
詩人的妻子季娜伊達回憶這場出版競爭時說:“我們國內大家很氣憤,認為這是叛賣行為,而對方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則是大量賺錢和撈取政治資本。這形成一個很壞的局面。”不過,詩人并不這樣看,“他對我說,一個作家活著就是要把自己的著作出版,而國內卻把小說擱置了半年時間”(據季娜伊達的回憶)。
蘇聯和西方爭奪的,首先是出版權。蘇聯官方愿在修改的前提下促成小說的出版,而且很清楚一旦流出的書稿在國外面世可能造成的被動局面,也曾全力索要流出的書稿。這一點,美國人同樣明白。中情局的解密檔案是這樣描述的:“此書擁有巨大的宣傳價值,原因不只在于其固有的信息和令人深思的本性,還在于它的發表環境:我們有機會讓蘇聯公民思考其政府錯在何處,因為公認最偉大的在世俄國作家所寫的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竟然不能在他自己的國家,以他自己的語言,讓他自己的同胞來閱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詩人被迫拒絕領獎,事件持續發酵……大約在這一緊張時期,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在一次講話中談到了《日瓦戈醫生》,并被匯報給赫魯曉夫。有關人員從書中摘錄了一些“反革命語錄”,共三十五頁,呈送蘇共政治局委員。赫魯曉夫后來在回憶錄中承認,自己沒有看過書,他對自己同意采用行政手段處理感到后悔。“我至今后悔當時沒有把那部小說印出來。跟文藝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的手段來下結論。如果當時把《日瓦戈醫生》印成書,會發生什么特別的事嗎?我相信,什么事也不會發生!”
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對帕斯捷爾納克的批判愈演愈烈:開除出作協、大規模的輿論攻擊、驅逐出境的威脅、詩人被迫放棄諾獎、發表違心的聲明……蘇聯的批判和歐美的聲援相互較勁,水漲船高。也許是出版過程中的博弈耗盡了耐心,也許是固有的文化領域粗暴政策,蘇聯方面采取了最愚蠢、最不明智的手段,使得腳本恰恰按照對手的期望順利地演出。在文化冷戰方面,美國及西方陣營戰略的深遠、戰術的細致、目標之準確、用人之得當,蘇聯望塵莫及,簡直像核武器和冷兵器的對峙。
《日瓦戈醫生》是一部冷戰小說,即使中情局之手沒有暴露,這一點也是明擺著的。文化冷戰中看不見的硝煙化作了它的光環,意識形態的需求砌成了它邁向經典的臺階。其實只要讀一讀就知道,《日瓦戈醫生》跳躍、破碎,敘事視角的轉換隨意而凌亂,與它一向被標榜的“史詩氣質”頗不相稱。它不乏流光溢彩的片段,但總體上似乎尚未把握好長篇小說的敘事藝術。它是一部典型的知識分子小說,某些描寫很有想象力,猶如攝影機一般極富視覺色彩,帶來強烈的印象,但若論人物刻畫的生動和深入,時代氣息的復雜和悲劇性,它遠不能與《靜靜的頓河》相比。
現代小說訓練我們理解破碎、斷裂的敘事,情節并非必須,連貫不算美德,但是就《日瓦戈醫生》這樣以革命和歷史為標的的小說而言,如果人物缺乏內在邏輯,或其邏輯與小說的野心不相匹配,恐怕就成問題了—比如小說中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斯特列利尼科夫),這位作者著力刻畫的紅軍軍官,寫得不連貫、不真實,而且相當膚淺。他在自殺前有一大段情圣般的表白,原來他上大學、讀書、參軍、革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對拉拉的愛啊……《新世界》雜志給帕斯捷爾納克的退稿信中寫道:“日瓦戈所譴責的一切在這個(對革命進行審判的)法庭上沒有自己的辯護人。”的確,安季波夫這樣的角色,怎能充當革命的“辯護人”呢?恐怕也沒資格站上革命的審判席。他經歷了“一戰”,選擇了紅軍,毀于國內戰爭的風暴,但是這位涂滿革命的嚴酷迷彩的“槍決專家”,其實更像一名尚未走出青春期的少年維特,他所支撐的故事和理想,很不幸更接近一出愛情通俗劇而非時代悲劇。說到底,以愛情為源動力的“革命者”,最適合他們的土壤是好萊塢。
愛倫堡在回憶文章里說,帕斯捷爾納克“能理解自己,有時也能理解某些接近他的人,但無論如何也不理解歷史”,談及《日瓦戈醫生》則說:“小說中有一些極為出色的篇頁—描寫自然景色和愛情的篇頁,但是作者用了過多的篇幅去描繪他不曾目睹、不曾耳聞的事物。書中還附了一些絕妙的詩,它們似乎著重指出了散文精神上的錯誤。”(《人·歲月·生活》)顯然,《日瓦戈醫生》在藝術層面并非毫無爭議。《新世界》主編西蒙諾夫的看法和愛倫堡一致:全書最出色的部分—首先是作為附錄的詩歌,“在俄羅斯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帕斯捷爾納克都不是散文作家,而是二十世紀俄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偉大詩人因長篇小說而享譽世界,依托于語言的詩歌畢竟不易領會,而意識形態這個家伙在哪兒都能領到簽證。帕斯捷爾納克用《日瓦戈醫生》審判了革命。他相信:“誰也不能創造歷史,它看不見,就像誰也看不見青草生長一樣……革命是發揮積極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熱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們在幾小時或者幾天之內推翻舊制度。變革持續幾周,最多幾年,而以后幾十年甚至幾世紀都崇拜引起變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樣。”
詩人是否知道,他自己實實在在地參與了一種歷史的創造呢?在那場影響深遠的文化冷戰中,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是一面鮮艷的戰旗。這也是《日瓦戈醫生》直到今天還被閱讀的一部分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