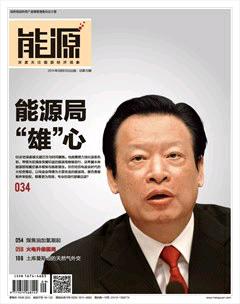“能源民主”帶來三大轉變
胡森林


1905年,美國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在文章中這樣寫到:“發電機本身只不過是將儲藏在骯臟發電室里那數噸劣質煤炭中潛藏的熱能傳遞出去的精巧渠道而已,但對我來說,發電機是無限可能的象征。”亞當斯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感慨,是因為電的使用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更大便利,此前盡管熱機早已廣泛運用,但讓人感到為難的是,功率再大的熱機也無法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只有電的誕生,才使人們能夠更好地分配和使用動力。
電是二次能源,可以經由多種原料生產得來,它的最大優勢在于極易運輸,只要在發電地和用電地之間架起電纜和電線,合上開關,就能獲得想要的動力。因而,電是能源轉換中的一種重要中介。國際能源署(IEA)認為,21世紀的世界能源結構將以電為框架,大部分能源都將轉化成電再加以使用,電成為能源基礎平臺和能源系統優化的核心。
在所有的能源類型中,電最具有民主性、普適性和普惠性,不管什么發電方式,什么用電方式,你都看不出這些電之間有什么區別,能夠區別的只是“有電”和“沒電”。電的這一特性,為人類第三次能源轉型提供了一種極富可能性的路徑,即以電為中心,圍繞更清潔經濟的發電、更安全高效的配置、更便捷可靠的用電展開,將各種用能方式、用能主體、用能區域高度連接在一起,從而呈現一種“能源民主化”的圖景。這一“能源民主”進程涉及與能源相關的權力結構、生產區域、生產主體、使用方式、能源品種以及驅動力量等多個層面,總體而言,將呈現三個特征:去碳化,從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去中心化,從精英能源到大眾能源;去資本化,從資本主導到資源主導。
去中心化 : 從精英能源到大眾能源
在世界范圍內,能源生產正呈現中心分散的趨勢。以最主要的能源品種石油為例,中東國家盡管仍然掌握著大部分資源,但中東之外的石油產量正在不斷上升,頁巖油氣等非常規油氣帶來了國際能源格局的深刻變化,加上俄羅斯的天然氣、委內瑞拉的重油、加拿大的油砂、巴西的深海等油氣資源,世界油氣地緣政治正在重塑,非OPEC國家的油氣生產比重不斷上升,生產重心西移、消費重心東移的態勢已然清晰。這一變化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傳統油氣生產國的市場份額和價格影響力不斷削弱,消費國的主動權越來越大,世界石油地緣政治越來越呈現從資源地爭奪向消費地爭奪轉變。雖然從長期來看石油供需仍然偏緊,但可以預見的是,越是油價高企,越會促進中東以外儲量的開發。世界能源供應多元化的趨勢將使生產者為主導的局面有所改變。而這一變化的間接影響則在于,在能源格局和各種變量綜合作用下,當今與未來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也在發生裂變,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在于,美國將越來越難以通過中東能源戰略影響全球能源和政經格局,而且是隨著雙邊和多方石油合作的增多,以美元為石油結算貨幣的格局也將受到沖擊。能源領域正在上演“去霸權化”的進程,美國霸權的逐步終結推動能源民主化,有望帶來國家權力之間更加扁平化的全球關系。
具體到一國范圍內,能源生產主體也將更加多元。能源不僅象征著財富,更象征著權力。以石油為代表的能源稟賦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有著重要的影響。目前在全世界石油行業中,只有美國是充分市場化的管理體制,石油公司屬于私人部門,有成千上萬的石油公司共同參與競爭,小公司承擔風險、孵化創新,大公司將創新的技術和模式發展成產業,這種市場結構和創新機制使得近百年來石油行業絕大多數創新技術誕生在美國,“頁巖氣革命”也唯獨在美國發生。而在大部分國家,石油均采取國有化的管理方式,形成高度集中的石油工業基礎結構,越是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政治經濟進程以及民主發展越是滯后。這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以石油為代表的化石能源屬于“精英能源”,它們只在特定地域出現,需要大量資本和強有力的控制體系對其進行開采、加工與運輸,還需要武裝力量以及持續的地緣政治運作來確保安全,從而形成大集團、產業大亨、集權式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垂直一體化開發和供應模式。這種壟斷或專營體制以及產業的資本密集型特性,使得在傳統能源時代,容易從體制中滋生排斥民主、排斥資源分享的內生力量。
新的能源革命將改變這一現狀。依靠技術的進步和產業模式的創新,給每個人創造了平等獲取能源的機會,這種普適性創造了能源民主的基礎;每個家庭、每個社區甚至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微型的能源工廠,打破對能源生產的垂直壟斷,創造能源民主化的前提。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描繪了這樣的藍圖:“人人開發能源、人人控制能源、人人享有能源、人人獲益能源,人人成為能源的主人。”由此可見,未來的能源發展模式是民主化和去中心化的,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公民社會的建設,能源民主化將形成水平分布和網絡擴散式的合作式能源開發與使用架構,這將從根本上重建社會網,使其向扁平化方向發展,進而衍生出一種與之相應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去碳化:從高碳到低碳
從能源自身的發展和演進來看,也將出現能源品種多樣化、能源使用方式多樣化并呈現從高碳向低碳演進的趨勢。化石能源推動了工業革命的進程,但隨著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劇,靠傳統能源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人類迫切需要減少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實現能源組合的多樣化和低碳化,因此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變革將不可避免。與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新能源具有可再生、無限量、無污染以及分布廣、密度低、波動性等特點,采用分布式的開發利用,能夠有效地改善和優化能源結構。2010年7月IEA發布的《能源技術展望2010》報告認為,初步跡象顯示,全球正在經歷一場能源科技革命,將對今后數十年經濟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能源科技創新與空間技術、人工智能并稱為世界三大尖端技術之一,它既可以表現為全新的科技創新(如氫能、地能、太陽能等),也可以表現為原有科技的改進與突破(如潔凈煤技術、二氧化碳CCS技術等);既可以表現為單一技術的創新,也可表現為綜合循環的技術系統,還可以表現為能源輸送、儲存以及使用的價值鏈增值。依靠這場深刻的能源科技革命,人類對能源的使用將經歷一個由高碳走向低碳進而走向無碳、從不清潔走向清潔的過程,能源利用方式將從低效走向高效,從資源密集型走向技術密集型,能源設施裝置將從小型走向大型進而形成大型和小型相結合的格局、從分散走向集中進而形成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格局,人類社會將從高能耗型走向低能耗型社會。
里夫金提出了支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個支柱: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使其成為世界能源供應的主力能源;將世界上每一棟建筑轉化為微型發電廠,實現能源自產自銷;發展和應用氫能等存儲技術,使每棟建筑成為剩余能源的儲備設施;利用網絡技術建立全球能源互聯網,使所有的微型發電廠通過網絡買賣和共享剩余能源;普及電動燃料電池汽車,使其通過全球電網充電或者出售剩余的電量。預想一旦變成現實,將意味著從能源的生產、搜集、儲存、轉化、銷售到使用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合體系。能源戰略制定與技術進步如此之快,使這一切正在逐步實現。2009年9月,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初,便將“新能源戰略”提升至美國國策的高度。他的第一個任期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和處理伊戰等事務而無法實施,第二個任期已經開始兌現其承諾,2014年5月29日他提出了大膽的“全方位”能源戰略,鼓勵發展低碳技術。在歐洲,丹麥和西班牙的普通民眾可以參股風力發電項目,北歐四國電網之間實現了互聯互通。能源品種的分布式、多元化和去中心化運動,將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分享,從而建立一種以“能源和諧”為標志的新型經濟社會關系。
去資本化:從資本主導到資源主導
能源民主化的影響絕不限于能源領域,它對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都將帶來重大沖擊,主要依靠大資本、大投入的資本主導型能源發展模式將受到挑戰,充分利用分散的資源、即產即用型的資源主導性能源發展模式逐步興起,這意味著在能源領域形成一種“去資本化”的趨勢,從而對經濟體系和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法國經濟學家皮迪克在其新作《21世紀的資本論》中揭示了這樣一個現實,21世紀美國的財富分配幾乎已經到退回到19世紀的歐洲:前10%的人掌握了50%的財富,前1%的人更掌握了20%的財富,這一套資本主義繼續玩下去,只會讓有錢的人更有錢,沒錢的人更沒錢。因為從1980年代以來的趨勢就是資本利得遠遠高過工資所得,這將導致金錢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形成十足的世襲資本主義。這種趨勢不加以改變,21世紀將會和19世紀一樣,面臨巨大的貧富落差、尖銳的社會矛盾、紅旗到處飄揚,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戰爭。皮迪克認為,為了維護民主政治的穩定,必須采取行動遏制財富過度集中到少數富人手里,這是避免出現社會動蕩和戰爭的最佳方案。
皮迪克揭示的現象是觸目驚心的,反思是深刻的,已經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極大關注。在全球化的經濟運作機制下,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呈現資本主導的趨勢,唯有能源民主化有可能產生對全球化帶來的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反作用,從而對不斷加深的社會矛盾加以校正和緩解。可再生新能源分布于世界各地,是“不能移動”的本地資源,要想開發這種資源,就必須到當地去開發,這一過程帶動的是整個產業體系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而改變每個個體的經濟狀況,比如裝在每家每戶屋頂上的太陽能發電設備發出的電,先供自家使用,多余的電量可以并入電網進行買賣來獲得收入。特別是對于化石資源匱乏的發展中國家,這種新的能源發展模式更具有誘惑力,不但可以促進本國的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創新,也能讓更多的人分享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的“紅利”。
能源生產與使用方式的民主化與人的智慧發揮互為表里,這種能源發展模式內在地呼喚一個人人參與、人人分享、人人創造的社會。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深入探討了自工業革命以后現代經濟增長出現以來,先后領跑世界經濟增長的英國和美國的創新動力源泉和激發這種動力的制度環境,指出它們取得大繁榮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愿望。當前,創新驅動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的共識,但這種“創新”并非源于少數人的、精英的、從上而下推動的狹義的創新,而是一個基于大眾的、草根的、自下而上、充滿活力的廣泛意義上的全面創新。大多數創新并不是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也不是簡單的新發明,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和制度的創新,它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草根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了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以及“美好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回顧英美等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中國要實現真正的繁榮很大程度取決于創新活動的廣度和深度,只有從民族根部煥發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將創新滲透到每一個社會階層,每個人都積極思考“我”生活的本質意義,中國才有實現全面繁榮的可能。
馬丁·路德曾這樣寫道:“每個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解釋圣經”,“修會不必存在”。新的能源革命也將演繹這句話新的內涵:“每個消費者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生產能源,能源工廠不必存在。”任何人都可以不借助大型集中設施等中間介質,自由實現能源的生產和使用,就像每個人都可以開一個淘寶店出售自己的商品、隨時在微博上更新一條信息一樣,一個更加開放和多元、參與性和互動性更強的經濟體系將出現在我們面前,第三次能源轉型帶來的“能源民主”精髓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