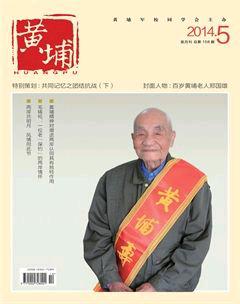揮之不去的老兵情結
“老周,咱們寫一首歌唱老兵的歌。”
這是三年前音樂制作人、作曲家黃埔漢先生(真名張忠良)向我發出的邀請。“好呀。”我隨意答應了一聲,沒想到他竟較起了真,一星期后就向我索稿,并邀我一道去荔浦看望他父親——九十歲的抗日老兵。其實我早已開始構思醞釀了,只是這是個重大題材,絕不是幾句口號,幾段漂亮的文字就可以組成的,它的分量太重了,幾十年來積壓在我心中的情感又太多太多,一時還找不到最佳的感覺,找不到突破口,所以遲遲不敢動筆。
老人在家中款待我們。他滿頭銀發,剪得很短很短,每一根都精神抖擻地豎著,眉毛花白了,胡子也刮得精光——渾身透出一股軍人特有的精干。一杯酒下肚,老人打開了話匣:“我1940年16歲時應征當兵,跟隨桂軍一七五師抗日,走遍大半個中國,大小戰役打了40余次。”當時的桂軍很能打,說著他哼起了廣西軍軍歌:
中國省份二十八\廣西子弟最剛強\天生會打仗\個個喜歡把兵當\扛起槍桿上戰場\雄壯真雄壯……老人雖然牙齒漏風,五音不全,但那質樸的歌詞、鏗鏘的節拍震撼了我的心靈,馬上把我帶到了那戰火紛飛的歲月。隨后老人給我們講述了一個個慘烈的故事。他萬分感慨地告訴我:“當年和我一起去當兵的幾十個兄弟,打完抗戰所剩無幾,我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我的命是兄弟們的血換來的,我忘不了他們……”說著他掀起衣服露出一塊塊傷疤,望著那暗紅色傷痕和殘缺的手指,我的眼睛頓時濕潤了。當老人得知我們準備寫一首歌唱老兵的歌時,緊緊握住了我的手:“周先生,寫,一定得寫,不能忘記他們!”說著他捧出他正在撰寫的回憶錄給我看,“我也在寫,讓子孫們牢記這段歷史”。捧著這疊厚厚的凝聚前輩血與淚的書稿,我的淚水終于流了下來,第一段歌詞便從心中蹦了出來:
叫一聲親人老兵,
淚水模糊了眼睛;
叫一聲老兵親人,
我貼近了你滾燙的心。
翻開塵封的記憶喲,
又見你威武身影;
拂去歲月的迷霧喲,
又見你叱咤的風云。
國家存亡,匹夫有責,
熱血青年,沙場點兵。
你用血肉擋住了日寇鐵蹄,
你用身軀筑成華夏的長城。
當晚,我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望著窗外起伏的黑色山巒,看著一勾彎彎的殘月,我又想起了我的老父親,一件件往事浮上了心頭。
家父周邦,無錫國專畢業,是黃埔軍校十四期中美干訓團的學員,參加過長沙大會戰以及桂林的抗戰。抗戰結束后,因反對內戰離開了軍政界,開始了教書生涯。解放后被清除出教師隊伍,批判為“歷史反革命、右派”,為此,也一度遭到我的誤解。
如今,家父雖然早已離開了我們,但每想起這些,我的眼睛就會濕潤,總會默默地叨念,“爸爸,兒子錯怪了您”!
如今撥亂反正,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我想父輩們為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付出的實在太多太多,我們應該為他們豎一塊精神的豐碑,讓千秋萬代記住他們的功績,傳承他們愛國革命的精神。我含著熱淚一字一句地寫下了歌曲的副歌部分:
老兵喲老兵,
中華的脊梁,民族的精英!
你是歷史的豐碑!
勇敢的中國軍人!
歌詞寫好,我如釋重負,馬上交給了黃埔漢先生。他連夜譜曲,加班制作,不少熱心的人也給了我們很多支持和鼓勵,使作品日臻完善。隨即廣西著名歌唱家謝斌老師主動上門演唱。經他聲情并茂地演繹,一首飽含深情、寄寓著無數人厚望的歌曲《中國老兵》誕生了。
記得第一次播放這首歌時,我在家中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儀式,把父親的遺像擺在正中,點燃了一炷香,在裊裊煙霧中讓那低沉悲壯的歌聲在屋里沖撞回蕩,我雙手合十,默默祈禱,愿我遠在天國的老父親和千千萬萬為國捐軀的抗戰老兵們能聽到這首遲來的歌,以慰藉他們的在天之靈。同時希望這首歌能伴隨健在的抗戰老兵們度過余生;能撥動每一位華夏兒女的心弦,喚起他們的愛國熱情。
后來,我們將歌曲貼到網上,還以獨唱、大合唱等形式參加老兵聚會以及各種演出,得到好評如潮。在演出中,不少老兵緊緊握住我們的手,熱淚盈眶,不少人來索要影碟、歌譜。這首歌在海外華人中也產生了一定影響,一位美國舊金山的朋友在網上點擊到這首歌后給我來信寫道:
周昭麟老師:
由您作詞的《中國老兵》,我已反反復復聽了不下15次﹗而且多次熱淚盈眶﹗這實在是一首感人肺腑﹑內涵深邃﹑伸張正義﹑拔地擎天的好歌﹗
向您和您的合作者致敬﹗
我們清楚,這首歌之所以能打動人,其實并不是這首歌寫得如何好,如何煽情,而是那段歷史太悲壯,太刻骨銘心!最后希望我們的《中國老兵》能慰藉每一位抗日老兵受傷的心靈,伴隨他們度過余生;能撥動每一位中華兒女的心弦,喚起他們的愛國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