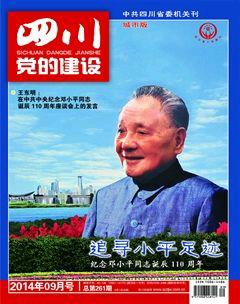變革中的戶籍制度
雷怡安
2014年7月30日,注定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日子。
這一天,《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出臺。意見指出,要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
這一天,全國首例戶籍歧視案終于在南京鼓樓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安徽女孩江亞萍在南京謀職遭遇戶口歧視,歷經一年的維權,最終勝訴,獲賠1.1萬元。
我國現行戶籍制度的確立以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為標志,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表明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管制。在中國社會發展的50多年間,戶籍制度在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社會流動性的增加,現行的戶籍制度逐漸顯露出它的弊端。數億的農村青壯年離開戶籍地到城市打工,許多人打工一輩子,依然沒有城市戶口,仍然不是“城市人”。
下面是一個在成都生活了10年的外地農村人的真實故事,從中我們可以體味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生存在城里的農村人
35歲的楊秀華到成都賣菜已有10年的時間,現在她的固定攤位在金牛區新二村菜市場,市場周邊大部分居民在此買菜,所以生意一直不錯。
楊秀華的老家在新津農村,進城賣菜前她還在餐館做過洗碗工,后來聽別人說賣菜賺錢,就辭掉工作開始賣菜。
10年來,雖然楊秀華的身份從未婚變成已婚,還有了一個上小學的女兒,但楊秀華的戶籍依然在新津縣農村。由于不是成都戶口,2008年,在給孩子選擇學校時,楊秀華沒有少折騰。當時學校提出了要一次性繳納6年的借讀費,這種讀書議價的方式讓楊秀華很無奈。她想要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學,這樣可以節約上學費用,但是她內心不想讓孩子回到農村,希望孩子能夠在城市接受教育。為了能讓孩子在成都上學,楊秀華找了好幾所學校,但最終都因為戶口的問題,不能讓女兒像其他城市孩子一樣正常入學,最終楊秀華還是繳納了6年的借讀費,讓孩子在城里讀書。
當楊秀華得知這次國家將取消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后,楊秀華說:“能和城里人享受到一樣的待遇,我就滿足了。”
據了解,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外出農民工已達到1.74億人。有關專家以金額量化方式測算過城鄉戶籍分隔制度背后的福利待遇差距,農村比城市人均福利要少30多萬元,在特大城市,差距甚至要達上百萬元。
2009年,楊秀華把老家的父母都接到了城里住,一方面因為父母年齡大了需要照顧,另一方面她也希望父母能到城里來幫著照顧女兒。
楊秀華的父親患有高血壓,因此每個月都要到醫院去做檢查,每三個月還要去醫院開一次降壓藥。在老家,楊秀華的父母已參保了新農合,到村上的衛生所或者鎮上的醫院看病取藥還是比較方便,而且能夠即時報銷。
住到城市后,雖然醫院多了,但看病卻變得困難了。更麻煩的是成都還不能進行異地就醫即時結算,這就意味著在成都看病的費用不能直接報銷,必須回到老家報銷,同時需要住院病歷復印件、費用總清單、診斷書等7樣證明材料。
楊秀華計算了一下,從看病到最終報銷他們花去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如果能夠異地即時結算,這個時間將會大大縮短。
對于打工者來說,雖然城市并不是他們真正意義上的故鄉,但依然不能阻擋一批又一批進城務工人員的熱情。隨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農村人選擇進入城市打工,他們在選擇自己生存方式的基礎上,也在選擇著他們整個的人生軌跡。
今年,楊秀華決定在成都買房。雖然到成都已經10年了,但是他們一家依然住在新二村一套50平方米的租賃房里。看著女兒一天天長大、父母的年齡也日漸增高,她很渴望能在成都買一套房子,有了房子就代表自己是城里人了。
為了買房,她和丈夫看了不少樓盤,她的想法是不要離開現在的生活圈。然而在房屋中介處詢問了多次后,她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她所待的這一生活圈在一環內,就算很一般的二手房也將近1萬元一個平方米。所以她決定在北面買一個遠一點的房子,這樣經濟壓力小一點。
“我是賣菜的,又不是成都戶口,能不能貸款買房?”楊秀華對這點不太清楚,于是她專門到成都市房管局去詢問了工作人員,得到的答案是完全和成都本地人一樣貸款,而且她在成都買房,還可以將戶口遷入成都。得知這些信息后楊秀華很高興,她悄悄地說:“ 女兒以后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是成都人了。”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研究,楊秀華和家人看中了成都昭覺寺附近的一棟樓盤,均價8000多元一個平方米。她打算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該買房了,買了房才有歸屬感。”對于不算低的還貸壓力,楊秀華還是比較樂觀的,趁著年輕多賺點錢,有了自己的房子才能讓孩子和老人幸福。
政策和落實之間
2014年省統計局發布《四川省進城務工人員現狀調查報告》指出,目前省內進城務工人員當中,舉家入城的比例占到近半,隨遷子女教育、城鎮購房等市民待遇需求較大,而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明顯不高。
進城務工的農民對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在分享勞動成果方面依然還與城市人有著顯著的差別。怎樣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打通城市與農村從形式到內容的分叉,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2014年成都市教育局發布了《關于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意見》就2014年和2015年成都市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的申請時間、提交材料及審核入學等環節提出了統一的規范要求。
擁有4925名隨遷子女的成都市武侯區依然面臨著隨遷子女集中片區學位緊張、全區學位分布不均衡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其他片區也同樣存在。endprint
如何解決隨遷子女上學的問題,武侯區教育局相關工作人員介紹,根據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的規定,當地政府必須無條件解決戶籍所在地適齡兒童入學問題,保障符合政策的隨遷子女全部入學為前提,統籌安排符合政策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學位。
作為農業大省的四川發展是不均衡的,除了成都以及周邊的幾個中心城市發展飛速外,大部分以農業為主的地區發展緩慢而艱難。如何改變這種發展差異化帶來的發展困境,2003年開始實施的城鄉統籌發展不失為一次改革的探索,而其中統籌城鄉中對“三農”的關注更是重點。為了緩解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狀況,成都市推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統籌方案,在實施的11年里,新農合給農村的老百姓帶來了切實的利益。
2013年,政府再次提高了補助,新農合人均籌資平均水平提高到340元,其中政府補助280元,個人繳費60元。可是,如何看病報銷成了一個大問題,對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或者到城里生活的農村老人來講,異地就醫不能即時結算,不僅帶來了不少麻煩,還讓他們在身份的認知上仍然存在一絲困惑。
相關數據顯示,2011年我省異地參保人數達72.7萬人,異地住院報銷人次達到29萬人次,異地住院醫療費用達到33.6億元,大部分異地參保人員報銷周期長、墊支壓力大。
2012年12月,宜賓翠屏區思坡鄉五塊村凌姓村民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證,在省人民醫院成功報賬獲得住院補償1371.31元,這是四川首例異地即時報結。下一步是如何擴大異地就醫即時報銷的面,有了經驗的翠屏區準備逐步與具備條件的華西附一院、華西附二院、省腫瘤醫院、省骨科醫院、瀘州醫學院附院、省第二中醫院等省級定點醫療機構開通網絡即時報賬。
人社廳相關負責人說,目前人社廳已與省發改委、財政廳溝通協作,完成了異地就醫即時結算管理的前期準備工作,計劃在2014年完成異地就醫省級數據交換平臺建設,并選擇成都的一些大醫院和異地就醫需求迫切的市州,接入省級異地就醫數據交換平臺,先行解決在成都就醫的刷卡結算問題,2015年全面實現異地就醫即時結算。
養老也是進城務工人員面臨的問題,從省統計局對進城務工人員社會保障水平調查中可見一斑。
目前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險或商業醫療保險參保率為82.5%,但主要是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其中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城鎮社會保險的比例都較低。在單位上班的進城務工人員中,與工作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工作單位為其購買了保險或住房公積金的比例不到四成。
在中國還有成千上萬和楊秀華情況相似的農村人,為了生存得好一點而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里,準備扎根。他們面對的實際困難還有很多,所以必然得依靠當地政府的幫助,解決他們的難題。政府在此次新型戶籍制度改革中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取消城鄉戶籍制度的束縛,將帶給城市里的農村人巨大的改變。
所有人都期待著改變的發生。(責編:李妍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