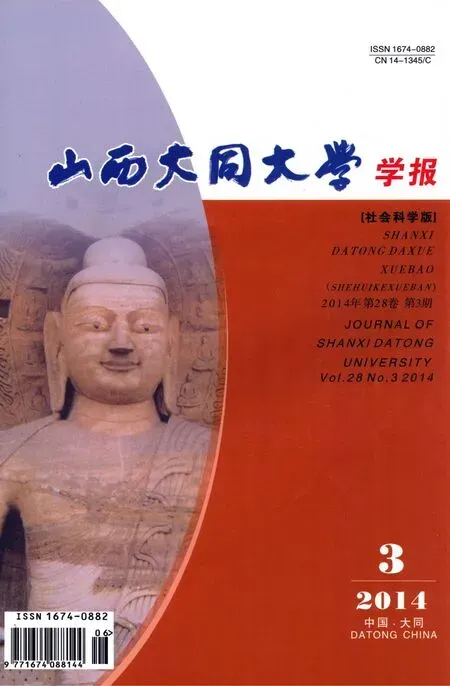大同蛙崇拜的歷史文化意蘊
張 瑞,薛文禮
(1.湖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院,湖北 恩施 445000;2.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大同蛙崇拜的歷史文化意蘊
張 瑞1,薛文禮2
(1.湖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院,湖北 恩施 445000;2.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借助大同地區流傳的蛙崇拜故事和自然景觀蛤蟆山,研究了大同蛙崇拜產生的文化環境基礎,揭示出大同蛙崇拜、女性生殖崇拜的漫長歷史演變過程及其在大同歷史文化中的價值和意義。
大同湖;蛙崇拜;傳說故事;蛤蟆山
蛙崇拜是遠古社會進入原始母系氏族時期崇拜意識的產物之一,也是自然崇拜的一種,其流傳的地區非常廣泛,大同也不例外。在大同,無論是民間傳說,還是自然景觀,都給我們留下了蛙崇拜的歷史痕跡,研究這一課題有著厚重的歷史文化意義。
一、大同湖:大同青蛙崇拜的客觀基礎
大同的蛙崇拜離不開遠古時期大同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大約在一千多萬年前的中生代末期和新生代初期,一連串劇烈的地殼差異性升降變化和山體構造活動,導致大同地塊逐漸下降為洼地,海水倒灌后大規模火山噴發巖漿堵塞河流出口,迅速形成了一個閉合型的大湖泊,考古學家將這個多達九千平方公里的汪洋大海稱為“大同湖”,后又經火山噴發,巖漿覆蓋,地殼變化,湖水蒸發外泄,形成了今天的大同盆地。大同盆地,東鄰石匣里,南界恒山,西抵管涔山,北至陰山,包括今天的山西大同地區的大同縣、陽高、天鎮、渾源、廣靈、左云,朔州的懷仁、山陰、應縣、右玉,及河北陽原縣和蔚縣的部分等12個縣。由于當時大同湖氣候溫暖濕潤,落葉松、冷杉、云杉、榆樹、柳樹、榛樹等珍貴樹種和其他喬木和灌木競相生長,三趾馬、大角鹿、劍齒虎、野狼、野豬、巨駝等動物自由棲息。湖中刺魚、鯉魚、青蛙、麗蚌、螺等水生動物大量繁殖。在這個風景秀麗的動植物王國中,青蛙以其超強的環境適應力,歷經千萬年的進化而存活下來,青蛙“繁殖能力強,產卵數量多”,“雌雄異體、水中受精,屬于卵生。”[1]這一特性,正好迎合了人類追求人口繁盛、生生不息的心理,于是古大同人便將生殖崇拜意識移植到青蛙的身上,青蛙自然擔負起了這一重要角色,成為大同人生殖崇拜的根源之一,青蛙崇拜由此產生并延續至今。
二、“蛙”與“媧”——大同人生殖崇拜的心理選擇
遠古大同人的生殖崇拜源于兩種原因:一是源于自然啟迪,即“蛙”的想象,二是源于文化選擇,即“媧”的崇拜。
(一)“蛙”——大同人生殖崇拜的自然選擇考古發現,沿大同湖的周邊至今保留著青磁窯、許家窯、峙峪、云岡南梁、鵝毛口、李家峪、高山以及虎頭梁等眾多古人類遺址。在原始社會,生產水平低下,生產工具簡陋,險惡的自然環境和無法抗拒的疾病威脅,客觀上造成了古大同人口數量稀少,存活率低,平均壽命短的現實。影響人類繁衍的決定性因素,“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2](P3-4)為解決這一生存繁衍難題,人類從湖中蛙類的繁殖優勢上得到啟示,借助原始想象將腹圓膨大的“蛙”與婦女的“子宮”聯系起來,把對青蛙的崇拜移植到人類自身的“種的繁衍”上,于是生殖崇拜意識便油然而生,成為人類實現族群繁衍壯大的精神追求。基于這一認識,古大同人便衍生出以青蛙為對象的女性生殖崇拜,這不僅解決了當時無法對女性生育做出科學合理解釋的事實,而且也使“女性獨體生殖” 的繁育觀念成為可能,同時也將婦女對后代的繁衍視為莊重而神圣的行為,自此,“蛙”圖騰崇拜便在古大同人心中形成并定型。
(二)“媧”——大同人始祖崇拜的文化選擇大同人始祖崇拜既是氏族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古代宗教由對自然崇拜上升到對人的崇拜的產物。古大同人將青蛙視為自身繁殖的象征,除自然選擇外,還有文化選擇的因素,即對始祖女媧的崇拜。由青蛙崇拜演變而來的女媧崇拜,從神話思維的角度來講,女媧不是一個具體的青蛙形象,而是人化的蛙神,屬神話學的范疇,官方不做過多的關注和客觀的記述,僅存在于民間的口耳相傳中。而從語言學角度來看,盡管“蛙”和“媧”存在著不同的上古音,但從“蛙”的古字“鼃”結構和“媧”的“從女,咼聲”[4](P1777-1778)來看,或掌控天地間的萬事萬物,或創造世間萬事萬物,是整個世間生命的肇始者,人類的先祖、天地的母親。其基礎仍然是以《詩經》和《說文解字》為代表的先秦兩漢語音系統,《詩經》的成集完全是通過官方整理,是在多人多次努力下完成,這是事實。加之《詩經》產生的區域大約相當于今天的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部一帶,包含了考古學上的“大同湖”,所以女媧信仰在遠古大同地區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古大同人把蛙作為人類崇拜的始祖,實質是女媧崇拜在大同民間故事中有所體現。
三、大同蛙崇拜的史實痕跡
大同的蛙崇拜是遠古社會遺留下來的原始信仰的產物,盡管今天的大同,原始時期流傳下來的蛙崇拜的具體形式已非常少見了,青蛙崇拜的觀念也隨時代的進步而淡出,但是蛙崇拜意識的確曾存在于大同民眾的社會生活中,這可從大同地區的傳說故事和自然景觀中找到歷史遺跡。
(一)民間故事中的蛙崇拜 大同地區流傳著許多關于蛙崇拜的傳說故事,最具代表性的是《蛤蟆兒》、《青蛙精的故事》和《青蛙記》三則傳說故事,故事折射出大同人希望通過與青蛙結成的特殊關系而達到轉移或加強人類自身旺盛生殖能力的心理,滿足民眾渴求人丁興旺、生命周而復始、生生不息的美好理想。傳說故事中的蛙崇拜具體表現在:
1.神秘的誕生
在大同的傳說故事里,最能夠體現青蛙神秘誕生的是《蛤蟆兒》。[5](P651-652)故事中,青蛙的誕生帶有神秘的色彩,一輩子無兒無女的老兩口“為了得個后繼,也曾東廟燒香,西寺磕頭,求神打卦,吃齋念佛”,后來好不容易懷了孕,可是經過“12個月”的懷胎最后生下一只“活蹦亂跳的蛤蟆”,但老太太并沒有將這個怪異的“兒子”拋棄,而是像對待孩子一樣把它撫養成人。從故事所表現的主要內容看,屬“AT440A神蛙丈夫型”[6](P89-90)故事,母題是:(1)求子心切的夫婦想要一個兒子,吃齋念佛,上廟敬香;(2)他們得到了兒子,卻是一只奇怪的蛤蟆,老頭兒一氣之下外出經商;(3)蛤蟆兒長大后,鄰居女孩執意要嫁給他;(4)蛤蟆兒帶著信找尋做買賣的父親,父親聽聞后大喜,一起回家完婚;(5)新婚之夜蛤蟆兒脫去蛙皮變成人形,成為一個英俊的少年;(6)在妻子的指引下,父母窺探并藏起蛙皮,蛤蟆兒從此變成人;(7)全家過著幸福的生活。
故事以原始古樸的母題為情節的發展奠定基調,并呈現出四層含義:一是展示了大同民眾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孝道觀念支配下,向神靈祈子,祈求能夠延續香火,繁育后代的美好愿望;二是故事的主人公表面上雖是只蛤蟆,但卻在他的身上處處展現出善良孝順,穎悟絕人,通情達理的善良本性,處處閃爍著大同人純美心靈的美好情操;三是故事揭示了蛙與生殖崇拜之間的內在關系。故事中懷著蛤蟆(蛙的俗稱)的老太太是蛙與生殖崇拜一體化的表現,老太太挺大的肚子是對女性生殖器官——子宮的形象描繪,從青蛙的外形與孕婦肚子的表象上看,共同特點都是渾圓且膨大,是古大同人把對生殖崇拜的目光聚集到青蛙身上的具體表現;四是揭示出在遠古以母權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女性獨體生產繁育了后代子孫,故而大同初民對女性的生殖器頂禮膜拜,當然蛤蟆兒的誕生也預示著新生事物的開始,與文字學推斷的“媧”象征意義共同構成了人類的始祖崇拜。
2.蛙到人的幻化
大同民間幻想故事中的青蛙之所以能夠成為青蛙妻子或丈夫,完成蛙到人的完美幻化,是通過“蛙皮”實現的。“蛙皮”不單單是生物學意義上普通表皮,而且是使青蛙能夠擁有超越一般動物意義上的特異功能,具有神的獨特本領,有著無窮的法力,也是人到神轉化的關鍵,同時也是體現遠古大同人思維不斷完善的過程,《青蛙精的故事》便是最好的說明,故事的梗概是:失去雙親的福順兒在財主三通家打工,30多歲了仍沒有成家。一次放羊的路上,在路邊的雜草叢中發現了唱歌的青蛙精,三通看到福順兒不好好放羊,罵了福順兒并打傷了青蛙精,心地善良的福順兒將青蛙精帶回家放進水缸中悉心照料,青蛙精為報恩德現出人形與福順兒結為夫妻,好色的三通發現了漂亮的青蛙姑娘進行調戲并百般刁難福順兒。三通知道了青蛙精變人的秘密后,和老婆一起設計陷害青蛙姑娘。三通老婆嫉妒青蛙姑娘的美貌一氣之下把護身的蛙皮燒掉,失去蛙皮的青蛙精化作一股青煙消失在天際,而失去美妻的福順兒傷心欲絕化成翹首的石頭立在那里。
從故事的內容看,奇特的“蛙皮”使得青蛙不僅有了人的特質,而且也將人變換為神仙,這種從動物青蛙到人再到蛙神的變換是通過蛙皮的巨大作用實現的,它是架起動物與人、人與神之間特殊關系的橋梁,這種關系是大同蛙崇拜發展歷程的真實反映。古大同人從動物蛙的繁衍習性的認識,到對女性崇拜,再到對始祖媧神的信仰無不是沿著故事中青蛙的轉變路線進行的。“蛙皮”的出現使得青蛙精由人變為神蛙,在青蛙精的身上凝聚了遠古大同人對女性的重視,特別是對始祖女媧的重視,正是女性崇拜的象征性表達。故事中的青蛙精出現于雜草與泥土附近,當其受傷時富順兒又將她放置在“浸滿清水”的瓷罐之中,才能使生命得以延續,才能擁有象征意義,可見自然環境為青蛙的不斷繁殖帶來了巨大的益處,同時為大同原始初民蛙崇拜搭建了得天獨厚的現實基礎。
3.人與蛙的結合
遠古的大同人認為,人類與動植物或無生物之間締結某種親屬關系,這種關系和人與人之間形成的親緣關系一樣,是完全可能獲得益處的,而且彼此之間的這種關系一旦確定下來,該動植物或無生物就會履行一定的義務,與他們結成特殊關系的人不僅不會受到傷害,而且還會得到保護。尤其是通過這種親屬關系的建立,動植物或無生物所具有的獨特能力還會轉接到人的身上,而青蛙強大的繁殖能力與人類困難的自身生產形成強烈的反差,于是,人們便甘心情愿地與蛙結合,縱使有千難萬險也要付之實施,以達成目標的實現。大同傳說故事《青蛙記》[5](P635-640)最具典型性,講的是一個關于蛤蟆山由來的愛情故事,故事梗概如下:
七峰山下的老獵戶有三個兒子,三郎在父親下世后遵從父親的臨終遺言娶到了仙女化身的青蛙姑娘,三兄弟分家后,大哥妻子螞蚱精和二哥妻子蜘蛛精妒忌青蛙姑娘的美貌和賢惠,趁三郎不在家時設計對她百般刁難,后終被當年王母娘娘蟠桃會上看中仙女的三頭兇龍抓上了玉龍洞,并強逼其成婚,青蛙姑娘執意不從以死相抗,兇龍將其關進了水牢。于是三郎冒死上七峰山救妻,尋妻路上救得三只熊,三熊報恩指點三郎報仇,并給他靈芝,從神仙爺爺那里得到寶劍,制服大嫂螞蚱精,殺死二嫂蜘蛛精和三頭兇龍,三只熊從水牢里救出奄奄一息的青蛙姑娘,三郎和青蛙妻子和和美美地過著幸福的生活。人們為了紀念三郎除暴安良的功績,把七峰山的第七個山峰起名為“蛤蟆山”。
《青蛙記》的故事盡管篇幅較長,情節發展離奇曲折,是前兩則故事的延伸與拓展,故事中人與異類的婚戀在現實生活中聞所未聞,但是大同民間故事卻將它演繹到了完美的境地。三郎與青蛙姑娘的結合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故事演繹了大同人對凄美愛情的忠貞不渝,三郎為了救出愛妻冒死前往七峰山與兇龍搏斗,而青蛙姑娘在三頭兇龍強逼成婚的情況下拒死不從,體現了對自由愛情的執著追求;二是故事典型再現了我國傳統婚姻習俗,整個過程包含了良辰吉日的選擇,鼓樂的演奏,拜天地,入洞房等婚慶儀式,如在“吉日良辰”,三郎抱著妻子青蛙“在樂鼓聲中拜天地,入洞房”,儼然是古老婚俗的故事化展示;三是故事中三頭兇龍強逼青蛙姑娘成婚的情節,雖然有遠古大同搶婚習俗的翻版,再現了大同地區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的多元文化傳統的特點,但是青蛙崇拜的意象極為鮮明。總之,《青蛙記》故事中這種奇特的人與蛙的婚戀是大同民眾希望通過像夫妻之間所結成的直接血緣關系,將青蛙旺盛的繁育能力和頑強的存活率移接到人的身上,使得人類與青蛙一樣子孫后代循環往復,無限延續。
4.傳說故事的深層折射
大同三則青蛙故事以蛙崇拜信仰為基礎,所描述的內容與大同民眾的審美追求合二為一,有著四層深層折射,其特點為:
第一,神奇的婚戀。故事中人與異類神蛙的婚戀實質是中華婚俗的變相展示,盡管青蛙與美女或青蛙與男子的結合神奇、神秘,如蛤蟆兒與鄰居女孩的結合,福順兒與青蛙精的婚戀以及三郎與青蛙姑娘的愛情,但是仍然可以窺探出我國傳統婚俗無比清晰的婚娶過程。
第二,蛙圖騰崇拜。大同民間神蛙故事傳承了傳統文化中的信仰基礎,將青蛙神圣化為蛙神并作為遠古某一氏族部落的圖騰予以崇拜。借助文字學“音近義通”[7]的語用原則,即“蛙”與“媧”音相同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人類智慧的巧合,筆者認為大同初民或許曾以蛙為氏族部落的圖騰,后將其轉化為以蛙神為象征對象的生殖崇拜,對女媧崇拜也由此過渡而來。
第三,故事生活化。三則青蛙故事的幻想情節充實了生活細節描寫,不論是神蛙的出世,還是成婚、遭難,乃至最后美滿的幸福生活,都充滿著人情味和人性美,總能使一個個虛構的神奇幻想故事具有親切感人的藝術魅力。語言敘述古樸淺俗,既貼近當時人們的口語,又融合有今天的方言,對話傳神優雅。
第四,人物形象鮮明。三則神蛙故事除去跌宕起伏的情節之外還塑造了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寄寓了大同民眾的審美理想,表現出大同人愛憎分明。故事中的神蛙丈夫雖然外貌丑陋,但他“孝順”、“能干”、“心地善良”,并且具有超群的膽識和力量,是大同民眾審美取向的外顯。青蛙姑娘穿上“蛙皮”是神,脫了“蛙皮”是人,她“貌美能干”、“眼盈秋水,面似嬌花”,濃彎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挺的鼻梁、櫻桃般小嘴、雪白的皮膚、楊柳般的腰枝以及善良的心地,賢淑的品行,對丈夫的愛忠貞不渝,心美如畫的愛情追求,實在是大同人美好愛情的現實寫照。
(二)自然景觀中的蛙崇拜 大同人對蛙的崇拜不僅僅存在于亦真亦幻的民間傳說故事中,而且現實生活里也可探尋到它的蹤跡。其中最能體現大同蛙崇拜的自然景觀是坐落于大同市南郊區的蛤蟆山,它是大同民眾對蛙崇拜的活見證。
1.蛤蟆山的地理位置
蛤蟆山位于大同市南郊區口泉鄉的西南部,離大同市區約19.4公里,海拔約1312米,宛如蹲著的大蛤蟆,她頭朝正南,張開大嘴,仰頭嘶鳴,似在講述一個遠古的秘密,其背微微隆起,后腿蜷縮著蹲爬在地,前腿支撐著整個身體,從山的正東方向可見山的尖頂,那便是蛤蟆鼓鼓的眼睛。山峰野草競相生長,仿佛綠色蛙衣,尤其在清晨或夕陽掩映下,繚繞的煙霧晚霞,為蛤蟆山平添了幾分超自然的靈氣,若是微風輕拂,草木搖曳,掩映其中的蛤蟆更顯蠢蠢欲動之勢。
2.蛤蟆山:古大同人青蛙崇拜的神山
“人對自然物體進行崇拜時,總是將某種神性賦予了自然物體,或以自然物體具有神性為前提”。[8](P101-102)蛤蟆山是賦予了神性的自然物體,她迎合了古大同人對青蛙的崇拜心理,是古大同人青蛙崇拜的神山。盡管至今仍沒有有力證據證明,但從大同湖周邊眾多古人類遺址的史實,以及流傳至今的原始古樸且類型齊全的青蛙故事,我們仍不難猜想、推斷出古大同先民就是把蛤蟆山作為自己的神山來頂禮膜拜。大同先民之所以如此崇拜,并不是單純地將其作為自然景物來看待,而是關注隱匿其中的蛙神所具有的超自然的神力,當然這也與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有關,因為蛙神能給人提供降福納吉,去惡避災,降子繁衍的神奇力量。在古大同人心中蛤蟆山是有生命的神山,她一方面承載著民眾蛙崇拜的社會心理,另一方面也寄托了始祖“女媧”的崇拜,這種將青蛙、蛤蟆山、蛙神、女媧融為一體的崇拜心理,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以傳說故事的形式,斷片似的保留至今,實屬罕見。雖然先前蛤蟆山輝煌的光環不再被民眾所張揚,但是作為挖掘保護的意義則格外重大,我們有義務、有責任以祭拜禁忌的姿態,讓蛤蟆山,讓蛙神,讓媧祖重新煥發青春,綻放出天地人合而為一的思想光芒。

位于大同市南郊區口泉鄉西南部的蛤蟆山
四、大同蛙崇拜的文化意蘊
大同蛙崇拜是母系氏族社會生殖崇拜的產物,蛙崇拜作為民間大眾心理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伴隨著古老的歷史而來,展示了一定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況和審美取向,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和社會意義。
(一)大同蛙崇拜是原始文化的傳承與再現
大同蛙崇拜是原始文化中的一種,是遠古人類精神文化的核心。作為承載大同遠古人類傳統文化記錄的蛙崇拜,以其普通的民眾生活、淳樸的思想和美好的愿望,書寫了一部普通民眾史、底層社會史、民間文化史,排列出了古人類文化演變的時間序列。盡管存在約200余萬年的大同湖在晚更新世消失了,但是這種巨變并沒有使人們的原始信仰消退,反而以傳說故事的形態傳承下來。對它的探索研究,不僅能幫助我們了解遠古時期的歷史與文化,而且可以知曉現代社會人民大眾的精神世界,對開發傳統文化資源,促進多樣性文化的生成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大同蛙崇拜的探究有利于文化遺產的保護表現在文化遺產的保護上,可以讓人們由對蛙的崇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女性生殖崇拜、始祖女媧崇拜的研究,延伸到對該意識下產生的民間傳說故事、人文景觀、遠古生殖崇拜、精神信仰以及人類社會的歷史變遷有更深刻的了解。然而,與神奇的蛙崇拜格格不入的是,大規模的開山取石不僅毀壞了蛤蟆山的前部和周邊山體,而且修路挖斷了蛤蟆的脖頸,遠遠望去山上石塊凌亂,植被裸露,山下廢棄物隨處可見,山上山下渾身縈繞著煤土塵埃,使原本雄渾端莊的蛤蟆山面臨消失的危險。保護,尤為急迫保護,需要我們以蛙崇拜為探究對象,深入發掘其文化價值,以喚起民眾保護傳統文化的意識,增強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觀念,激起民眾的危機感和責任感,運用多種手段還原蛤蟆山的歷史風貌,讓蛤蟆山依然成為今天大同人心中祈求多子多福的神山,使之成為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典范。
[1]劉范弟.蛙(蟾蜍)與女媧[J].湖南城市學院學報,2010(02):33-37.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黃友賢.海南黎族蛙崇拜溯源[J].廣西民族研究,2008(04):143-148.
[4]王筠.說文句讀[M].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5]大同市十大文藝集成辦公室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大同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6](美)乃通著,鄭建威,商孟可,段寶林等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7]王貴生.從“圭”到“黿”:女媧信仰與蛙崇拜關系新考[J].中國文化研究,2007(02):103-112.
[8]陳 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rog Worship in Datong
ZHANG Rui1,XUE Wen-li2
(1.National Institute,Hubei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Enshi Hubei,445000;2.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With the aid of stories about frog worship and the Toad Hill,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basis of frog worship and reveal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worship of frog and female reproductive organs 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worship in Dat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Datong lake;frog worship;legend;toad hill
I276.3
A
1674-0882(2014)03-0033-05
2014-03-12
2007年山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2007041035-05)
張 瑞(1990-),女,內蒙古烏蘭察布人,在讀碩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學;
薛文禮(1964-),男,山西朔州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民間文學。
〔責任編輯 馬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