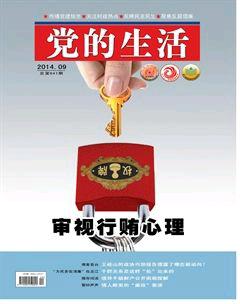話外音
據《新京報》報道: 2014年1月8日和5月4日,江蘇省南京市市委書記和市長視察了同一個地點。事后,當地政府官網上的兩則視察報道,除了日期、領導職務和名字不一樣,其余內容居然一模一樣,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一點不差。
評論:新聞報道出現令人難以辨認的“雙胞胎”,無疑是記者采訪不深入、不扎實造成的,說明“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還停留在口號上。在全黨認真解決“四風”問題的今天,需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的不僅僅是記者,領導干部也應包括在內。形式主義的調研、視察,往往導致形式主義的宣傳報道。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 “我們膽子小,人老實,錯過了2008年以來舉債發展的黃金期。”西部地區一位干部說。在接受采訪的基層干部中,不少人對當地近幾年沒能大規模舉債發展而深感遺憾。
評論: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過度舉債的教訓不能說不深刻。然而,至今還有相當一部分政府官員對過度舉債帶來的嚴重危害缺乏清醒的認識,仍糾結在“悔不當初”的情緒里。這種缺少理性態度的“遺憾觀”一旦形成舉債沖動,其后果是令人擔憂的。
據《西安晚報》報道: 湖南省北部某縣擁有一般公務車100來輛,如果全部取消,一年可以減少上千萬元的財政支出,但同時得拿出近4000萬元給全縣7000多名公務員及按公務員管理的事業編制人員發放車補。
評論:公車改革的核心目的是節省財政開支,降低行政成本。但如果越改越費,就與車改的初衷背道而馳了。目前,我國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出現不同狀況實屬正常。但無論怎么改,都應該基于一點——不增加納稅人負擔,更不能把改革變為權力自肥的盛宴。
據《南國早報》報道: “蓋個章竟要收70元?”近日,有網友發帖質疑,廣西靈山縣武利鎮武利居委會向居民收取“蓋章費”。居委會干部回應稱,他們收的不是“蓋章費”,而是居民“捐資”,用以維持居委會的正常運轉。該鎮黨委書記對此表示,收費屬于違規,鎮紀委已介入調查。
評論:“捐資”當屬自愿行為,但“被捐資”,群眾就難免怨聲載道了。近些年,基層亂收費現象屢禁不止,原因很復雜。解決此類問題,既需要加大問責力度,又需要從根本上堵塞漏洞——不能既讓馬兒跑,又不給馬兒草。不然,“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情況注定還會發生。
據《京華時報》報道: 2013年4月,安徽省宣城市女孩江亞萍在報考南京市人社局時,只因不是南京戶籍而被拒之門外。經過長達15個月的訴訟,江亞萍近日拿到1.1萬元的賠償款,這也為“全國首例戶籍就業歧視案”畫上了一個標志性的句號。
評論:消除包括就業歧視在內的各種歧視,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內在要求,既需要完善的制度支撐,也需要每個公民像江亞萍一樣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維權,更需要社會各方面特別是用人單位自覺地遵紀守法。隨著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全國首例戶籍就業歧視案”一定不會成為一件孤案。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 張某被安徽省紀委帶走接受調查之后,其妻王女士想找關系“撈人”,結果被自稱“能擺平紀委”的任鵬宇陸續騙走1460萬元。最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此詐騙案做出終審判決,判處任鵬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評論:“花錢“撈人”被騙,對上當者而言當然是“壞事”,但對社會來說則不失為一件好事。一些涉嫌違紀違法的官員家屬之所以不惜重金“撈人”,是因為堅信“有錢能使鬼推磨”,也是因為遵從可以凌駕于法紀之上的“潛規則”。可以斷言,隨著反腐敗力度的不斷加大,花錢“撈人”的市場會越來越小。
據《春城日報》報道: 2014年2月,四川省眉山市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鄭某在云南省大理市交通肇事撞死路人,打算讓弟弟頂包。交警識破“頂包計”后,鄭某被檢察機關起訴。鄭某所在單位領導親自跑到大理,向當地法院遞交了免予刑事處罰請求函,以組織的名義請該院對鄭某免予刑事處罰。近日,鄭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
評論:部下觸犯法律,單位領導從四川遠赴云南,甚至還遞交了一份免予刑事處罰請求函,真算得上是“關愛有加”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以求情方式關愛下屬的做法未免有些荒唐——如果法律可以為此“高抬貴手”,那么,哪還有什么法律的尊嚴可言!
據《湖北日報》報道: 為進一步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嚴防“四風”反彈,中紀委監察部再次于官網開通“公款送月餅等‘四風問題舉報窗”,從8月10日起,每周對違反規定者點名道姓曝光。
評論:點名道姓地公開曝光,不僅是行之有效的震懾手段,也保障了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在其他一些領域,還需要更多公開的點名道姓,需要更大程度的開放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