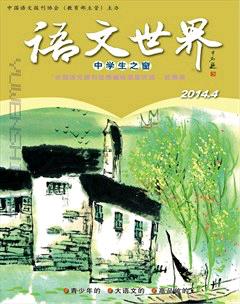夜深還照讀書窗
葛兆光
燈下讀書,想起宋人劉子翚兩句詩:“明月不知君已去,夜深還照讀書窗。”不覺愴然。現在已經很少有閑人讀閑書的閑情了,明月不知人已去,依舊來照,已不再是讀書窗。就是讀書,也不再有“臨月漫披卷,憑欄且數星”的情致。都市的燈光早已把明月擠成了昏黃的一片,遙遙地掛在天邊,印刷體加洋裝封皮也不像線裝書那樣可以握成一卷,更不像線裝書那樣容易撫慰焦躁的心境,不拿筆記本與卡片紙是不能記憶這紙上意思了。陶淵明“不求甚解”的讀書法在今天大概是考不中文憑的,換作了今天,他一樣只能在燈下操起放大鏡一字一句地尋章摘句。
現代人從小讀書,說來比古人多得多。據說孔子“學富五車”,以竹簡折成鉛字算來,他肚子里也不過就是三本兩本。杜甫所謂“讀書破萬卷”,萬卷其實是夸大而言其多。現代人又何止讀萬卷書?可是現代人既成不了圣哲,也成不了詩圣。現代人讀書太實用,本來,讀書并不在多寡,知識未必是智慧,但現在這個一切都需要分斤掰兩拿計算器來估量價值的時代,“急用先學、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讀書法,加上“書中自有黃金屋”之類的讀書觀,早已把“讀書”二字從樂趣變成了折磨。讀書已淪落到和木匠磨斧頭,裁縫理針線沒什么不同的境地。《朱子語類》云:“學須先理會那大底,理會得大底,將來那里面小底也自然通透,今人卻是理會那大底不得,只去搜尋里面小小節目。”只這“大”“小”之分中便有個讀書真意在。“大”不是肚皮里可以車載斗量的知識,而是心靈中無可計算的智慧,讀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心智的潤養。
公正地說,讀書可分兩種:伏案苦讀細啃書,記得公式,背得數字,每到領悟處不禁長噓一聲,是書生苦事。這時猶如爬山,一山放過一山攔,攀登時想的是文憑,是課題,是職稱,是經世致用,“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和“功名如探囊取物耳”是一回事,書中文字被讀成肚里知識。品茗呷酒漫讀書,心與書通,忘卻經營生計、案牘文字,每到會心處不禁拊掌,是賞心樂事。這時雖人問書中所言何事均渾然忘卻,但書中意味則如鹽化水中,時時在心頭提撕點撥,讓人自省,催人自覺,于是書中文字化為心頭素養。
誠然,時代在變,文人那點閑情也許已不合時宜了。不過,如果能在電話鈴聲、汽車笛聲、機器轟鳴聲中留下一小片安靜,讓人體會閑讀書、讀閑書、讀書閑的滋味,如果能在霓虹燈光、白熾燈光、探照燈光中給明月留下一點縫隙,讓它來淡淡地照一照讀書人的書案書窗,似乎也還能給人一線安慰。在連嘆息都沒工夫的歲月里,人怎樣才能將知識轉為智慧?其實,讀書仿佛旅游,人何必處處拍照留影,處處題寫“到此一游”,那山水溪石林壑松風在心頭留下些快意,殘存半分溫馨,讓人回想起來就忘卻了塵世的疲憊與困惑,這不也就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