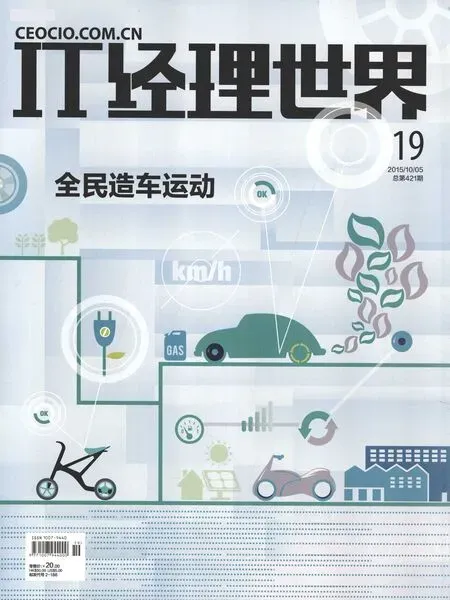鵬華基金:構建“失控”的IT系統
鐘嘯靈

凱文·凱利(Kevin Kelly)是馬化騰最推崇的一位硅谷大咖,他所著《失控》一書影響了很多人,鵬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術部總經理朱瑜就是擁躉者之一。
雖然此書是在近幾年才引入中文版,風靡國內科技界,但朱瑜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熟讀此書,并將書中的理論應用于他的工作實踐中。
舉例來說,大多數IT同行普遍認為,一定時間內應該凍結客戶需求不做變更響應,但朱瑜提出要擁抱需求積極響應變更;在談及IT規劃時,他表示不做太多規劃,讓系統處于一定自然成長的失控狀態,打造一種平衡的內部IT生態系統。
《失控》是凱文·凱利對當時科技、社會和經濟最前沿的一次漫游,以及借此所窺得的未來圖景。書中提到并且今天正在興起或大熱的概念包括:大眾智慧、云計算、物聯網、虛擬現實、敏捷開發、協作、雙贏、共生、共同進化、網絡社區、網絡經濟等。可以被稱之為一本“預言式”的書。
“這本書完全打開了另外一個世界,包括我談到的敏捷開發、生態系統等很多概念都來自于作者,它幫助我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模式。”朱瑜表示。
對他影響至深的另一本著作來自王陽明的《傳習錄》,受書中“知行合一”思想的影響,他逐漸形成一種高效、務實、重視實踐的工作方式。
鵬華基金也逐漸成為一家以信息技術為主要驅動力的基金公司,處于基金行業綜合實力十大公司之列,截至2014年一季度,公司管理資產總規模達到1443.42億元。在京東今年推出的首批 “小金庫”上線兩款貨幣基金產品中,鵬華基金的“增值寶”貨幣基金即是其一。
構建IT生態系統
2008年朱瑜到鵬華基金上任時,公司內部對技術處于看似重視又不重視的模糊狀態。投資交易系統本身依賴IT,因而鵬華基金內部很依賴核心系統,但日常業務和管理上還沒有應用更多的技術支持,員工的日常工作更多是通過紙質的方式流轉。當時的情況與現在管理層、業務部門開會溝通時,每人言必談數據的情況截然不同。
面對當時的狀態,朱瑜對《失控》一書的思想進行了實踐轉化——不需要做太多的IT規劃,主要是確定系統整體架構、團隊工作模式等,余下的讓系統處于自我修正,以部分放任的狀態,打造一種平衡的內部IT的生態系統。
受《失控》關于生態系統的理論影響,朱瑜認為,一家企業內部的IT系統類似一個生態系統,生態系統的基礎往往不是大型生物,而是一些微生物,微生物通過進化逐漸演變為更復雜的生物。這里的微生物指的是通過技術可滿足用戶基本需求。
為此,朱瑜采取的第一個策略是,激活業務人員的需求。“企業的IT發展一定取決于業務需求,而不是IT投資多,業務就必然發展”。在具體的做法上,他選擇了兩個業務部門,試點推行一些節省人力、改善效率的系統,業務部門很快感受到了技術的好處,帶動各個部門逐漸形成提出各種需求的習慣。
他采取的第二個策略是,為新生態系統建立適合微生物生長的土壤,即建立一個包含流程平臺和數據平臺的底層平臺。按照業界的傳統思維和做法是,應用先行,后做平臺。朱瑜則“背道而馳”,他認為,打造一個友好、統一的平臺,后期可以省時省力,這種做法也源自《失控》一書所提倡的敏捷開發。平臺僅半年時間即實現全部部署,鵬華基金據此建成包括流程平臺和開發平臺在內的大平臺,真正支持后續的敏捷開發和快速迭代。
在建立統一平臺后,朱瑜做了一個現在看來非常正確的決定:基于平臺建立新的外包開發機制。就普遍情況來看,企業在建設一個IT項目時,一般采取外購或項目型外包的方式進行。由于有了強健統一的平臺支持,鵬華基金要求外包的IT團隊駐場公司,并且基于平臺的標準進行開發,因此可以很好地控制公司IT項目開發的質量、應用的統一性和延續性,也便于對整體的應用進行管控。
IT團隊也得以完成一個很好的轉型。原來企業在采用項目型開發的外包服務時,乙方人員一進場,甲方人員就變成了“包工頭”,主要工作是每天監督乙方的工作進度,可是項目一旦開發完成,乙方人員離場,甲方還是不知道內部的設計細節。鵬華基金自從采用基于統一平臺的開發機制,便對自身的甲方人員提出更高的要求,甲方需要具備更高的技術技能、包括把控需求、設計主要的技術路徑,從長遠來看更有利于IT團隊能力和價值的塑造。
另一方面,朱瑜摒棄傳統的、相對保守的技術思維,“天下武功唯快不破,IT應該是不斷試錯的過程”。這種思維與傳統的IT思維完全背道而馳,傳統的IT思維厭惡風險,害怕出錯,為此前期需求調研時間很長,應用推出的周期冗長,業務部門等待時間過長,客戶滿意度較低。
而《失控》倡導在一個生態系統的構建中,每個單元都要切割得足夠小,并且相互獨立,可達到共同進化目標。朱瑜的破解方式是,將每個應用切分到足夠小,降低每個應用錯誤的風險,快速迭代推出應用,首先滿足客戶的關鍵需求。“我們對一個IT項目的定義是,除去核心系統,一個在3個月以內的項目才叫項目,超出3個月的項目不叫項目,而是項目群。 ”
這種思維在實踐中俯拾即是,比如,在構建這個生態系統的過程中,朱瑜看到,一個企業的IT生態系統,除了有微生物(即各種應用)外,另外一個特征是如何讓它們之間會構成非常復雜的交互,因為有了聯系才能激活產生更復雜的東西,而這種聯系用IT的語言表述就是流程。一般而言,很多企業會設計很多長流程,有的企業的流程環節可以多達驚人的30多個節點。
受《失控》倡導的小單元、協作、共生、共同進化的影響。朱瑜采取了一種新做法,將一個流程的設計控制在4到5個環節內,并且將流程之間的關系設計為可以相互調用,即一個流程可觸發另一個流程,各種短流程形成一種網狀調用關系,“在產業變化很快的情況下,經常需要變化流程的調用關系,短流程可以比較靈活地完成這種調用。”
管理客戶需求
讓流程彼此產生聯系后,朱瑜為一個閉環的生態系統構建最后關鍵的一環,也就是有效管理客戶的需求。
客戶的需求實現程度往往直接關系到項目效果。如果你問一位CIO,可否量化一個項目的效果,他們多半會表示很難被量化,事實上這已成為很多企業在進行IT投資時的一項顧慮,也是IT部門被詬病的主要原因。為此,IT部門需要在前期有效的管理客戶需求管理,便顯得尤為重要。
朱瑜通過多年的技術實踐,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技術思維的觀點,“世界上任何東西都可以量化,一開始的評估不是那么準確,隨著后續改善,量化方法會越來越準確”。他將量化的管理模式應用到IT項目中。除了戰略型系統,朱瑜將公司內部的改善型系統、數據支持型等兩類系統,從使用角度進行量化,包括需求管理、IT實現程度、業務期望值的角度,考量IT是否已經滿足業務的期望。
以需求管理為例,他和IT團隊在開始建立IT系統時,便在系統中設置一個默認規則,那便是建立客戶的使用日志。通過使用日志,管理層、業務層的每一個使用者都可以了解公司整體系統的使用情況:哪些系統使用的頻率更高,哪些功能用的多,哪些功能用的少等。
通過這一設置,公司內部形成了一種新觀念:一個系統用得好不好,首先源于業務部門的需求提得好不好,業務部門應該對這些需求負責。如果業務部門提出一項需求,但實際上并不使用這些功能,說明當初的需求提得不好。
為了幫助業務部門更好地提出需求,朱瑜一方面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模式,每個月IT團隊會和各業務部門定期溝通,了解業務變化、需求變更。另一方面建立管理一個項目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模型,覆蓋初始化階段、規劃階段、執行階段、關閉階段、檢查階段。
“很多IT人員工作的習慣是,拿到需求后,馬上就投入需求實現的工作中,沒有人追問需求提得是否合理。”朱瑜表示。為此,他在管理模型中建立初始化階段,即IT部門接到一項需求后,不馬上執行,而是先對需求進行初始化,探究需求背后的動機,了解業務部門的真實想法、管理者的想法、技術人員的想法,各方達成一致,確定需求的內容是否合理后,才會開始進入規劃和執行階段。
對于很多IT團隊而言,平時最頭疼的并非項目型需求,而是來自用戶平時的零散需求,這些并非來自一個項目,而往往來自對現有某一項功能的改進,或者臨時需要對一部分數據進行處理等。面對這些零散需求,一般企業的IT部門會采取拖延戰術,盡可能不做響應。因為在傳統的IT部門思維里,在一個系統的漫長開發和使用階段,在一定時間內要凍結變更和新增的需求,不做任何變更,這是一種習慣做法。這種做法與成本關系不大,僅僅是企業級IT資源提供的慣性模式。
而朱瑜在內部提出不拒絕變更,要擁抱變更,“一個好的系統是設計出來的,一個好的系統也是用出來的”。在他看來,一個系統在用戶的使用中,必然因為用戶的習慣和業務變化,產生各種需求,而IT部門通過小修小補的多次改變,才能逐漸讓系統變得友好易用。反之,如果一個系統不做任何變更,用戶逐漸便不愿意使用,系統也就荒廢了。
在實踐中,他一方面積極管理用戶的需求,另一方面有必要時對系統進行重構。比如,公司的很多系統經常需要調用產品信息,他便將產品信息從其他系統中剝離出來,建立了一個獨立的產品信息系統,以方便其他系統對產品信息的調用。“我最驕傲的事情是,做出的系統在10年20年以后,大家還在用”。這并非空想,他在乙方任職期間參與開發的一套核心系統,目前還在甲方公司運轉,至今已有15年。
隨著來自業務的需求越來越多,鵬華基金引進流行于制造業的看板管理,現在看板被設置在IT部門中,那些重要的需求會被寫在看板上。接下來他會將這個看板逐漸挪到IT系統中,每個IT人員都可以看到哪些需求正在排隊,哪些需求正在解決中,以及哪些需求已經解決完畢。通過這一設置,每個人可以看到流過IT解決管道的流量,“他們不要為了追求數量而犧牲質量”。
現在朱瑜開始關注核心系統的開發,并加緊規劃移動平臺、大數據平臺,基于這些新平臺,他在思考一些可以幫助業務創新的問題。比如,如何通過大數據幫助投資人員做好投資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他希望IT團隊都具有投資研究知識和新技術的應用能力,“以后的項目做成什么樣,我希望這是團隊的想法,而不是我一個人的想法,這也是失控的一種體現。 ”
朱瑜多次談到《失控》的各種觀點,不過即便如此,他仍然認為并非人人都適合這種模式,“我自己經常捫心自問,換一個公司,你是否還能做出這樣的事情?”。他也經常會自比世界級的基金公司,而常常覺得差距還很大,某種程度上,他以一種類似喬布斯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狀態,不斷地尋找前進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