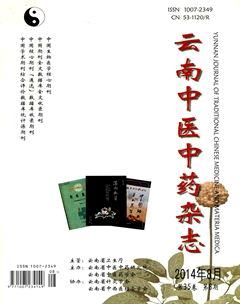健脾滋陰法論治消渴病
王萍 趙泉霖
摘要:近代醫家對消渴病從脾陰虛論治均有獨特見解,引述古代醫家“脾虛致消”的論述及現代醫家的見解和臨床研究,從脾陰虛與消渴病的發病關系分析,結合臨床論述了健脾滋陰法在現代消渴病治療中的應用。
關鍵詞:消渴病;健脾滋陰法;臨床經驗
中圖分類號:R255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4)08-0015-02
消渴病,歷代醫家對其病機多認為以陰津虧損、燥熱偏盛為主,治療上多從上、中、下三消論治,如《醫學心悟·三消》云:“治上消者,宜潤其肺,兼清其胃”,“治中消者,宜清其胃,兼滋其腎”,“治下消者,宜滋其腎,兼補其肺”。然而《靈樞·本藏篇》有“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之說,消渴發病以陰虛為本,且陳修園云:“脾為太陰,乃三陰之長,故治陰虛者,當以滋脾陰為主。”故健脾滋陰法是治療消渴病不容忽視的治法之一。
1健脾滋陰法的理論依據
《內經》云:“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養四臟。”《素問·生氣通天論》:“陰者,藏經而起亟也。”張錫純云:“脾陰足自能灌溉諸臟腑。”《慎齋遺書》云:“善多食不飽,飲食不止渴,脾陰不足也。”《何氏虛勞心傳》:“陰虛成病,十之八九;陽虛成病,百無一二。……然勞倦傷脾,乃脾陰分受傷者多”。均強調了脾陰在臟腑調節中的重要作用,而消渴病中諸臟陰虛未有不損及脾陰者,脾的運化升清功能失常,則津生無源,且津液不能上承布散,肺津干涸,化燥生熱,故需飲水自救,而出現口渴多飲;胃乃燥土,喜潤而惡燥,脾虛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胃失潤養,致胃熱亢盛,熱者善消谷,而見消谷善饑。脾不能轉輸水谷精微,津液趨下,濁陰下流,注于小腸,滲于膀胱,故小便頻數而長,水谷精微末經肺之宣發變味而用,故下流原味而出,出現小便有脂而甜。津液不能濡養肌肉皮毛,而見皮膚干燥,身體日漸消瘦。五臟陰虧也可導致脾陰受損,如腎陰不足,腎水枯涸,不能上滋脾陰,虛火上熬脾陰,則脾陰虛致消,故健脾滋陰法治療消渴病與其病機特點頗為契合。《醫學入門·消渴論》曰“治渴初宜養肺降心,久則滋腎養脾,蓋本在腎標在肺……然心腎通于脾,養脾則津液自生。”
2健脾滋陰法的潛方用藥
《素問·五臟生成篇》:“脾欲甘”,《臟氣法時論篇》:“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瀉之,甘補之”。脾之正味為甘,故健脾滋陰藥物總以甘味為主,佐以甘淡、甘微寒或苦味藥等。甘味藥性多平緩,宜于滋養脾陰。脾喜燥惡濕,淡能滲利脾濕,甘淡相合,寓補于瀉,滋而不膩,滲利水濕而不燥,所選藥物宜生津質潤、甘淡平和、守陰健脾之品;甘微寒以滋養脾陰,所選藥物宜微寒不礙脾;甘苦以堅脾陰,所選藥物宜化濕健脾、滋而不膩。常用藥物如扁豆、薏苡仁、茯苓、白術、山藥、玉竹、桑葚、沙參、葛根等,佐以烏梅、石斛、天冬、麥冬、百合、天花粉等甘寒或酸甘滋陰化陰之品,另可配伍益氣溫陽之品“陽中求陰”,以達“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效。
3病案舉例
患者男,52歲,2013年11月19日初診。患者自述5年前因“乏力、多飲伴消瘦4月余”就醫,于當地確診為糖尿病,后口服二甲雙胍、消渴丸治療,未嚴格飲食控制,效差。就診時訴口干多飲,乏力,頭暈,視物模糊,納少,眠差,夜尿2~3次,大便質黏,便后不
中華醫學會醫學教育分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醫學教育專業委員會2012年度醫學教育研究立項課題(2012-LC-52) 爽。舌體偏胖,色暗,苔白膩,脈弦數。空腹血糖107 mmol/L,餐后2 h血糖143 mmol/L,尿糖(++)。治以健脾滋陰,益腎平肝。處方:烏梅10 g,黃芪30 g,炒山藥30 g,茯苓15,丹參20 g,葛根30 g,沙苑子30 g,黨參20 g,炒白術15 g,枸杞20 g,黃精30 g,炒棗仁30 g,鉤藤30 g,天麻10 g。水煎至500 mL,早晚飯后溫服,日1劑。12月3日復診,自述乏力、口干多飲較前減 輕,納少,眠可,小便略頻,大便質可。空腹血糖89mmol/L,餐后2小時血糖128 mmol/L,尿糖(+)。處方:上方加雞內金10 g,炒山藥30 g,金櫻子30 g,治療1月后復查空腹血糖:74 mmol/L,餐后2小時血糖:96 mmol/L,尿糖(+),體力增加,偶有口干渴,納眠可,二便調。囑其守方繼服半月,后口服玉藍降糖膠囊,隨訪病情穩定,未見復發。(收稿日期:201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