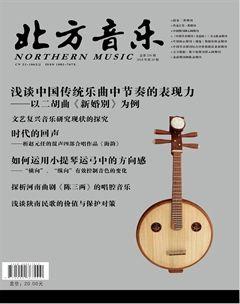音樂表演中的意向性問題之微探
謝靜楊
【摘要】“意向性”活動是人們生活中一個客觀存在的狀態。人們作為意向性的一方,去認識意向對象,并對其進行意義設定,將所看到的現象轉為人腦中的表象,并分析綜合判斷其本質,這就是“意向性”活動的過程。音樂表演也是一個認知的過程,必然包含著一系列的“意向性”活動。作為一個優秀的表演者應該使意向性活動更好地發揮作用。文章試圖從現象學以及心理學等角度分析一系列的“意向性”問題,并闡釋其在音樂表演中的運用。
【關鍵詞】意向性;音樂表演;意念;現象學
當下,音樂表演領域,重技輕藝的現象比比皆是,許多人認為只要有精湛的表演技巧,再現出樂譜的內容就可以算音樂表演了。特別是在對待考級的問題上,許多家長只是為了拿到證書而拼命學曲子,而忽視了樂曲的內涵和表演的意義。
毋庸置疑,嫻熟高超的技巧是音樂表演得以成功的前提和基礎。沒有技巧,談不上音樂表現。但技巧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只是音樂表現的手段。音樂表演最終目的是準確、無誤地展現出音樂及表演者的內涵與風格。劉德海先生在《鑿河篇》中說:“技差而無情理,為劣之劣者;技佳而無情理,為匠之劣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技術又足以副之,為優之優者。”只有技巧與表現兼備的表演者才能稱得上是“音樂家”。
一、與“意向性”有關的概念問題
涉及到“意向性”的問題,就有以下幾個概念:意念:指的是音樂創作中的藝術獨創性。在現代,意念與“意向作用”為同義語。意識:是人對環境及自我的認知能力以及認知的清晰程度。在現象學領域,意識是由意向性與意向對象構成的。意向性與意向對象:意識總是對某物的意識,指向者與被指向者雙方互為相關項。指向一方為意向性,稱為“內在主體”;被指向一方為意向對象,稱為“內在客體”。意向對象的意義就是由主體設定的,而這一設定的過程就叫做意向作用,即人的意念。故由以上幾個概念,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意向對象的意義是意向作用即人的意念所設定的。毫無疑問,這一過程必然牽扯到“內在主體”的意向性。
二、現象學中的“意向性”
既然,意向對象的意義必然牽扯到“內在主體”的意向性,那么設定意向對象意義的前提是什么呢?胡塞爾申明了自己認識論的前提:首先,我們所認識的只是物自體的現象,而不是物自體本身。其次,一切都是值得懷疑的。只有直觀現象所提供的“給予性”才構成現象學所承認的可信性的起點。最后,“超越之物”不能作為預先被給予的東西來運用。筆者用康德的一句話來概括:“作為我們的感官對象而存在于我們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樣子,我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它們的現象,就是當它們作用于我們的感官時在我們之內所產生的表象。”
人們在認知事物的現象和設定意向對象的意義時就必須要經過“直觀”與“還原”。“直觀”就是直接觀察,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經驗的直觀即后天的直觀,它獲得的是知覺現象。二是“純直觀”即先天的直觀,它只直觀它的形式。三是理智直觀,即把直觀到的表象給予邏輯的連接,以構成判斷。現象學的直觀是運用現象學方法的直觀,此外還必須進行兩種“還原”。第一,現象還原即經驗的還原。它排除一切“超越之物”,把認識限制于實在的內在意識所直觀到的現象之中。第二,本質還原,就是要從個別人直觀的內在,轉向于一般直觀之中的一般內在。這就必須進行“本質直觀的抽象”。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向性”,都可以設定意向對象的意義。但由于個人直觀把握的內容只具有個別現象的意義,而不具有一般的、本質的意義。所以,我們要借助認識的“主體間性”,從個人直觀的個別性過渡到人們直觀的一般性,抽象出其中的“同一之物”,就能知道個人所設定的意向對象意義是否是對象本身及符合事實。
三、音樂表演中的“意向性”問題
若把“物自體”的現象稱為現象甲,把人們直觀之中的“現象”稱為現象乙,可得出以下結論:“對象在認識中構造本身”——也就是“現象甲在人的意識中顯現,與意向作用構成的相關項,被設定為現象乙。”按胡塞爾的說法也可稱作“存在在意識中的消融”。現象甲屬于存在,現象乙屬于意識,而現象甲在意念設定的過程中被現象乙擋住或者掩蓋了,于是現象甲就消融在現象乙之中了。
這里,筆者暫且不討論一度創作,只說二度創作。那么,在音樂表演中:作曲家的生評、創作風格、時代背景以及樂譜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稱作現象甲;而表演者了解作曲家創作風格及思路,將分析樂譜的結果與自己的想法相融合,呈現在腦中的意識狀態就是現象乙。
同樣,意念的設定也可以用皮亞杰的“同化”、“適應”理論來解釋。皮亞杰在《發生認識論》中提到過一個公式:S-A-R,即:一切反應R,都是刺激s經過主體A同化、適應之后做出的反應。而“同化與適應”,是人類接受信息過程中的常規現象。主體A的信息儲存庫就像一個書架,自身形成了一定的結構即“心理圖式”。當新的信息納入主體原有的心理結構,并經由主體原有的信息儲存予以解釋消化,就是“同化”;而主體原有的心理結構在吸收了新的信息之后,所發生的對客體環境的新的適應變化,就是“適應”。由于主體A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所以同化適應出的結果R即在腦中的現象乙也是不同的。
由于主體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認識在具有客觀性的同時,還具有主觀性,也就是人們所理解的對象的不同意義。就像上文所述,不同的人認識的對象是不同的,那么他所設定的意向對象的意義也會不同。認識的主觀性,是屬于認識的內在的“實在”的內容,是由主體意識的區別即由意向方式所決定的。
四、“意向性”問題在音樂表演中的運用
音樂表演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演奏前階段、登臺瞬間以及演奏后階段。經過前文論述,很顯然“意向性”的這一過程對于音樂表演來說,是每個表演者必須經歷的,而“意向”出的結果也是有差異的。
(一)演奏前階段
在這一階段,表演者要完成“把譜面的標記化為個人的內心聽覺”即“分析樂譜階段”,以及“把個人內心聽覺化成為實際音響”即“練習階段”兩重任務。一是分析樂譜階段:前文提到的皮亞杰的“S-A-R”公式,認為一切反應R都是刺激s經過主體A同化、適應之后做出的反應,而讀譜同樣也是接受信息,因為也服從這一規律性。所以,表演者對作品的感覺和理解都經過了表演者本人主體同化的過程,表演者本人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并不重要。有些表演者認為,分析譜子自然而然就產生了認知和內心聽覺,這也可以稱為“直覺起作用”。瑞士的心理分析家榮格認為,直覺是在無意識狀態中的知覺過程,而潛意識和無意識又是意識的兩種狀態。在實際生活中,意識與潛意識是可以進行雙向交流的人們在生活中積累許多信息(現象甲到現象乙的轉變),稱之為“信息儲存”,后由于某種契機或某種相似性的啟發,喚醒了潛意識的信息儲存,就稱之為“信息啟動”。而表演者這種“自然而然”類似于靈感的狀態,就是潛意識領域的信息儲存上升到意識領域,形成創造性想象、產生新的組合,這就是直覺起作用。在這一階段,“同化與適應”、“直覺起作用”都是表演者的意念設定也即意向對象作用設定的過程。通過這一設定,表演者才能夠更好地將譜面的信息借助于自己的頭腦表現出來。二是練習過程:當表演者認真分析并傾聽了樂譜后,內心升起了實際的音響,而這時需要以什么技法來表現和呈現音響,這也跟不同主體的認識性和表演技巧有關。
(二)登臺瞬間
這一階段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思想感情的二重性。我們知道,作品中所表達的感情并不完全是作曲家本人的感情,而是作曲家想象、創造的藝術世界中的特定感情,但這種感情是二重性的,其中必然包含著作曲家個人的生活體驗,雖然這種體驗并不與作曲家切身利益有關。同理,表演者在音樂表演中所表現的感情也和作曲家的感情具有相同性質,也是表演者本人所想象、創造的藝術世界的感情,同樣具有二重性。筆者認為,在這一階段表演者在臺上去創造和想象,去展示藝術的感情,就必然包含著一系列的“意向性”活動,包括意識的構建和意念的設定。但是“意向性”活動是表演者理智的所作所為,而實際在舞臺上,表演者必須進入“規定情景”,將理智和情感相輔相成,激情地投入演出。因為表演者在進入了樂曲的氛圍后,成了樂曲中所表達的人或情感,這一過程都是潛意識在活動,但表演者不能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在演出,而應該有意識、冷靜地控制整個表演過程,這就是意識的過程。就像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說道:“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方能寫之;出乎其外,方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筆者認為這與表演者在理智與情感間游刃有余具有同樣的道理。
(三)演奏后階段
茵加爾頓在《音樂作品及其同一性》中說,音樂作品不等于每一次的演奏。所以演奏具有不可重復性,這就要求表演者能夠自我超越,尋求每一次的突破。而自我突破,就是怎么樣才能把同一首作品演奏得更好的問題。不同的演繹一首曲子的共同特點就是能構成一種部分相似、網狀相似的關系,即“家族相似”的關系。這又引申出“文本”與“型號”。“文本”是作品本質屬性的抽象概念,它不等于實在的物,它符合作品一個“家族相似”的概念。即“文本”就是“家族相似”中各種交叉中的核心部分,也即前文所說的本質還原后直觀出的“一般性”。而“型號”則是由于音樂作品演奏的不可重復性所導致的,有的型號符合文本,有的則不符合。用“意向性”的問題來解釋,可以理解為,每個表演者都會有不同風格的表演,這都是每個人設定意向對象的意義以及技法的不同的結果,但這不同的表演符合與否作品,就需要綜合不同優秀表演者演奏中“同一”的東西,進行比較得出。也就是胡塞爾所說的認識論都是有前提的。
五、總結
“家族相似”中各有長處,若放在同一個表演者身上,由于主體的知識儲備和認識的主觀l生決定著“意向性”活動的不同結果,就存在著不斷向新的目標追求,力求更好地解釋文本的情況。而想要自我超越,就要提高藝術修養、藝術認知、表演技巧。若放在不同的表演者身上,由于主體的藝術修養、藝術認知不同,所以每個表演者在闡釋樂曲的時候,都會產生不同的“意向性”活動,設定出不同的內容。
音樂表演是一個二度創作的過程,既然是創作就要有創新,就需要表演者在認知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再用精湛嫻熟的技法把腦中分析出的音響轉化為實際的音響。俄國文藝批評家謝洛夫曾說,演員藝術的最高成就是:他“所表達的一切都是作者所想的,此外,演員所說的一切都好像是他自己的即興,所有這些思想感情都是一瞬間在他身上出現的。演員的演技完全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并且補充了新的詩意,這樣,所體現的思想可能甚至在戲劇創作時都沒有這樣完美。”筆者認為,這句話同樣適合于音樂表演。真正杰出的音樂表演,是表演者通過一系列的“意向性”活動,探索音樂作品的內在含義,使作品通過自己的表演表現的更加鮮明突出,甚至超出作曲家的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