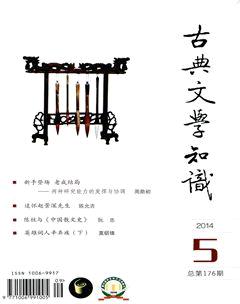新手登場老成結局
兩種研究能力的發揮與協調周勛初晚飯后總要看一會電視新聞,有時也看體育節目,覺得兩種情況差異很大。那些短跑運動員,如百米選手,爆發力特別強,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取得勝利;那些長跑運動員,如馬拉松賽中的選手,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具有過人的耐力與超凡的毅力,然而二者兼能的情況似乎比較少見。學術界中人物也有這種情況,但如協調得好,則可兼容,兩方面都可取得成功。
民國時期的學壇,這種現象比較明顯,而在一些體現新學風的人物身上,更有很多可資借鑒之處。
北洋軍閥之間爭戰不歇,學術領域中卻出現了較為寬松的環境,其時一大批國外留學的精英回國任職,引入了新思想和新方法,這一批人原來的國學底子較好,新舊融合,開疆拓土,揭開了歷史上新的一幕,馀波嫋嫋,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前后。
胡適引進了實驗主義,一切訴之理性,主張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對古來三皇五帝之說提出挑戰,在這股新思潮的推動下,顧頡剛發起的疑古運動,其聲勢之大,影響之巨,突過前人。
顧頡剛于1923年發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直有振聾發聵之勢。其后他又主編或委托他人編有《古史辨》凡七集,對古史的原有體系加以破壞,似有摧枯拉朽之勢。這些地方,可以說具有十足的爆發力。
《古史辨》派提出種種挑戰性的言論之后,也有劉掞藜等人提出詰難,然似不能顯示出什么力度,顧頡剛把反對意見也一一編進了《古史辨》中,這些地方均可看出顧氏的雍容大度,體現出了學者探討真理的精神。比之后來一些人熱衷于憑仗權勢壓制反對意見的作風,直有天壤之別。
經過歷史的一大曲折,大家慢慢認識到,在批評《古史辨》派的人中,張蔭麟的《評近人顧頡剛對于中國古史之討論》一文具有很高水平。他在《一、根本方法之誤謬》中指出:“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意謂靜默之論據)。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其后他又分從《二、夏禹史跡》、《三、堯舜史跡》等方面進行“辨正”,力破顧氏之說。
顧頡剛受胡適的影響,也講求方法,張蔭麟由此進行批判,可謂抓住了要點,不過這一問題的徹底解決,有待日后考古學的發展。隨著近幾十年來田野考古新成果的大量出現,胡適提出周宣王以前的歷史盡不可信的理論早被打破,顧頡剛興起的疑古思潮也已消退,人們要求走出疑古時代。學界普遍認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之說,更具說服力。
張氏歿時年僅三十七歲,未能盡展其才,他的著述中評論文章占了絕大部分,其中對梁啟超、馮友蘭、郭沫若等人的批評,均能片言中的,足以見其目光的敏銳,但總嫌不成體系。他想盡力完成的一部大著《中國史綱》,僅完成上古篇,由于時代劇變,也已很少有人提及。人未盡才,不能不使人產生“人固不可以無年”之嘆。
上面所舉的例子似可說明,大凡學人之成功,創新能力最好的時期,往往在其年輕階段。其時精力旺盛,思想活躍,假如外界約束較少,也就會噴薄而出。年紀大了,精力日衰,人事活動又會急遽增加,這時一些學力好的人往往轉而從事長線工作,像顧頡剛,逐漸轉向《尚書》研究,于此也取得了很多成績。
我們也可看到,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學者,每以一種著作名世,如所謂“九通”之學中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書,杜佑、鄭樵、馬端臨等人花了幾十年功夫,慢慢磨煉而成。這些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編輯者不但要掌握各門學科的豐富內容,還要構擬出一種體系,慢慢梳理,匯成各種系統。長期鉆研,鍥而不舍,畢生精力盡瘁于是,近乎那些馬拉松式的選手。時移勢改,當今社會紛紜擾攘,各門學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以個人之力還想完成這一類型的著作,怕是很難的了。
當務之計,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鑒》的經驗似可借鑒。他邀請了當時最具實力的史學家劉攽、劉恕、范祖禹三人,移居洛陽,遠離政治漩渦,花了十九年的工夫,從纂輯資料做起,完成了這部大書。當時他也具備了很多有利條件,朝廷崇尚文治,反對他的人不對此進行干擾或迫害,生活穩定,一心向學,才能取得成功。
司馬光的治學精神又是這么感人。從珍藏于故宮博物院中的幾頁《資治通鑒》手稿來看,字體方方正正,一筆不茍,體現出了一種極為嚴肅的態度。修改的過程不算,一個人就是用正楷把《資治通鑒》抄上一遍,需要多么大的毅力,難怪司馬光在呈報朝廷時說“臣之精力盡瘁于是”了。這樣的著作自能垂之不朽。
吾等治學,自當以史為鑒。當今政治空氣寬松得多,歪路不必重走,自可從容思考,結合自己的具體情況找一條適當的路走。
對我而言,不論從成長的環境來看,還是從個人的秉賦來看,都有許多先天不足的地方。雖然自己主觀上還算努力,然而總是不由自主,只能隨波逐浪,順乎自然,難以做到后天協調。然而回顧前塵,則又可以說是仍與學術界中人物常見的發展過程有其相合之處。
我在學生階段長期生病,精力不敷,只是思想還是比較活躍。盡管我在八十多歲時還能寫一些長篇論文,也有人稱贊我腦子仍然好使,然而心知肚明,人過六十精力日衰,本來就顯得遲鈍,此時更是悟性大減。三十上下完成《九歌新考》一書,氣勢或許還有一些,也曾獲得過一些贊譽,然而未能闖出一片天地,只能算是試水的新手。數十年來,歷經艱險,不甘自暴自棄,孜孜兀兀,至今仍在握管。只是拖三拉四,鈍刀子割肉,半天也難滴出一點血來。
私心自幸,走的道路還算規范,后半輩子做事越來越順手。年輕時從事先秦兩漢學術的研究,也就為后來的發展打下了一些基礎。老輩學者認為,中國學術起于先秦,治學之人應當在先秦學術上打下一些基礎,即使專攻小說、戲曲,也應如此。我與章培恒討論過這方面的問題,他就推崇孫楷第的成就,認為可稱此中翹楚。而孫楷第之所以能在這領域內取得成就,也就因為他在先秦兩漢的學術上也下過一番功夫。我總覺得,我曾有過一番研究楚辭與先秦諸子的經歷,對我影響很大。有人替我抱怨,以為我在楚辭方面的成就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估,我則對此很釋然。先秦學術,特別是神話、傳說等方面的問題,不易得到實證,因此常是眾說紛紜,難以取得共識。楚辭學界在理論領域中少見突破性的進展,與此有關。我在《九歌新考》中提出的一些新見,作為各家中的一說,僅供參考即可。
處在政治決定一切的年代,條件差的人本無可能選擇什么發展道路,一切都得服從組織安排。我在“大躍進”后轉入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領域,其后產生了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小史》,還產生了《王充與兩漢文風》、《〈文賦〉寫作年代新探》、《梁代文論三派述要》等論文,有了新的任務之后就得立即轉向。見縫插針,總算還留下了一些成果。現在看來,當時的準備工作做得仍嫌不夠,然而畢竟年輕,精力還是充沛一些,能夠進行一些較深入的思考。前此已經接受過一些思維方面的訓練,分析與歸納的能力尚能支配,從而取得了一些在批評史方面立足的資本。
“文化大革命”中奉命注釋法家著作,重新回到先秦學術上來,注意力集中到思想史方面。先秦諸子本難以現代學術歸類,于是我把哲學、歷史等方面的典籍又重新復習了一遍,在訓詁、校勘、版本等實學上又提高了一步。
在那一家獨尊的年代,郭沫若憑借其特殊身份,還能乘機拋出一本《李白與杜甫》,大家也就可以托他的福,讀讀唐代詩人的書了,于是我就轉入高適、李白、杜甫等人的研究,又寫下了《敘〈全唐詩〉成書經過》等論文,這也為后來的發展準備了一些條件。
改革開放之后,全國高校之間出現競爭態勢,我校中文系力量太弱,各方面都不占優勢,然自程千帆先生回母校工作建立博士點后,力量逐漸壯大。卞孝萱先生隨后加入,吾等也就確定以唐代文學為重點,展示我們的優勢。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千帆先生出任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學會同仁從工作考慮,讓我擔任學會副秘書長,那我就必須全力投入到這一領域中去。古委會成立,我出任古籍所所長,自當在此機構內多所活動。處在其他兄弟單位競上大項目的形勢下,至少也得有一個中型項目可以撐撐場面,于是我就提出了《唐人軼事匯編》這一能夠體現本所特色的項目。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國家財政困難,文科教師既無科研經費,本身收入又低,出門開一次會都捉襟見肘。幸虧古委會每年能有一兩萬塊錢的經費下來,才能支撐起這個攤子。于公于私,我都得在這個大集體中起些作用。因此,自古委會成立始,我在每一項重大活動中都曾努力貢獻力量。
古委會下來的錢,不能用于提高工作人員的生活水平,于是大家轉向創收,想盡辦法多發一些獎金。有的學校忙著辦班,有的學校忙著編通俗讀物,我作為一家之長,也得忙著張羅,于是接下了《冊府元龜》校訂本等任務,以為這樣做,可以做到業務提高和改善生活兩不誤。事后看來,效果還是不錯。這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參與整理的人在業務上都有提高,收入尚稱豐厚,對我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的聲譽也有所提高。
老師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學生,我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備課和教學上。那些一心只想通過科研提高個人聲譽的人,也不能算是合格的教師。這樣的人,盡管學生時而也會講上幾句好聽的話,目的可能也只是搭個順風車,利用“名師出高徒”的傳統觀念為自己加分,內心深處可未必尊師。這樣的師生關系,出于功利目的,一有波折,也就會分道揚鑣。
集體項目的負責人要有高度的責任感。一些超大型的著作,往往需要一批人去做基礎工作。他們窮年累月,從事一些簡單勞動,難于提高層次,結果總有一批人得不到正常發展。處在目前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有人若是趕不上步伐,往往慘遭淘汰。因此那些負責全局的人,不能只考慮自己的光環如何擴大,應該多為屬下著想,不但要幫他們在經濟上脫困,首要任務還是要幫他們求得正常發展,穩扎穩打,在學術界占個有利位置。這樣的大項目做來才有意義。既完成了任務,又培養了人材,這種項目才可算是取得成功。
時代不同了,學人所處的環境已有很大變化,像我這樣的一名小知識分子,出身不好,身體又差,思想跟不上形勢,時時處在肅殺的氣氛之內,僅因還有那么一點使用價值,才能做做文墨工作。這樣的角色,自然不能擔當大任,憑自己的興趣去求得發展,平時只能兢兢業業,不出岔子,自求多福。改革開放之后,多少能夠獨立自主了,但紛紜擾攘,也難以潛心向學。我想,目下已經不可能再出杜佑、鄭樵、馬端臨等一輩子搞一本大書的可能,也不能再有司馬光主持《資治通鑒》那樣的條件,我的情況更是如此。那些條件比我好的人,似乎也難以突破當前條件的限制。有些學界中人,口氣大,聲勢壯,搞的項目規模宏大,足以超邁前古,但能否編出像《通典》與《資治通鑒》那樣傳世之作,還是一個未知數。
不過話得說回來。處在當前情況下,作為一個單位的負責人,完全不去考慮項目,爭取科研經費,看來也有困難。既然進也難,退又不能,那就得找一條可行之路,選一些確實有意義的項目來做。這種項目,不一定都要在通史、通論、集成、匯編等方面去考慮,思路可以放開一些。
我對從事《冊府元龜》校訂和《唐人軼事匯編》、《宋人軼事匯編》等項目的編纂抱有信心,確信這些工作都是有意義的,都是學術上的基本建設,本身也有學術價值。如果限于時間,限于條件,工作一時不能達到理想高度,還可再接再厲,再次加工。像《冊府元龜》這種項目,篇幅大,參加的人多,有的卷內問題尚有,我們還要再磨上幾年,訪求其他資料,不斷加工,重行修訂,力求完善。只要你的項目有價值,整理出來的書可以流傳,那就可以不斷重印,把自己發現與他人發現的問題一一改正過來。象《唐語林校證》,印了三四次以后問題也就大大減少,這可是超過前人的優勝之處。古人用木板刻書,重刻一次不易,那些編書的人大都為官作宦,一回官場,也就難以繼續。因此,我等自可利用目下有利條件,或編寫,或整理,心無旁鶩,留下幾本有用的書來。
在此我還可以介紹一下《全唐五代詩》這一項目的產生與我出任第一主編的前后經過。
回顧歷史,縱覽全局,可以發現,每一種有價值的著作的產生,都與其特定的時代背景有關。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可能產生于唐代或元代,吾等從事《全唐五代詩》的編纂,只能在中國步入改革開放之后。
自上一世紀八十年代起,唐代文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為了糾正前此學風空疏之弊,學界轉而重視文獻方面的建設。時至九十年代,唐詩學界的朋友發起了編纂一種《全唐五代詩》的計劃,并推舉我擔任第一主編。所以如此,當與其時在我身上集中了許多有利條件有關。如上所言,我一直在唐詩學界與古委會中活動,與各方面的朋友多所交往,與境外漢學界的朋友也多有聯系,可以匯集各方面的力量與資源。我本人也做過一些唐詩方面的研究,對《全唐詩》也有一定的認識與鉆研。或許大家認為我是辦事比較公道,認真負責,樂于與大家共享成果,能將這項事業完成的吧。而且我還具有另一方面的優勢,工作中如果發生了困難,那我校文學院古代文學專業與古籍所內的人員都會全力投入,這些都是能夠保證工作完成的強大后盾。
我在主持編寫《唐人軼事匯編》與編纂《唐語林校證》時,都附有詳細的人名索引;主持校訂《冊府元龜》時,后面也附人名索引,這些都對編寫《全唐五代詩》中的詩人小傳有幫助。我還做過唐人筆記小說方面的研究,熟悉詩人種種軼聞,這些都可在編纂《全唐五代詩》的工作中發揮作用。
不論從我個人的條件看,還是從外部條件看,如果結合二者而作綜合考察,我自應列為出任第一主編的首選人物。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唐代文學研究獨領風騷,只是“文革”之后國家元氣已傷,很難在古代文史的某一領域大筆投資,幸好在中央的支持下,財政部直接下撥一筆款子,支持古籍整理。古委會的全稱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屬教育部領導,前幾任秘書長,均由高教一司分管科研的章學新、陳志尚、夏自強等同志擔任。當時學界一片荒蕪,工作只能逐步鋪開,教育部先在下屬十八所高校內設點,分從教學與科研兩方面著手培養人材。《全唐五代詩》的兩個工作點,蘇州大學和河南大學都無直屬古委會的古籍所,不能申請大型項目。二校唐詩研究室開展工作,無法解決經費問題,于是唐詩學界內的朋友推舉我出來任職,提出申請,也是勢所必然。這樣,《全唐五代詩》的情況就很特殊,與《全宋詩》、《全明詩》等不同,工作單位并不設在南京大學古籍所內。之前我也參加過兩校的一些會議,河南大學一直想在李嘉言提出的方案上開展工作,蘇州大學方面則計劃利用當時條件,新編一部總集。我對二校工作都曾提出過建議,但從不想介入具體事務。身為南京大學古代文學的學科帶頭人,教學、科研、社會活動、對外交流本已不堪重負,無法再外加什么重大任務,只是朋友們讓我設法籌款,于情于理,不應推托。畢竟我在古委會內工作了十年左右,主任周林對我已有了解,評審組內成員對我的情況也深有所知,都表示積極支持,工作才能上馬。此等大事,首先要得到古委會周林主任的首肯,其時他本不想再增加“全”字號的大項目,打算在原有項目有了經驗之后再行發展,但他認為我辦事可靠,唐詩又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部分,項目具有重大意義,也就改變了原先的想法,支持我出任第一主編,作為古籍整理工作中另一種方式的試點工程。
但他們仍照原先的規章制度辦事,認準我的南京大學古籍所所長身份,一切公文都先發給我。參加《全唐五代詩》的一些單位和人員,用了多少錢,都有完整記錄,可以迅速查出各處經費的下達情況。這筆經費,決定《全唐五代詩》能否啟動,能否開展。
《全唐五代詩》于1992年正式立項,申請表內明言,我負責統籌全局,并協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開始,大家想得比較簡單,以為彼此認識已有多年,事情好辦,然而后來的情況并非如此。現在的人,在社會上立足,面臨錯綜復雜的各種關系,比之前時,要艱難得多。參加有影響的重大項目,與人交往時所展示的身份,會牽涉到各種利益。個人在項目中活動,在任職的校內也會有其作用,顯示學術地位。因此,參加集體項目的人,自然會關注自己的身份與利益。有的人強調自己的貢獻大,但對他人的貢獻估計不足,甚或漠視;有些人強調自己學校的貢獻大,但對別的學校的貢獻估計不足,甚或敵視;有些人聲稱要為學校爭取榮譽,實際上只是想提高個人在學校中的地位。各人考慮問題的角度不同,情況越來越復雜,工作之初想不到后來的結果,項目初現成效時各種矛盾也就漸次暴露。盡管工作仍在蜿蜒曲折地前進,到了后期,也就出現了舉步維艱之勢。
我一直秉承古委會的宗旨辦事。周林主任囑咐我團結各路人馬,我就促進蘇州大學與河南大學聯合。承擔項目的各界人員發生問題時,我得一一協調解決。截至世紀之交,打個長途電話都有困難,至今我的柜子里還保留著來來往往的幾十封信件。
我接手這項工程的有利條件也很多。古委會的堅決支持,主編會議中的主要成員——傅璇琮、郁賢皓等幾位老同志齊心協力,始終以事業為重,珍惜彼此數十年的情誼,終于攜手沖出各種困境。絕大多數的作者都與我們持同一立場,立即簽署了授權出版合同,冷對那些非法扣押其成果的昔日“朋友”。
蘇州大學唐詩研究室與河南大學唐詩研究室分別完成了各自承擔的任務,古委會建議,初盛唐部分的收尾工作,中晚唐部分的完成,改由南京大學古籍所內人員來承擔。我校文學院古代文學與古典文獻專業的人員隨即接下了這一任務,盡管他們教學與科研上負擔都很重,但還是不計私利,不計報酬,以國家事業為重,全力投入了這項新的工作。
這時我又經歷了一次思想轉變。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我不想搞大項目,考慮的是留校的那些博士生和碩士生要有一個提高和鞏固階段,讓他們把學到的東西消化一下,將論文好好加工,達到公開出版的水平,然后順利進入學界。如今情況已有不同,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方面的年輕教師都已有一兩本書在手,他們嘗到了甜頭,正在向專家的道路上飛奔。我總覺得,為學不必太急于求成,應該趁年輕,多積累些知識,開闊眼界,樹立遠大目標。常言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則無所得。一個人如果取得了一些成績就沾沾自喜,則常是以小專家的身份結局,我之動員他們投入這一項目,即著眼于此。一個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不懂得版本、目錄、校勘等問題,古籍所內人員,不清楚唐詩方面的基礎知識,不能品味把玩,領略唐詩的妙處,都不能算是合格人材,將來也難有大的發展。而且通過集體項目的鍛煉,可以增加任職單位內的凝聚力,培育團隊精神。大家都可由此發現他人的長處,不致只看到自己的點滴成就而沾沾自喜。
我一直認為,為人處世,應先公后私,先集體后個人。在集體利益得到保證之后再來考慮個人利益。先要做好人,然后考慮做好學問,否則即使你能取得一些成績,在社會上博得一些聲譽,但不能得到大家內心的尊重,甚或引來一些負面的評論,那外面那些虛假的榮光又有什么意味?
中國人所說的家國情懷,就是要求擺正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單位就是我們的“家”,只有單位搞好了,才能求得個人的正常發展。如果過分強調個人利益,棄“家”不顧,甚至只想到用“家”來博取個人利益,那“家”里的人必然會對你側目而視。與此相同,如果過分強調本“家”的利益,侵害到了別“家”的利益,那也難以獲取“大家”的認可。即使一時靠這取得了一些好處,他人遲早也會覺察到此中問題而腹非,甚至譴責。
歲月匆匆,我已步入耄耋之年,歲月無多,但承擔的任務都得一一有所交待,這樣既無負于他人,也不負當年委我以重任的人。
人的一生,因緣湊合,往往有很多事先無法估計的情況出現。如果某些事情落到了你頭上,那就應當承擔起責任,盡力把任務完成,這樣才能對得起大家,也對得起自己。我知道,《全唐五代詩》中凝聚著多少專家學者的心血,現在既然承擔了這份責任,就得對歷史有個交待。處在目前情況下,要把大家團結起來凝聚成一股力量,很不容易,但我一定不負眾望,黽勉從事,與編寫人員中的絕大多數專家打成一片,與陜西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繼初盛唐卷之后,把中晚唐部分出齊出好,留下一種比較完善的總集,貢獻于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