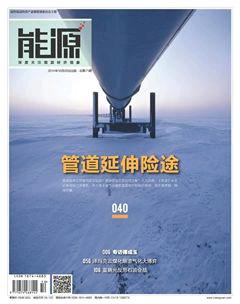排污收費與企業減排
林永生

當今世界,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胖”,居民錢包越來越“鼓”,但空中的煙霧卻越來越濃,2013年初開始進入公眾視線的十面“霾”伏,敲響了中國環境治理的警鐘。因此,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確保環境優先,制定實施環境經濟政策,促進企業減排,便成為當前各級政府關注的焦點,征收排污費就是其中一環。
排污費是我國于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實施并不斷改進的一項環境經濟政策,1982年國務院發布《征收排污費暫行辦法》,1996年《國務院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依據“排污費高于污染治理成本”的原則,進一步提高了排污收費標準,2014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和環境保護部聯合印發《關于調整排污費征收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省(區、市)結合實際,調整污水、廢氣主要污染物排污費征收標準,實行差別化排污收費政策,建立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促使企業主動治污減排,保護生態環境。
影響因素
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政策主要針對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旨在通過增加企業生產經營過程污染物排放成本影響企業決策,采取減產或對生產和治污設備進行升級改造,最終削減污染物排放量。但影響企業排污決策的因素很多,至少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排污成本影響企業排污決策。排污稅費問題最早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由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其外部性研究理論中提出,庇古認為要使環境成本內部化,就需要政府采取稅費或補貼的形式來對市場進行干預,使私人邊際成本與社會邊際成本相一致。通常而言,排污費征收標準越高,企業排污成本就越高,進而就會相應減少污染物排放。
二是產品供求彈性影響企業排污決策。產品供求彈性是指產品市場價格每變化一個百分點造成了幾個百分點的供給量、需求量變化,刻畫的是廠商和消費者對產品價格變化的敏感程度。產品供求彈性是制約稅負轉嫁形式及規模的關鍵因素,一部分稅負通過提價形式向前轉給消費者,一部分通過成本減少(或壓價)向后轉給原供應或生產要素者,究競轉嫁比例如何,根據供求彈性而定。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即便提高排污費,增加企業排污成本,但如果該企業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較小,也就是說,價格變化幅度很大但市場需求量變動很小,則該企業易于把排污費引致的生產成本增量轉嫁到產品價格中去,進而不能夠形成有效的減排約束和激勵。
三是違約成本影響企業排污決策。科學縝密的污染物排放監測體系和具有公信力的獎懲體系是影響企業排污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政府在研究制定政策過程中容易忽略企業違約的情況,即暗含假設企業都守約,人們逐漸認識到,企業并不總是遵守現存的規制。
效果有限
那么,中國的排污收費是否顯著降低了工業企業污染物的排放量呢?
下表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來,我國排污費征收總額持續增加,從2000年的58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01.6億元。過去13年間,我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的年度排放量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3186.2萬噸降到2012年的144.2萬噸。工業廢水排放量略有增加但基本穩定,2000年的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94.2萬噸,2012年增至221.6萬噸。但工業廢氣排放量仍快速增加,從2000年的13.8萬億立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63.6萬億立方米。
因此,總體來看,我國排污收費政策并沒有顯著降低工業企業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但需要肯定其積極作用,排污收費制度是“污染者付費”原則的體現,可以使污染防治責任與排污者的經濟利益直接掛鉤,促進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繳納排污費的排污企業會有一定壓力和動力去加強經營管理、革新技術與裝備,實現節能減排。
排污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專項用于環境保護,由縣區級及以上環保部門核定征收與管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國已經踐行30多年的排污費政策培養和鍛煉了一批人、探索與完善了一系列程序、制度與規范,為未來亟待推進實施的環境稅改革奠定了基礎,也為不同地區的污染治理籌措了部分資金,促進了環境保護。目前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全部開展了排污收費工作。2013年全國排污費征收開單216.05億元,比2012年增長10.73億元,增幅為5.2%;征收戶數為43.11萬戶,比2012年增加7.8萬戶,增幅為22.2%。
環境稅猜想
我國各界醞釀已久的環境稅征收方案至今仍未出臺,但有跡象表明,排污費改為環境稅不失為一種可能。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全面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深化財稅改革”專題中明確提出要“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2014年4月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三條指出,“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繳納排污費。排污費應當全部專項用于環境污染防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擠占或者挪作他用。依照法律規定征收環境保護稅的,不再征收排污費。”
無論是進一步完善當前的排污費政策,還是制定實施未來的環境稅方案,都要基于我國排污收費政策現存的問題進行優化和糾偏,大致可歸為三個方面:一是現行排污費主要對排污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征收,無法對主要污染物排放“貢獻”越來越大的生活源形成約束,進而表現為地區排污費征收水平和地區污染物排放總量之間難以找到顯著的負向相關關系,需要研究并適時擴大排污費的征收對象;二是現行排污費在征收種類、標準、額度等方面的規定過于單一、片面,主要依據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噪音等主要污染物類型及其相應污染物中的危險成分制定,沒有考慮到不同行業的污染物排放量、特別是其行業產品的供求彈性,從而無法給排污單位形成有效的減排約束和激勵;三是現行排污費規模仍然較小,在國家或地區層面,都不足以籌措到治理污染、改善生態環境所需的足夠資金。
2013年,我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為56.88萬億,工業增加值為21萬億,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6.28萬億元。然而2013年上繳的各種排污費加在一起只有216.05億,可以設想,如果環境稅由排污費轉化而來,那么216.05億的稅收如何承擔起6.28萬億工業企業利潤所帶來的環境污染。解決途徑要么從擴大征收對象和種類、提高標準等方面增加排污費或環境稅征收總額,要么在排污費之外大幅增加地方生態環境治理籌資渠道和財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