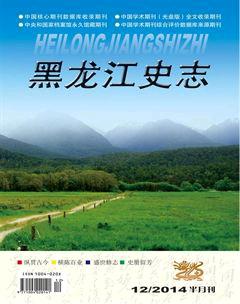關于鎮江花山灣古城建造年代問題的探究
陳昱文
[摘 要]關于花山灣古城,歷來爭議不斷。但根據歷代文獻的記載,結合1984年、1991年、2010年三次考古發掘的結果,可以大致理清這一地區城市發展的沿革。經過分析,推斷花山灣古城與“晉陵羅城”的稱謂無關,也非由郗鑒、王恭所筑,而是晚唐時期周寶所筑的羅城。這座城在北宋經過了加筑,南宋時已不見城垣。
[關鍵詞]花山灣古城;晉陵羅城;筑城年代
1984年,鎮江博物館在鎮江市區東北花山灣發現一座古代城址,1991年,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和鎮江博物館對城址進行勘探和發掘,兩次發掘主要集中在花山灣地區,發現了一些不連貫的城垣。在古城的始建年代上,存在著較大的爭議。鎮江考古所劉建國在發掘報告中將其定名為“晉陵羅城”(1),認為其始建年代為東晉。后韋正在《論六朝時期的鎮江古城》一文中,對“晉陵羅城”的說法予以質疑,但未提出自己的看法。《江蘇鎮江市花山灣古城址1991年發掘簡報》中,則認為該城是唐代潤州羅城,社科院的曲英杰先生在《長江古城址》一書中的結論也與此相同。此后,鎮江博物館又進行進一步發掘,發表《江蘇鎮江花山灣古城遺址2010年發掘簡報》,認為該城建成于唐代晚期,宋代進行加筑,至南宋時完全廢棄。
從文獻記載中,可以大致還原這一地區城市建設的沿革。較早關于在此筑城的記載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11年),“孫權徙鎮于此筑京城”(2)。晉室南渡后,東晉郗鑒“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之軍事(3)”,后王恭又有“更大改創(4)”。唐代在此置潤州,潤州城的地望也應在此地。又有,唐太和年間,觀察使王璠修東西夾城,在城周圍開隍。唐僖宗光啟三年(公元887年),鎮海節度使周寶“筑羅城二十余里(5)”。南唐林仁肇“復修之”。此后,府城數次加筑、重建,也多有廢棄,史籍均有可考。與花山灣古城建造者可能相關的,是東晉的郗鑒、王恭,以及唐晚期的王璠、周寶。
孫吳在此筑的城位于北固山,號鐵甕城,這一點應無疑義,歷代史書均有記載,如明代的李一陽在《府治后垣記》中寫道:“吳大帝筑子城,控扼南北,號曰鐵翁,規制宏壯。(6)”又《輿地志》載:“(鐵甕城)吳大帝孫權所筑,周迥六百三十步。(7)”但此后郗鑒的“城京口”,以及王恭的“更大改制”,是在鐵甕城的基礎上修繕,還是另建新城?根據文獻記載,郗鑒在京口筑城,是為了防御劉征率領的數千賊人從東南面海上的抄略,可能僅僅是對京口城防的加固,并無必要另建一座大城。從時間上看,這伙賊人不久便被討平,其間時間較短,根本不足以另筑新城。當時大量的北人南遷,被安置在晉陵附近,據估計約有二十萬眾(8)。對于流民,郗鑒抱有了極大的防備心理,這從他晚年的一封奏疏可以看出:“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處興田宅,漸得稍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9)”郗鑒常年坐鎮京口,既防北方的軍事侵襲,又有控制流民之用,而建造一座規模巨大的城,將南遷流民置于城中,似乎不是郗鑒之意愿。他曾對平南將軍溫嶠說:“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后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10)”郗鑒的軍事策略是“屯聚要害”、“堅壁清野”,花山灣地區地勢相對較平坦,而且面積廣大,無險可守,在此筑城并不符合郗鑒“屯聚要害”的“待賊”之法。無論從筑城的時間、目的,還是從郗鑒的方針策略來看,似乎都沒有建造花山灣古城的可能。歷代文獻中有關郗鑒、王恭筑城的記載,幾乎均是將其所筑的城看做是“鐵甕城”。元代《至順鎮江志》中載:“子城吳大帝所筑……晉郗鑒嘗修,王恭更大改創。(11)”此外,《太平寰宇記》引《京口記》中的“晉王恭為刺史,改創西南樓名為萬歲樓,西北樓為芙蓉樓”,根據調查以及名稱推斷,當時的萬歲樓在今千秋橋附近,位于今鼓樓崗西側。至此向北,其范圍大致與鐵甕城西垣相重合,這就說明,王恭的“改制”可能也僅僅是在鐵甕城的基礎上修繕和增筑城樓,并沒有另外起一座規模巨大的城池。
需要說明的是,“晉陵羅城”的定名,可能不適用于花山灣古城。東晉時,京口作為晉陵的郡治,僅僅是太興元年(公元317年)至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的十二年(12),具有臨時性,可能與邊防和控制流民有關,更多的時間里,晉陵的郡治被放在了丹徒和今天的常州一帶。再者,“晉陵羅城”的說法在東晉并不存在,《晉書》中,“晉陵”作為地名較為常見,而“晉陵羅城”的說法則無一次被提及。唐代恢復晉陵后,治所在今天的常州而非京口。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分天下十五道,江南東道潤為會府(13)”,此時,京口地區已屬潤州,與晉陵所屬的常州明顯分隔兩地。照此,花山灣古城既不可能是東晉的“晉陵羅城”,又不是唐代的晉陵,那么可以解釋的說法是,“晉陵羅城”的字樣,標明的是制磚人的籍貫。根據銘文磚上的字體、書寫格式等,斷定其與東晉城磚相異(14)。《江蘇鎮江市花山灣古城址1991年發掘簡報》以及其后的《江蘇鎮江花山灣古城遺址2010年發掘簡報》,均將“晉陵羅城”磚的年代斷為唐,應該與事實接近。
又,晉陵羅城遺址若為唐代潤州城,則與文獻記載存在抵牾。《唐書音訓》載:“京口,在潤州城東北,甘露寺側。(15)”據此可知,唐代的潤州城應在京口西部開闊地。南宋《嘉定鎮江志》載,“東山,在城東二里,亦號花山(16)”,可見,南宋時的府城應在鐵甕城及以西,花山地區已不存城池。如果文獻記載無誤,那么,花山灣古城既非唐代初置“潤州”時的潤州城,也不是南宋的府城,其建筑及使用的年代應該是唐中晚期至南宋。文獻中關于唐代筑城的記載,分別是太和年間(公元827—835年)王璠所筑的“東西夾城”和光啟三年(公元887年)鎮海節度使周寶所筑的羅城。關于羅城的形制,文獻中雖無詳細記錄,但對城門的名稱、位置則有較為詳細的記錄。《嘉定鎮江志》載,羅城“共十一門”,東有兩門,“北曰新開,南曰青陽(17)”。《至順鎮江志》中記載元時尚存的東門“青陽門”,“去府治二里(18)”,推測新開、青陽兩門應均應該距離府治有二里左右。又根據古子城北門在“府治后”,判斷元代的“府治”應在鐵甕城范圍內。2010年對花山灣地區的發掘,發現城門門址一座,從距離上來看,在1000米左右,與“二里”的記載相差不大,只有羅城東垣的兩座城門具有可能性,考古報告中亦將此門定為“新開門(20)”。由此推斷,花山灣古地區發現的城垣應為羅城,是為唐代晚期的周寶所修筑。endprint
關于羅城城垣的長度,文獻中多有記載,據《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引《城邑考》:“更筑羅城,周二十余里。(21)”南宋《嘉定鎮江志》記“羅城周回二十六里十七步(22)”,《至順鎮江志》也記郡城“二十六里十七步(23)”,可知羅城周長在二十里以上。根據考古發掘報告,花山灣古城的周長約為十里,與文獻記載的二十多里相差甚遠。可能的情況是,羅城的西部的城垣,疊壓在今天鎮江的市區之下,后代的府城即是在羅城西部城垣的基礎上加筑的。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宋禮在前代城墻上加砌磚石,城“九里十三步”,清人實測發現城周不是九里,而是十二里多。如以十二里多計算,則與花山灣古城合計二十多里,則與文獻所載接近。
從1984年的考古發掘資料看,西墻較其他三面城墻,出土了較多宋代的遺跡、遺物。如在西墻A、D段,發現了模印有“鎮江府城”、“府城磚”、“鎮江水軍”等字樣(24)。“鎮江”的稱謂,是在宋徽宗政和三年改潤州為鎮江府時才出現,所以這些城磚應是宋代或以后燒制,結合文化層分析,此應為宋代的城磚。以西墻C段為例,在此處開有探溝T2,發現五層文化堆積,其中第三層是夯土,包含大量宋代陶瓷、磚瓦,第四層也是夯土,出土夯窩、夯土間厚均與第三層相似。如果第三層中未發現有晚于宋代的遺物,那三、四層應為宋代的夯筑城墻無疑。由此推測,西墻與其他三墻可能并不建于同一時期。文獻記載羅城“二十六里十七步”,那么羅城在經南C段向西后,可能并不是彎折向北與西A段相連,而是在大學山南麓向西南彎折,進而圍合成一個大圈,將鐵甕城、后代的府城圍合在內。西墻疊壓下即使有唐代的夯土,也很有可能是王璠所建東夾城的西垣。宋代城磚及夯筑遺跡僅在西墻發現,北、東、南三墻在三次發掘報告中均未提及有出土,可能宋代府城沿用了部分唐代羅城、夾城的部分城墻加筑而成,花山灣地區的羅城則棄之不用
根據上述推論,可推測該地區城市發展的沿革是:三國時期,吳國建鐵甕城;東晉時郗鑒和王恭先后在鐵甕城的基礎上加筑;唐代建潤州城,子城位于鐵甕城處,并新建城垣,將子城圍合,但并未包含花山灣古城。后又建有東西夾城。唐晚期周寶建羅城,囊括了花山灣古城、鐵甕城、明清府城的范圍。宋代加筑城垣,但花山灣古城部分棄之不用,僅在鐵甕城及以西部分筑城。上述推斷,僅是根據文獻、考古資料以及前人的研究所作出的一種假設,揭開真正的事實,還需要對該地區進行更加細致、更大范圍的調查和發掘。
注釋:
(1)劉建國.晉陵羅城初探[J].《考古》.1986年第5期.
(2)(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O].卷二十五.
(3)房玄齡等.晉書·郗鑒傳[O].卷六七.中華書局.1974.
(4)(元)脫因修、俞希魯.至順鎮江志[O].卷二.中華書局.1990.
(5)司馬光.資治通鑒[O].卷二五六.中華書局.1956.
(6)(明)李一陽.府治后垣記.[O]
(7)(南朝)顧野王.輿地志[O]
(8)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后之民族遷徙[J].《燕京學報》,第15期。
(9)房玄齡.晉書·郗鑒傳[O].中華書局.1974.一七八〇頁.
(10)(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府志[O].卷二十.江蘇古籍.1999.第八六二頁。
(11)(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府志[O].卷二.江蘇古籍.1999.第九頁.
(12)韋正.試論六朝時期的鎮江古城[J].《東南文化》1993年6期.
(13)(南宋)盧憲.嘉定鎮江志·卷一[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二六頁.
(14)劉斌.鎮江“晉陵羅城”命名問題的探討[J].《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15)(清)張九征、何洯、程世英等.康熙鎮江府志[O].卷五十四.
(16)(南宋)盧憲.嘉定鎮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二頁.
(17)(南宋)盧憲.嘉定鎮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一頁.
(18)(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府志[O].卷二.江蘇古籍.1999.第八頁.
(20)鎮江博物館.江蘇鎮江花山灣古城遺址2010年發掘簡報[J].《江漢考古》.2012年第2期.
(21)(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O]卷二五引《城邑考》.
(22)(南宋)盧憲.嘉定鎮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第二八三二頁.
(23)(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府志[O].卷二.江蘇古籍.1999.第八頁.
(24)鎮江博物館.鎮江東晉晉陵羅城的調查和試掘[J].《考古》.1986年第5期.
(25)鎮江博物館.鎮江東晉晉陵羅城的調查和試掘[J].《考古》.1986年第5期.
參考文獻:
[1](南宋)盧憲.嘉定鎮江志[O].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
[2](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府志[O].江蘇古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