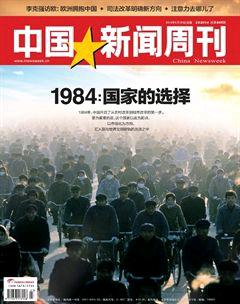中美應如何建立“新型大國關系”
何亞非
美國2009年宣布“轉向亞洲”,2011年公布“亞太再平衡”戰略,并據此采取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行動。這不僅造成中美關系再度緊張,還打破了地區戰略均衡,加劇了中國與部分鄰國的主權和海洋權益爭端,給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增添了新的復雜和不確定因素。
在上述情況下,并思考21世紀中美作為上升大國以及美國作為守成霸權應如何相處以避免歷史重演,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倡議,中美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這不僅著眼于雙邊關系,更具全球視野,以期走出一條新世紀大國和平相處之道。
“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新型大國關系”主張從根本上說,是兩國在整體戰略上的較量。
盡管中美存在不同的戰略利益取向,政策重點也有分歧,但中美建交35年雙方始終有個共識:即中美在全球化背景下,兩國利益深度融合、相互依賴,結成合作伙伴關系。
中美作為全球大國,共同利益大于分歧,需要培養和鼓勵自我克制、相互理解的戰略文化,為增進雙方互信、構建健康穩定的新型大國關系提供必不可少的戰略文化氛圍和思維方式。美前副國務卿斯坦伯格曾提出中美平行采取戰略再保證措施,來逐步培育互信。其觀點得到不少中美學者的贊同。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中,如何增強戰略互信將是至關重要的。這種互信不僅包含增加信心、信任和信賴多重內涵,更強調行動的累積。所謂累積就是雙方需要不斷地“平行”而不是相互對抗為前提、以“零和”思維采取實際行動,來顯示愿意走互信和合作的道路。
中美有分歧,甚至有重大分歧是常態,管控分歧和危機、培育互信應該成為常態化行動。要學會“把分歧裝進箱子”,不影響大局,并開展持續有效的“戰略再保證”性互動,來培育正能量,抵消分歧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核心是雙方確保尊重對方的“底線”或者核心利益,采取措施讓對方“放心”自己的戰略意圖,追求一家利益最大化是不可取的。
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增加戰略互信,并據此采取相應的行動,還可以向國際社會作戰略宣示: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美國歡迎中國發展和壯大,也愿意和平競爭;雙方無意建立在世界和亞太分割勢力范圍的G2,而將在重大問題上加強磋商與合作,努力推動形成均衡、合理、公正的國際和地區格局;構建有助于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安全”/排他安全的地區軍事安全架構;致力加強雙邊分歧管控,強化危機管理能力。
中國領導人去年在倡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基礎上,提出與周邊國家共同建設“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目的就是為地區和平與發展、建立新的區域治理機制與體系作謀劃,做頂層設計。
中國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銀行是其中一項措施,將對亞洲國家共同發展、共享中國發展紅利做出貢獻。
亞洲很特殊,其開放性、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哪一家說了也不算。一兩個大國或大國集團不可能解決亞洲的問題,亞洲治理需要“亞洲精神”,那就是地區國家團結合作,開放包容,和平相處,共同創造“亞洲奇跡”。
從國際關系角度看,大國關系是關于國際秩序的。在國際關系中,世界無序狀態是常態。正因為是無政府狀態,戰爭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大國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都是傳統的觀念,需要改變,國際關系理論也需要調整。
這些年全球化快速發展、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加深,世界變小了。這些全球治理的努力是各國希望在無序狀態上,建立某種“秩序”,以避免人類陷入戰爭和危機不斷發送的惡性循環。
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種種現象表明,現存國際秩序出現了問題。如何建設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建立大家都認可的全球治理機制和體系,是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
總結起來說,“建設新型大國關系”其實不復雜,它是中國繼“韜光養晦”政策和“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政策后提出的重要理論概念。三者的核心一致:中國要做新型大國,打破“大國爭霸”邏輯,在實現自身和平崛起中,維持世界和平。當然,中國能否建設“新型大國關系”中國說了不算,還取決于其他大國。“新型大國關系”必須在大國互動中逐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