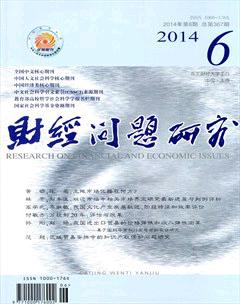征稅抑或補(bǔ)貼
付春香
摘要:在社會轉(zhuǎn)型的結(jié)構(gòu)性張力作用下,低收入群體的規(guī)模還在不斷遞增。我國現(xiàn)行的直接補(bǔ)貼式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促進(jìn)社會公平和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的同時,也暴露出重生存、輕發(fā)展,重形式、輕實(shí)質(zhì),高成本、低效率等問題。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將對象由少數(shù)人變?yōu)槿采w,由被動的接受補(bǔ)貼轉(zhuǎn)換為主動的享有“負(fù)納稅”權(quán)利,體現(xiàn)出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
關(guān)鍵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負(fù)所得稅;福利依賴;制度效應(yīng)
中圖分類號:F812.44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6-0011-05
從1992年山西省左云縣率先進(jìn)行農(nóng)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稱低保制度)試點(diǎn)開始,至今,我國的低保制度實(shí)施已二十余年。截止2011年9月底,全國共有3 744萬戶和7 535萬人城鄉(xiāng)低保對象,城鄉(xiāng)低保人均支出水平分別達(dá)到208元和86元。
在這期間,低保制度的覆蓋面不斷擴(kuò)大,支出水平不斷提高,管理效率不斷提升,極大地促進(jìn)了社會公平,維護(hù)了社會穩(wěn)定。但是,隨著社會轉(zhuǎn)型的加劇,現(xiàn)行的低保制度也暴露出高成本、低效率,重生存、輕能力等問題。因此,我們應(yīng)對現(xiàn)行的低保制度進(jìn)行反思,對其進(jìn)行重構(gòu)。
一、現(xiàn)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國外實(shí)踐表明,人均GDP超過3 000美元后,社會貧富差距將進(jìn)一步擴(kuò)大。2008年,我國的人均GDP已超過3 000美元,2010年已超過4 000美元,進(jìn)入經(jīng)濟(jì)社會矛盾凸顯時期[1],各種經(jīng)濟(jì)社會問題交織,這種形勢必然要求低保制度在調(diào)節(jié)貧富差距和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方面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克拉克認(rèn)為,在各個要求獲得應(yīng)得權(quán)利的人中間分配財富是一個重要的經(jīng)濟(jì)社會問題
[2]。然而,現(xiàn)行的補(bǔ)貼式低保制度無論是在財富的再分配還是在經(jīng)濟(jì)效率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
1.補(bǔ)貼地區(qū)差距、城鄉(xiāng)差距過大,難以體現(xiàn)制度的公平性
我國低保制度的實(shí)施,長期執(zhí)行中央和地方共擔(dān)的機(jī)制,表現(xiàn)為越是發(fā)達(dá)的地區(qū)支付越高的馬太效應(yīng)。如2011年9月城市低保人均支出水平,北京市朝陽區(qū)為每月515元,而云南省永勝縣為117元,前者為后者的4.4倍。2011年9月農(nóng)村低保人均支出,浙江省江干區(qū)為455元,河南省尉氏縣僅有14元,前者為后者的32.5倍。全國城市低保2010年人均每月為189元,而農(nóng)村則為74元,前者為后者的2.6倍。
數(shù)據(jù)來源: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tjsj。低保支出的區(qū)域差異和城鄉(xiāng)分割影響了制度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2.支出水平過低,生活無保障,難以讓居民有尊嚴(yán)地生活
政府兜底式的低保金能夠提供居民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基礎(chǔ),但僅達(dá)到“餓不死人”的目的,不利于居民的脫貧和發(fā)展。2010年,全國城市低保平均標(biāo)準(zhǔn)3 012元/人年,占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76%,全國農(nóng)村低保平均標(biāo)準(zhǔn)1 404元/人年,占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3.72%,各級財政共支出低保資金969.7億元,僅占GDP的0.25%,占財政支出的1.80%。這么少的投入,很難真正解決貧困居民的實(shí)際困難,更不用說讓居民有尊嚴(yán)地生活。
3.直接補(bǔ)貼容易養(yǎng)“懶人”,形成“福利依賴”,降低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jì)效率
一些低保對象得到補(bǔ)貼,解決饑餓問題后,如果有工作機(jī)會,由于收入比較少而選擇寧愿放棄,從而表現(xiàn)為典型的“福利依賴”。從表1可以看出,2007—2010年,城市低保對象中失業(yè)人員的比重在40%左右,低保金的領(lǐng)取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就業(yè)率,導(dǎo)致社會活力和效率的下降。美國1995年進(jìn)行的兩次民意調(diào)查表明,大約有70%的人認(rèn)為“人們會通過長期依賴和不盡全力擺脫等方式濫用這一福利”。因此,大多數(shù)發(fā)達(dá)國家都以發(fā)展式的補(bǔ)救型保障代替補(bǔ)貼式的“全民保障”。
4.低保管理的“身份化”和低效,容易出現(xiàn)勝者全得現(xiàn)象,形成新的分配不公
我國的低保制度在執(zhí)行中以家計(jì)調(diào)查為基礎(chǔ),以“費(fèi)”的形式支付,不但耗費(fèi)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執(zhí)行成本提高,而且在實(shí)踐中由于技術(shù)、管理等因素,造成執(zhí)行偏差。同時,我國目前的醫(yī)療、教育和住房等專項(xiàng)救助大多與低保戶相關(guān),一旦擁有低保戶的身份,就可以享有更多的其他社會救助,出現(xiàn)勝者全得現(xiàn)象。而低保邊緣戶因沒有低保戶的身份,既無法享受低保待遇,也很少享有其他社會救助,導(dǎo)致其生活狀況甚至不如低保戶,從而形成新的分配不公。
綜上所述,現(xiàn)行的低保制度難以體現(xiàn)公平性和有效性,制度的隨意性比較強(qiáng),人為操作機(jī)會大,容易造成分配文化的頹廢。羅爾斯認(rèn)為,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jī)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chǔ),都應(yīng)被平等分配[3]。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zhuǎn)型的關(guān)鍵時期,多種制度尚在完善當(dāng)中,貧困人口眾多,財力短缺。因此,應(yīng)重構(gòu)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其發(fā)揮更加有效的作用。
二、稅收視角下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構(gòu)
Friedman首次提出了負(fù)所得稅制,用以代替現(xiàn)行的對低收入者補(bǔ)助制度[4]。米爾利斯等在假定政府目標(biāo)是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條件下,得出了政府應(yīng)當(dāng)給予低收入者補(bǔ)助的結(jié)論。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將對象由少數(shù)人變?yōu)槿采w,由被動的接受補(bǔ)貼轉(zhuǎn)換為主動的享有“負(fù)納稅”權(quán)利,體現(xiàn)出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因此,與其向低收入群體發(fā)放補(bǔ)貼,還不如向低收入群體“征稅”。
1.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征稅式低保制度構(gòu)建
(1)確定征稅對象。
將征稅對象擴(kuò)展為所有居民,將現(xiàn)行的個人所得稅累進(jìn)稅率結(jié)構(gòu)進(jìn)一步擴(kuò)展到低收入群體,以“稅”的形式來代替現(xiàn)行的補(bǔ)貼式低保。
(2)確定最低收入標(biāo)準(zhǔn)。
本文將目前我國人均工資、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和最低生活保障標(biāo)準(zhǔn)等因素綜合考慮,確定最低收入標(biāo)準(zhǔn)平均為400元/月,各省可以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調(diào)整最低收入標(biāo)準(zhǔn)。對收入低于標(biāo)準(zhǔn)的人提供負(fù)所得稅補(bǔ)助,收入高于標(biāo)準(zhǔn)時,按個人所得稅法正常納稅。
(3)確定稅率。
稅率越低,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越高,其激勵性越強(qiáng)。稅率越高,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越少,收入越趨向平均,稅率為100%時,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為0。在設(shè)計(jì)時,稅率根據(jù)具體的政策目標(biāo)而定。負(fù)所得稅計(jì)算公式為:
從圖3可以看出,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在轉(zhuǎn)折點(diǎn)內(nèi)時,由于引入負(fù)所得稅計(jì)劃,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時,預(yù)算約束線在右移的過程中,斜率變?yōu)?[g(1-t)],與轉(zhuǎn)折收入點(diǎn)對應(yīng)的直線CF相交于M點(diǎn),從而形成新的預(yù)算線GM。低收入者在獲得政府的負(fù)所得稅后達(dá)到了一個更高的無差異曲線U4,GM與U4 相切形成新的均衡點(diǎn)E4[7]。
第三,當(dāng)個人收入在收入轉(zhuǎn)折點(diǎn)和起征點(diǎn)之間。
根據(jù)筆者前面的設(shè)計(jì),此時個人既得不到負(fù)所得稅補(bǔ)貼也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時,可支配收入M和工資收入Y一致:M=Y=gL=g(W-S),從圖3看出,新的預(yù)算線變?yōu)镸N,斜率和預(yù)算線CD、PN斜率一致。也就是說,當(dāng)納稅人的收入超過轉(zhuǎn)折點(diǎn)后,征稅和直接補(bǔ)貼效用是一致的。當(dāng)個人收入超過起征點(diǎn)時,就應(yīng)繳納個人所得稅。
(3)兩種極端情況。
一種是極端偏好收入,這類人的無差異曲線特別平緩,不管工資率多少,他都會用全部時間工作,也就是所謂的“工作狂”,這類人的閑暇需求為0,勞動供給為W;一種是極端偏好閑暇,這類人的無差異曲線特別陡峭,不管工資率多少,他都會將時間用于閑暇,也就是所謂的“懶人”。這兩類人的均衡解都是角點(diǎn)解。這兩類人不具有代表性,現(xiàn)實(shí)中很少,在設(shè)計(jì)制度時,暫時不予考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從效用和公平來看,U4>U3>U2,征稅優(yōu)于直接補(bǔ)貼,直接補(bǔ)貼優(yōu)于既不補(bǔ)貼,又不征稅;從經(jīng)濟(jì)效率看,征稅也明顯優(yōu)于直接補(bǔ)貼。當(dāng)然,既不補(bǔ)貼,又不征稅的自由狀態(tài)經(jīng)濟(jì)效率是最高的,但忽略了公平。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奧肯認(rèn)為公平與效率兩者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兼顧兩者,就必須協(xié)調(diào)兩者的沖突。社會的經(jīng)濟(jì)效率主要是由高收入者決定,社會穩(wěn)定和公平則主要由低收人者決定,整個社會的運(yùn)行是否有效,是由二者共同決定的[8]。綜合來看,以負(fù)所得稅為基礎(chǔ)的低保制度在平等公平基礎(chǔ)上,兼顧了經(jīng)濟(jì)效率和社會活力,從而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
(二)征稅式低保制度的行政效率分析
本文重新構(gòu)建了城鄉(xiāng)一體、地區(qū)一致的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縮小了低保的地區(qū)差距和城鄉(xiāng)差距,而稅收的無償性和固定性也使對低保對象的管理“去身份化”,實(shí)現(xiàn)了動態(tài)優(yōu)化管理,體現(xiàn)了制度的公平性。由于負(fù)所得稅可以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稅收征管力量和征管網(wǎng)絡(luò),不需要單獨(dú)設(shè)立機(jī)構(gòu)和配置人員,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當(dāng)然,我國目前的征管技術(shù)可能與負(fù)所得稅制的要求有一定的距離,需要利用信息技術(shù)提高征管水平,大力提升稅務(wù)管理人員的素質(zhì)和能力等,而這些措施可能會提高稅務(wù)的行政成本,但這不是負(fù)所得稅制帶來的成本增加,而是稅制本身的成本。
2.征稅式低保制度的文化效應(yīng)分析
任何一種救助制度除了有形的錢物流動外,還滲透著提供者、管理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和價值觀。這些無形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僅影響制度的執(zhí)行,也制約著制度預(yù)期功能的實(shí)現(xiàn)。美國社會心理學(xué)家邁爾斯認(rèn)為,態(tài)度—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態(tài)度會影響行為,行為反過來也會影響態(tài)度[9]。
征稅式低保制度使低保對象的角色發(fā)生變化,賦予了低保對象一個統(tǒng)一的新身份:納稅人。將這部分人由有失尊嚴(yán)的被補(bǔ)貼者轉(zhuǎn)變?yōu)楣鈽s的納稅人,有尊嚴(yán)地獲得負(fù)所得稅,在收入高的時候,履行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wù);在收入低時,行使獲得負(fù)所得稅的納稅權(quán)利。既可以給,也可以取,權(quán)責(zé)對等,有利于全社會稅收文化和分配文化的重塑,使低保對象的可支配收入與自身的工作和努力掛鉤,提高了工作積極性,讓納稅人既關(guān)注生存問題,更注重能力和發(fā)展機(jī)會,從而降低了“福利依賴”水平。貧困文化理論認(rèn)為,要消滅貧困就必須改變貧困人員的文化價值觀,提高其素質(zhì)和能力。所以,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組織在救助的同時,有責(zé)任加大對低收入者的能力培訓(xùn)和文化培訓(xùn)力度,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jī)會,讓這部分人能夠自食其力地自我發(fā)展。
四、結(jié)論
給低收入者適度的保障,是促進(jìn)社會公平和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要求。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與直接補(bǔ)貼式的低保制度相比,具有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當(dāng)然,無論是以家計(jì)調(diào)查為基礎(chǔ)的補(bǔ)貼式低保制度,還是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要及時準(zhǔn)確地確定低保對象的收入都是一個難點(diǎn),因此,要重構(gòu)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就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居民收支信息庫,加快低保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采用動態(tài)的綜合管理信息系統(tǒng),加大與財政、稅務(wù)、銀行、房管和公安等部門配合的力度,從而保證新制度綜合地、系統(tǒng)地、有效地推行。
參考文獻(xiàn):
[1]喬俊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公共政策因應(yīng):韓國做法及啟示[J].改革,2011,(8):90-91.
[2]約翰·貝茨·克拉克.財富的分配[M].邵大海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1.
[3]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中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8.5.
[4]Friedman,M.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5]鄭功成.社會保障與弱勢群體保護(hù)[DB/OL].中國網(wǎng),2003-01-20.
[6]陸銘.勞動和人力資源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7.82-89.
[7]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研究基金會,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研究會聯(lián)合專家組.收入分配與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2005.61-63.
[8]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權(quán)衡[M].王忠民,黃清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81-83.
[9]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xué)[M].張智勇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110.
(責(zé)任編輯:劉艷)
(3)確定稅率。
稅率越低,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越高,其激勵性越強(qiáng)。稅率越高,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越少,收入越趨向平均,稅率為100%時,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為0。在設(shè)計(jì)時,稅率根據(jù)具體的政策目標(biāo)而定。負(fù)所得稅計(jì)算公式為:
從圖3可以看出,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在轉(zhuǎn)折點(diǎn)內(nèi)時,由于引入負(fù)所得稅計(jì)劃,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時,預(yù)算約束線在右移的過程中,斜率變?yōu)?[g(1-t)],與轉(zhuǎn)折收入點(diǎn)對應(yīng)的直線CF相交于M點(diǎn),從而形成新的預(yù)算線GM。低收入者在獲得政府的負(fù)所得稅后達(dá)到了一個更高的無差異曲線U4,GM與U4 相切形成新的均衡點(diǎn)E4[7]。
第三,當(dāng)個人收入在收入轉(zhuǎn)折點(diǎn)和起征點(diǎn)之間。
根據(jù)筆者前面的設(shè)計(jì),此時個人既得不到負(fù)所得稅補(bǔ)貼也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時,可支配收入M和工資收入Y一致:M=Y=gL=g(W-S),從圖3看出,新的預(yù)算線變?yōu)镸N,斜率和預(yù)算線CD、PN斜率一致。也就是說,當(dāng)納稅人的收入超過轉(zhuǎn)折點(diǎn)后,征稅和直接補(bǔ)貼效用是一致的。當(dāng)個人收入超過起征點(diǎn)時,就應(yīng)繳納個人所得稅。
(3)兩種極端情況。
一種是極端偏好收入,這類人的無差異曲線特別平緩,不管工資率多少,他都會用全部時間工作,也就是所謂的“工作狂”,這類人的閑暇需求為0,勞動供給為W;一種是極端偏好閑暇,這類人的無差異曲線特別陡峭,不管工資率多少,他都會將時間用于閑暇,也就是所謂的“懶人”。這兩類人的均衡解都是角點(diǎn)解。這兩類人不具有代表性,現(xiàn)實(shí)中很少,在設(shè)計(jì)制度時,暫時不予考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從效用和公平來看,U4>U3>U2,征稅優(yōu)于直接補(bǔ)貼,直接補(bǔ)貼優(yōu)于既不補(bǔ)貼,又不征稅;從經(jīng)濟(jì)效率看,征稅也明顯優(yōu)于直接補(bǔ)貼。當(dāng)然,既不補(bǔ)貼,又不征稅的自由狀態(tài)經(jīng)濟(jì)效率是最高的,但忽略了公平。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奧肯認(rèn)為公平與效率兩者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兼顧兩者,就必須協(xié)調(diào)兩者的沖突。社會的經(jīng)濟(jì)效率主要是由高收入者決定,社會穩(wěn)定和公平則主要由低收人者決定,整個社會的運(yùn)行是否有效,是由二者共同決定的[8]。綜合來看,以負(fù)所得稅為基礎(chǔ)的低保制度在平等公平基礎(chǔ)上,兼顧了經(jīng)濟(jì)效率和社會活力,從而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
(二)征稅式低保制度的行政效率分析
本文重新構(gòu)建了城鄉(xiāng)一體、地區(qū)一致的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縮小了低保的地區(qū)差距和城鄉(xiāng)差距,而稅收的無償性和固定性也使對低保對象的管理“去身份化”,實(shí)現(xiàn)了動態(tài)優(yōu)化管理,體現(xiàn)了制度的公平性。由于負(fù)所得稅可以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稅收征管力量和征管網(wǎng)絡(luò),不需要單獨(dú)設(shè)立機(jī)構(gòu)和配置人員,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當(dāng)然,我國目前的征管技術(shù)可能與負(fù)所得稅制的要求有一定的距離,需要利用信息技術(shù)提高征管水平,大力提升稅務(wù)管理人員的素質(zhì)和能力等,而這些措施可能會提高稅務(wù)的行政成本,但這不是負(fù)所得稅制帶來的成本增加,而是稅制本身的成本。
2.征稅式低保制度的文化效應(yīng)分析
任何一種救助制度除了有形的錢物流動外,還滲透著提供者、管理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和價值觀。這些無形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僅影響制度的執(zhí)行,也制約著制度預(yù)期功能的實(shí)現(xiàn)。美國社會心理學(xué)家邁爾斯認(rèn)為,態(tài)度—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態(tài)度會影響行為,行為反過來也會影響態(tài)度[9]。
征稅式低保制度使低保對象的角色發(fā)生變化,賦予了低保對象一個統(tǒng)一的新身份:納稅人。將這部分人由有失尊嚴(yán)的被補(bǔ)貼者轉(zhuǎn)變?yōu)楣鈽s的納稅人,有尊嚴(yán)地獲得負(fù)所得稅,在收入高的時候,履行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wù);在收入低時,行使獲得負(fù)所得稅的納稅權(quán)利。既可以給,也可以取,權(quán)責(zé)對等,有利于全社會稅收文化和分配文化的重塑,使低保對象的可支配收入與自身的工作和努力掛鉤,提高了工作積極性,讓納稅人既關(guān)注生存問題,更注重能力和發(fā)展機(jī)會,從而降低了“福利依賴”水平。貧困文化理論認(rèn)為,要消滅貧困就必須改變貧困人員的文化價值觀,提高其素質(zhì)和能力。所以,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組織在救助的同時,有責(zé)任加大對低收入者的能力培訓(xùn)和文化培訓(xùn)力度,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jī)會,讓這部分人能夠自食其力地自我發(fā)展。
四、結(jié)論
給低收入者適度的保障,是促進(jìn)社會公平和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要求。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與直接補(bǔ)貼式的低保制度相比,具有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當(dāng)然,無論是以家計(jì)調(diào)查為基礎(chǔ)的補(bǔ)貼式低保制度,還是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要及時準(zhǔn)確地確定低保對象的收入都是一個難點(diǎn),因此,要重構(gòu)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就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居民收支信息庫,加快低保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采用動態(tài)的綜合管理信息系統(tǒng),加大與財政、稅務(wù)、銀行、房管和公安等部門配合的力度,從而保證新制度綜合地、系統(tǒng)地、有效地推行。
參考文獻(xiàn):
[1]喬俊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公共政策因應(yīng):韓國做法及啟示[J].改革,2011,(8):90-91.
[2]約翰·貝茨·克拉克.財富的分配[M].邵大海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1.
[3]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中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8.5.
[4]Friedman,M.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5]鄭功成.社會保障與弱勢群體保護(hù)[DB/OL].中國網(wǎng),2003-01-20.
[6]陸銘.勞動和人力資源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7.82-89.
[7]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研究基金會,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研究會聯(lián)合專家組.收入分配與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2005.61-63.
[8]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權(quán)衡[M].王忠民,黃清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81-83.
[9]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xué)[M].張智勇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110.
(責(zé)任編輯:劉艷)
(3)確定稅率。
稅率越低,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越高,其激勵性越強(qiáng)。稅率越高,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越少,收入越趨向平均,稅率為100%時,納稅人獲得的負(fù)所得稅補(bǔ)貼為0。在設(shè)計(jì)時,稅率根據(jù)具體的政策目標(biāo)而定。負(fù)所得稅計(jì)算公式為:
從圖3可以看出,低收入者的工資收入在轉(zhuǎn)折點(diǎn)內(nèi)時,由于引入負(fù)所得稅計(jì)劃,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大大提高的同時,預(yù)算約束線在右移的過程中,斜率變?yōu)?[g(1-t)],與轉(zhuǎn)折收入點(diǎn)對應(yīng)的直線CF相交于M點(diǎn),從而形成新的預(yù)算線GM。低收入者在獲得政府的負(fù)所得稅后達(dá)到了一個更高的無差異曲線U4,GM與U4 相切形成新的均衡點(diǎn)E4[7]。
第三,當(dāng)個人收入在收入轉(zhuǎn)折點(diǎn)和起征點(diǎn)之間。
根據(jù)筆者前面的設(shè)計(jì),此時個人既得不到負(fù)所得稅補(bǔ)貼也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時,可支配收入M和工資收入Y一致:M=Y=gL=g(W-S),從圖3看出,新的預(yù)算線變?yōu)镸N,斜率和預(yù)算線CD、PN斜率一致。也就是說,當(dāng)納稅人的收入超過轉(zhuǎn)折點(diǎn)后,征稅和直接補(bǔ)貼效用是一致的。當(dāng)個人收入超過起征點(diǎn)時,就應(yīng)繳納個人所得稅。
(3)兩種極端情況。
一種是極端偏好收入,這類人的無差異曲線特別平緩,不管工資率多少,他都會用全部時間工作,也就是所謂的“工作狂”,這類人的閑暇需求為0,勞動供給為W;一種是極端偏好閑暇,這類人的無差異曲線特別陡峭,不管工資率多少,他都會將時間用于閑暇,也就是所謂的“懶人”。這兩類人的均衡解都是角點(diǎn)解。這兩類人不具有代表性,現(xiàn)實(shí)中很少,在設(shè)計(jì)制度時,暫時不予考慮。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從效用和公平來看,U4>U3>U2,征稅優(yōu)于直接補(bǔ)貼,直接補(bǔ)貼優(yōu)于既不補(bǔ)貼,又不征稅;從經(jīng)濟(jì)效率看,征稅也明顯優(yōu)于直接補(bǔ)貼。當(dāng)然,既不補(bǔ)貼,又不征稅的自由狀態(tài)經(jīng)濟(jì)效率是最高的,但忽略了公平。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奧肯認(rèn)為公平與效率兩者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兼顧兩者,就必須協(xié)調(diào)兩者的沖突。社會的經(jīng)濟(jì)效率主要是由高收入者決定,社會穩(wěn)定和公平則主要由低收人者決定,整個社會的運(yùn)行是否有效,是由二者共同決定的[8]。綜合來看,以負(fù)所得稅為基礎(chǔ)的低保制度在平等公平基礎(chǔ)上,兼顧了經(jīng)濟(jì)效率和社會活力,從而使整個社會福利增加。
(二)征稅式低保制度的行政效率分析
本文重新構(gòu)建了城鄉(xiāng)一體、地區(qū)一致的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縮小了低保的地區(qū)差距和城鄉(xiāng)差距,而稅收的無償性和固定性也使對低保對象的管理“去身份化”,實(shí)現(xiàn)了動態(tài)優(yōu)化管理,體現(xiàn)了制度的公平性。由于負(fù)所得稅可以充分利用現(xiàn)有的稅收征管力量和征管網(wǎng)絡(luò),不需要單獨(dú)設(shè)立機(jī)構(gòu)和配置人員,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當(dāng)然,我國目前的征管技術(shù)可能與負(fù)所得稅制的要求有一定的距離,需要利用信息技術(shù)提高征管水平,大力提升稅務(wù)管理人員的素質(zhì)和能力等,而這些措施可能會提高稅務(wù)的行政成本,但這不是負(fù)所得稅制帶來的成本增加,而是稅制本身的成本。
2.征稅式低保制度的文化效應(yīng)分析
任何一種救助制度除了有形的錢物流動外,還滲透著提供者、管理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和價值觀。這些無形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僅影響制度的執(zhí)行,也制約著制度預(yù)期功能的實(shí)現(xiàn)。美國社會心理學(xué)家邁爾斯認(rèn)為,態(tài)度—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態(tài)度會影響行為,行為反過來也會影響態(tài)度[9]。
征稅式低保制度使低保對象的角色發(fā)生變化,賦予了低保對象一個統(tǒng)一的新身份:納稅人。將這部分人由有失尊嚴(yán)的被補(bǔ)貼者轉(zhuǎn)變?yōu)楣鈽s的納稅人,有尊嚴(yán)地獲得負(fù)所得稅,在收入高的時候,履行個人所得稅的納稅義務(wù);在收入低時,行使獲得負(fù)所得稅的納稅權(quán)利。既可以給,也可以取,權(quán)責(zé)對等,有利于全社會稅收文化和分配文化的重塑,使低保對象的可支配收入與自身的工作和努力掛鉤,提高了工作積極性,讓納稅人既關(guān)注生存問題,更注重能力和發(fā)展機(jī)會,從而降低了“福利依賴”水平。貧困文化理論認(rèn)為,要消滅貧困就必須改變貧困人員的文化價值觀,提高其素質(zhì)和能力。所以,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組織在救助的同時,有責(zé)任加大對低收入者的能力培訓(xùn)和文化培訓(xùn)力度,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jī)會,讓這部分人能夠自食其力地自我發(fā)展。
四、結(jié)論
給低收入者適度的保障,是促進(jìn)社會公平和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要求。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與直接補(bǔ)貼式的低保制度相比,具有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當(dāng)然,無論是以家計(jì)調(diào)查為基礎(chǔ)的補(bǔ)貼式低保制度,還是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要及時準(zhǔn)確地確定低保對象的收入都是一個難點(diǎn),因此,要重構(gòu)以負(fù)所得稅為核心的征稅式低保制度,就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居民收支信息庫,加快低保配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采用動態(tài)的綜合管理信息系統(tǒng),加大與財政、稅務(wù)、銀行、房管和公安等部門配合的力度,從而保證新制度綜合地、系統(tǒng)地、有效地推行。
參考文獻(xiàn):
[1]喬俊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公共政策因應(yīng):韓國做法及啟示[J].改革,2011,(8):90-91.
[2]約翰·貝茨·克拉克.財富的分配[M].邵大海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3.1.
[3]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中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8.5.
[4]Friedman,M.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5]鄭功成.社會保障與弱勢群體保護(hù)[DB/OL].中國網(wǎng),2003-01-20.
[6]陸銘.勞動和人力資源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7.82-89.
[7]中國經(jīng)濟(jì)改革研究基金會,中國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研究會聯(lián)合專家組.收入分配與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遠(yuǎn)東出版社,2005.61-63.
[8]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權(quán)衡[M].王忠民,黃清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81-83.
[9]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xué)[M].張智勇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6.110.
(責(zé)任編輯:劉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