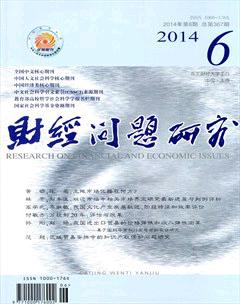基于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視角的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
蔡炯 田翠香 程晉烽
摘 要:社會(huì)發(fā)展離不開(kāi)公共產(chǎn)品。在我國(guó),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發(fā)展和改革受到了各方的關(guān)注。本文從公共事業(yè)單位受托經(jīng)營(yíng)公共產(chǎn)品可能存在的代理問(wèn)題出發(fā),從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視角研究了其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有利于避免代理失效的發(fā)生。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探討了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原則。最后,筆者對(duì)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實(shí)踐中應(yīng)關(guān)注的幾個(gè)問(wèn)題進(jìn)行了分析。
關(guān)鍵詞: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20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0-176X(2014)06-0081-05
一、問(wèn)題的提出
社會(huì)發(fā)展離不開(kāi)公共經(jīng)濟(jì)部門(mén)所提供的公共產(chǎn)品。公共事業(yè)單位是公共經(jīng)濟(jì)部門(mén)的主體。由于我國(guó)公共產(chǎn)品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的差異,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發(fā)展和改革近年來(lái)受到了各方關(guān)注。
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中,公共經(jīng)濟(jì)部門(mén)與私人經(jīng)濟(jì)主體相對(duì)。兩者的運(yùn)行均需要一定的經(jīng)濟(jì)資源,但兩者的經(jīng)營(yíng)目標(biāo)和管理方式存在差異:私人經(jīng)濟(jì)主要以利潤(rùn)作為目標(biāo),具有自利性;而公共經(jīng)濟(jì)部門(mén)則需更多地考慮公共目標(biāo)和社會(huì)利益,具有公益性;前者多提供私人產(chǎn)品,而后者多提供公共產(chǎn)品。
在公共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中,由于外部性和生產(chǎn)的規(guī)模要求等,對(duì)于社會(huì)公眾的公共產(chǎn)品需求,由于私人經(jīng)濟(jì)的資本、技術(shù)和人員等的限制,需要由政府進(jìn)行提供,形成第一層次委托代理關(guān)系;從社會(huì)分工的角度,政府設(shè)立或委托公共事業(yè)單位來(lái)提供相應(yīng)的公共產(chǎn)品,以節(jié)省社會(huì)成本,此時(shí)形成第二層委托代理關(guān)系。
如圖1所示。
這種委托代理關(guān)系的形成是隨著社會(huì)化大生產(chǎn)和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模擴(kuò)大等出現(xiàn)的一種有效的分工,這是公共事業(yè)單位賴以存在的基礎(chǔ),依靠代理合約來(lái)維系,并由此產(chǎn)生了權(quán)力和責(zé)任的重新分配。
顯然,公共事業(yè)單位為完成委托者委托進(jìn)行的所有活動(dòng)均為兩者間的交易。在委托代理關(guān)系中由于雙方信息不對(duì)稱(chēng)和委托代理合約不完全等容易出現(xiàn)道德風(fēng)險(xiǎn)和逆向選擇等情況,導(dǎo)致這種分工的有效性不完全,不能實(shí)現(xiàn)委托人的委托目標(biāo),筆者將其定義為代理失效。
產(chǎn)生代理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有限理性——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組織行為最后都需歸于具體的行為人,人的行為會(huì)影響到組織的決策和績(jī)效。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認(rèn)為,人是具有雙重動(dòng)機(jī)、有限理性和機(jī)會(huì)主義傾向的“有限理性經(jīng)濟(jì)人”[1-2-3]。即使面對(duì)全部信息,“有限理性經(jīng)濟(jì)人”由于偏好、動(dòng)機(jī)、對(duì)風(fēng)險(xiǎn)的判斷和對(duì)信息的理解差異及其與組織目標(biāo)的不完全一致,會(huì)導(dǎo)致道德風(fēng)險(xiǎn)或逆向選擇,影響到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發(fā)展及組織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現(xiàn)實(shí)中人們往往試圖明確界定委托代理關(guān)系,但這往往難以實(shí)現(xiàn),因?yàn)槿藗儾荒芨F盡所有的情況并在合約中加以說(shuō)明,即使在極端情況下能夠這樣做,為此付出的努力等也將形成不能忽視的“交易成本”。由于公共事業(yè)單位產(chǎn)品的公益性及其特殊的組織結(jié)構(gòu),公共事業(yè)單位在提供公共產(chǎn)品的過(guò)程中使得其較一般私人經(jīng)濟(jì)主體發(fā)生代理失效的可能性更大。
通常,“重復(fù)博弈”和“聲譽(yù)機(jī)制”被用于防止代理失效[4]。當(dāng)委托代理雙方能保持長(zhǎng)期關(guān)系、并建立起足夠的信心時(shí),雙方通過(guò)重復(fù)博弈,可以降低或減少“交易成本”,但前提是在長(zhǎng)期考察中代理人和委托人都持續(xù)、一貫地堅(jiān)持,并足夠理性,否則,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投機(jī)性,使得這種“重復(fù)博弈”,通過(guò)時(shí)間來(lái)驗(yàn)證結(jié)果可能變得不確定。至于“聲譽(yù)機(jī)制”,其形成需要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和時(shí)間,以便“有限理性經(jīng)濟(jì)人”能夠確認(rèn)“聲譽(yù)”符合要求從而做出選擇,因而存在局限性。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中,需要其他制度或機(jī)制作為補(bǔ)充以避免“代理失效”情況的發(fā)生。
二、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
威廉姆森和馬斯滕[5]認(rèn)為,制度使得人們的行為具有可持續(xù)性和可預(yù)見(jiàn)性,從而降低人們對(duì)交易結(jié)果的不確定性。不同制度下交易成本不同,效率也不相同。阿羅[6]指出,如果經(jīng)濟(jì)運(yùn)行成本是高昂的,那么整個(gè)經(jīng)濟(jì)體系就不可能獲得良好的績(jī)效;人的機(jī)會(huì)主義本性增加了市場(chǎng)交易的復(fù)雜性,影響了市場(chǎng)的效率,制度對(duì)于激勵(lì)人們避免機(jī)會(huì)主義或防止機(jī)會(huì)主義出現(xiàn)是非常重要的,此時(shí)交易成本就演化為經(jīng)濟(jì)制度的運(yùn)行費(fèi)用而非其他,從而降低了單筆交易成本。可以推論,在制度環(huán)境中人及人之外的環(huán)境、制度、人的動(dòng)機(jī)(激勵(lì))、行為及人的狀態(tài)間的關(guān)系就如圖1所示。代理合約是其中之一。
由科斯第二定理可知,當(dāng)市場(chǎng)存在交易成本時(shí),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安排至關(guān)重要[7]。威廉姆斯認(rèn)為,產(chǎn)權(quán)包括一個(gè)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quán)利;產(chǎn)權(quán)安排確定了每個(gè)人對(duì)于組織資源行為的規(guī)范,每個(gè)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或承擔(dān)不遵守這種關(guān)系的成本,產(chǎn)權(quán)成為一種社會(huì)工具,它們能事實(shí)上幫助一個(gè)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jìn)行交易時(shí)的合理預(yù)期。當(dāng)然,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建立是有成本的,只有當(dāng)產(chǎn)權(quán)界定的收益大于產(chǎn)權(quán)界定的成本時(shí),人們才有動(dòng)力(或激勵(lì)機(jī)制)去制定規(guī)則和界定產(chǎn)權(quán)。不同產(chǎn)權(quán)制度具有不同的建立和執(zhí)行成本,人們需要在正式的產(chǎn)權(quán)制度如“物權(quán)法”之類(lèi)的法律和非正式制度如一般管理制度、規(guī)則等之間進(jìn)行選擇。
如果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公共事業(yè)單位將因自身績(jī)效的好與壞,承擔(dān)相應(yīng)的責(zé)任,獲得相應(yīng)的激勵(lì),得到更多或更少的經(jīng)營(yíng)資源等,從這一角度看,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而由于績(jī)效責(zé)任不明確導(dǎo)致將行為人應(yīng)承擔(dān)的責(zé)任或應(yīng)享有的權(quán)益沒(méi)有明確界定而產(chǎn)生外部性,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實(shí)質(zhì)也是將組織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的外部性內(nèi)在化的過(guò)程。因而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有利于公共事業(yè)單位保持代理有效性。
在存在代理失效的情況下,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是否是經(jīng)濟(jì)的,或者說(shuō)是否對(duì)代理失效有作用呢?以系列1表示投入成本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后的交易成本,系列2表示沒(méi)有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交易成本,如圖2所示。
因此,在以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為必要的制度補(bǔ)充時(shí),可以節(jié)省公共事業(yè)單位的交易成本,促進(jìn)交易發(fā)生,減少或避免代理失敗情況的發(fā)生,因?yàn)閷?duì)于代理者而言,當(dāng)與委托者目標(biāo)一致的交易發(fā)生后,結(jié)果是可預(yù)期的,從而有利于提高公共產(chǎn)品的供給效果和效率,擴(kuò)大社會(huì)福利,實(shí)現(xiàn)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的組織目標(biāo)。
三、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建設(shè)原則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們對(duì)所研究的對(duì)象往往無(wú)法窮盡各種情況,為了保證行為的一致性,人們往往通過(guò)原則來(lái)實(shí)現(xiàn)對(duì)某類(lèi)行為總的、大體上的指導(dǎo),典型如會(huì)計(jì)信息質(zhì)量要求、財(cái)務(wù)管理原則等。對(duì)于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而言,評(píng)價(jià)原則具有重要的作用。
實(shí)踐中,人們已認(rèn)識(shí)到了評(píng)價(jià)原則的重要性,但尚未形成統(tǒng)一觀點(diǎn),在西方公共管理實(shí)踐中的,從組織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程度及取得相應(yīng)結(jié)果的有效性和效率等角度,有經(jīng)濟(jì)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等“3E”原則或加上公平性后的“4E”原則[8-9-10]。相較而言,似乎“4E”原則更為全面。但考慮到利益分配本身沒(méi)有絕對(duì)的公平,從不同角度理解公平會(huì)有不同的解釋?zhuān)绞且环N狀態(tài)和結(jié)果,而非影響因素,本文更傾向于“3E”原則。在此基礎(chǔ)上,考慮到事業(yè)單位的特殊屬性,筆者認(rèn)為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建設(shè)時(shí)還應(yīng)遵循治理原則、可比性原則和成本收益原則等,具體闡述如下。
1.治理原則
治理意為統(tǒng)治或管理,是委托代理關(guān)系的組織都需要的管理行為和期望的結(jié)果。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意在減少代理失效的情況發(fā)生,以更好地實(shí)現(xiàn)委托者的目標(biāo)。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內(nèi)容、指標(biāo)及權(quán)重的具體設(shè)計(jì)有很大的選擇空間。人人皆大歡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需與經(jīng)濟(jì)管理目標(biāo)與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目標(biāo)緊密相關(guān),在具體考慮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原則時(shí)需關(guān)注產(chǎn)權(quán)的完備性(特別是關(guān)鍵權(quán)利束的具備)、排他性(明確責(zé)任以避免“外部性”和“搭便車(chē)”等行為)、明晰性(明晰的產(chǎn)權(quán)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價(jià)值性(意味著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實(shí)施需要激勵(lì),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應(yīng)被用于決策等)、可轉(zhuǎn)讓性(意味著決策權(quán)和決策后果的承擔(dān),并保證權(quán)利不被壟斷)和穩(wěn)定性等屬性。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設(shè)計(jì)和實(shí)施應(yīng)符合組織治理的需要。由于公益事業(yè)單位的產(chǎn)品公益性,各有其存在的獨(dú)特使命,不能僅以財(cái)務(wù)指標(biāo)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而應(yīng)輔以必要的非財(cái)務(wù)指標(biāo)。卡普蘭和諾頓的平衡計(jì)分卡提供了一個(gè)很好的指標(biāo)組織框架。同時(shí),將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作為組織實(shí)現(xiàn)治理的一種手段時(shí),需考慮到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在管理效果上具有的“柔性”。這種柔性體現(xiàn)在很多方面,主要體現(xiàn)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過(guò)程及結(jié)果對(duì)于績(jī)效的責(zé)任人的權(quán)威性上。就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而言,不同的評(píng)價(jià)者、不同的評(píng)價(jià)范圍、對(duì)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不同處理,會(huì)賦予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不同的“權(quán)威”;對(duì)于績(jī)效的責(zé)任人,或者說(shuō)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的承擔(dān)者而言,它可以如同法律一樣客觀“無(wú)情”,也可以如同一項(xiàng)普通的“建議”一樣“無(wú)力”。這種柔性會(huì)影響到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治理效果。
在這一原則下,在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眾多利益相關(guān)者中,由政府即委托者主導(dǎo)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建設(shè)最為經(jīng)濟(jì),具體地可由行業(yè)協(xié)會(huì)負(fù)責(zé)將有助于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的實(shí)施。
2.可比性原則
對(duì)組織經(jīng)營(yíng)管理較好的一種方法就是進(jìn)行比較研究,但所做的比較和得出的結(jié)論應(yīng)當(dāng)是恰當(dāng)?shù)摹=M織間的比較將產(chǎn)生競(jìng)爭(zhēng)與合作的結(jié)果。績(jī)效信息的比較應(yīng)包括績(jī)效的組織間橫向比較和同一組織不同期間的縱向比較。
當(dāng)然,績(jī)效信息可比的前提是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的可實(shí)施,即評(píng)價(jià)過(guò)程中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可從現(xiàn)有的會(huì)計(jì)核算、統(tǒng)計(jì)核算和業(yè)務(wù)核算數(shù)據(jù)中獲得,而非“虛無(wú)”的完美。正如姚正海[11]所述,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工作重要的是把握本質(zhì),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目標(biāo)是要避免評(píng)價(jià)時(shí)的主觀臆斷、懷疑與測(cè)量的偏差,而并非將所有的東西全部加以量化才夠客觀。
此外,由于組織是在不斷發(fā)展變化的,要做到不同時(shí)期績(jī)效的可比,還需要評(píng)價(jià)體系本身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這意味著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在設(shè)計(jì)之初就需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有關(guān)標(biāo)準(zhǔn)和指標(biāo)設(shè)計(jì)需要對(duì)外部環(huán)境具有一定的適應(yīng)性。
3.成本收益原則
在已有效率原則和經(jīng)濟(jì)性原則的前提下提出成本收益原則似乎是重復(fù)的。這里想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成本的可承擔(dān)和投入的可控。盡管公共事業(yè)單位在性質(zhì)上屬于公益單位、來(lái)自政府部門(mén)或社會(huì)捐贈(zèng)、不以盈利為目的,但投入要素的多少仍要受到社會(huì)、國(guó)家及地方政府財(cái)政的可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對(duì)于具體的公共事業(yè)單位來(lái)說(shuō),資源更是有限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從本質(zhì)上是一個(gè)信息系統(tǒng)。績(jī)效信息的收集和處理是有成本的,需要消耗組織的資源,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具體設(shè)計(jì)和實(shí)施中,應(yīng)在成本收益原則的指導(dǎo)下,量力而為、有重點(diǎn)地設(shè)計(jì)和開(kāi)展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工作,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過(guò)程及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應(yīng)是可控的。
譬如,2005年聯(lián)合國(guó)可持續(xù)發(fā)展委員會(huì)推出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biāo)體系第三版,是目前最具權(quán)威的國(guó)際和國(guó)家一級(jí)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指標(biāo)體系,從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環(huán)境和制度四個(gè)方面展開(kāi)評(píng)價(jià),但該指標(biāo)體系的指標(biāo)設(shè)置過(guò)于龐雜,過(guò)分追求完美,在目前狀況下全部數(shù)據(jù)獲得十分困難,同時(shí)因該體系未曾涉及全部指標(biāo)最后的綜合等,影響了該指標(biāo)體系的實(shí)際使用[12]。
四、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建設(shè)中應(yīng)關(guān)注的幾個(gè)問(wèn)題
好的制度還需要好的實(shí)施,在使其成為“實(shí)質(zhì)上”而非“形式上“的制度的過(guò)程中,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從以下幾點(diǎn)入手。
1. 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應(yīng)常態(tài)化
制度(規(guī)則)本身就是人們不斷博弈的結(jié)果,其對(duì)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來(lái)源于其降低了長(zhǎng)期交易結(jié)果預(yù)期的不確定性。“制度”通常意味著某種行為的慣例和經(jīng)常化,只有當(dāng)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成為組織的管理常態(tài)之一,才能真正起到引導(dǎo)作用,避免管理機(jī)構(gòu)解決問(wèn)題時(shí)僅關(guān)注具有一次性水平效應(yīng)的績(jī)效活動(dòng)而不從長(zhǎng)遠(yuǎn)地角度出發(fā)解決組織發(fā)展問(wèn)題。當(dāng)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成為一種制度時(shí),評(píng)價(jià)者提供績(jī)效信息就有了責(zé)任,績(jī)效信息將具有一定的公信力,提高信息收益。在此基礎(chǔ),在績(jī)效和激勵(lì)之間建立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則會(huì)更好地實(shí)現(xiàn)公益事業(yè)單位受托使命。應(yīng)該說(shuō)西方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實(shí)踐的過(guò)程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
一個(gè)完善和穩(wěn)定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系統(tǒng)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實(shí)踐中逐步完成。筆者認(rèn)為可以借鑒企業(yè)部門(mén)業(yè)績(jī)報(bào)告與考核的做法做好如下幾個(gè)步驟:首先,要做好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工作的組織工作;其次,應(yīng)編制績(jī)效報(bào)告;再次,應(yīng)進(jìn)行原因調(diào)查進(jìn)行改善;最后,還應(yīng)根據(jù)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進(jìn)行獎(jiǎng)勵(lì)與懲罰。獎(jiǎng)勵(lì)通過(guò)贊許形成正向激勵(lì),而懲罰通過(guò)阻止對(duì)不符合期望發(fā)生的行為形成反向激勵(lì),激勵(lì)應(yīng)當(dāng)恰當(dāng),這就涉及到激勵(lì)問(wèn)題。
實(shí)踐中,習(xí)慣的力量不可忽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實(shí)施等需要消耗資源,會(huì)產(chǎn)生成本,同時(shí)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基礎(chǔ)上的獎(jiǎng)懲固然有利于組織績(jī)效的改善,但組織行為的慣性以及獎(jiǎng)懲的實(shí)施會(huì)招致組織中人員的反對(duì)等,都構(gòu)成了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進(jìn)行下去的阻力。但人們需要有長(zhǎng)遠(yuǎn)的目光。
2. 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
在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要實(shí)現(xiàn)的評(píng)價(jià)目標(biāo),從橫向上看,需要大量的信息并被有效的組織起來(lái)才能實(shí)現(xiàn)評(píng)價(jià)目的;從縱向上看,不同期間的績(jī)效信息相比才能更好地發(fā)現(xiàn)組織在經(jīng)營(yíng)中的問(wèn)題,并提供改進(jìn)的線索。特別是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成為制度并常態(tài)化后,連續(xù)期間展開(kāi)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更有利于發(fā)現(xiàn)組織績(jī)效變動(dòng)的原因,為未來(lái)提高績(jī)效提供更為完整的依據(jù)。要做到這一點(diǎn),就需要保留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降低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的復(fù)雜程度和成本。
而在目前的實(shí)踐中,對(duì)公共事業(yè)單位展開(kāi)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大量數(shù)據(jù)的搜集需通過(guò)對(duì)已有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理加工,或通過(guò)問(wèn)卷獲取,對(duì)于不能直接以利潤(rùn)衡量的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如國(guó)有林場(chǎng)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搜集、基本醫(yī)療服務(wù)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搜集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shí)間等,數(shù)據(jù)取得實(shí)屬來(lái)之不易。但在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中,這些珍貴數(shù)據(jù)的使用卻常常是一次性的,大多數(shù)的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和研究都是圍繞評(píng)價(jià)客體特定時(shí)間點(diǎn)或時(shí)間段的績(jī)效展開(kāi)的,數(shù)據(jù)隨評(píng)價(jià)者分散而分散,并且,多數(shù)情況下,相似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被不同的評(píng)價(jià)主體不同程度的重復(fù)著,但卻很難對(duì)評(píng)價(jià)客體形成完整、系統(tǒng)的看法。顯然,當(dāng)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化后則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問(wèn)題。
3. 改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中的激勵(lì)機(jī)制
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與激勵(lì)相輔相成,兩者與其他管理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的管理循環(huán)。激勵(lì)是基于組織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結(jié)果,從評(píng)價(jià)目的出發(fā),通過(guò)激勵(lì)激發(fā)組織中的人員來(lái)實(shí)現(xiàn)組織的目的,無(wú)論是組織外部還是內(nèi)部,激勵(lì)都只能施加于組織中的人員,使得評(píng)價(jià)具有了經(jīng)濟(jì)后果。在這一意義上激勵(lì)成就了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使之在本質(zhì)上作為一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
假設(shè)有兩個(gè)狀態(tài)類(lèi)似的組織A、B,甲、乙是它們的管理者,兩者同時(shí)上任,甲帶領(lǐng)A組織從組織戰(zhàn)略出發(fā),圍繞組織發(fā)展實(shí)施了必要的日常工作,由于定位準(zhǔn)確、措施到位,A發(fā)展平穩(wěn),當(dāng)外界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事件時(shí),A平穩(wěn)度過(guò);乙采取了與甲不同的管理方式,其以維持B現(xiàn)狀為日常工作,當(dāng)同樣面臨風(fēng)險(xiǎn)事件時(shí),B組織出現(xiàn)危機(jī),乙努力減少危機(jī)損失,假設(shè)其業(yè)績(jī)最終與甲的業(yè)績(jī)類(lèi)似,但由于危機(jī)的影響重大,乙挽救危機(jī)的行為廣為人知。此時(shí),評(píng)價(jià)甲、乙的工作并給以激勵(lì),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因?yàn)橐以谖C(jī)中的行為,使得乙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以此作為“信譽(yù)”的話,似乎乙較甲應(yīng)受到更多的正向激勵(lì),如升職或加薪;另一種情況,盡管兩者業(yè)績(jī)類(lèi)似,乙在危機(jī)中力挽狂瀾,但顯然在乙領(lǐng)導(dǎo)下的B組織的風(fēng)險(xiǎn)大于甲領(lǐng)導(dǎo)下的A。從風(fēng)險(xiǎn)與報(bào)酬的角度看,不同風(fēng)險(xiǎn)的投資,投資者要求不同的必要報(bào)酬率,風(fēng)險(xiǎn)越大要求的必要報(bào)酬率越高,組織經(jīng)營(yíng)的成本就越高,在同樣收益的條件下,風(fēng)險(xiǎn)越高,管理者的績(jī)效越差,這樣,甲的績(jī)效實(shí)質(zhì)上高于乙的績(jī)效,因此,甲較乙應(yīng)受到更多的正向激勵(lì),如升職或加薪等。
在不恰當(dāng)?shù)募?lì)機(jī)制下,會(huì)使得組織管理者在“不求有功但求無(wú)過(guò)”的氛圍中,過(guò)于謹(jǐn)慎而短視、固步自封,使得組織管理者的發(fā)展與組織發(fā)展相背離。組織中的人與組織目標(biāo)存在共同之處,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dǎo)致代理無(wú)效情況的發(fā)生。“重復(fù)博弈”和“聲譽(yù)機(jī)制”被用于防止代理無(wú)效情況的發(fā)生,關(guān)鍵在于對(duì)“信譽(yù)”的界定,這與組織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緊密相聯(lián),評(píng)價(jià)機(jī)構(gòu)對(duì)風(fēng)險(xiǎn)的偏好會(huì)影響到“信譽(yù)”的形成,從而影響激勵(lì)效果。
在績(jī)效和激勵(lì)之間建立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會(huì)更好地實(shí)現(xiàn)組織目標(biāo)。
五、結(jié)束語(yǔ)
在公共產(chǎn)品供給要求不斷擴(kuò)大和完善的今天,公共事業(yè)單位受托提供代理公共產(chǎn)品的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但需要其他制度或機(jī)制作為補(bǔ)充以避免“代理失敗”情況的發(fā)生。由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是必要的和經(jīng)濟(jì)的。在建設(sh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時(shí)遵循“3E”原則、治理原則、可比性原則和成本收益原則等,可以使得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過(guò)程與其治理過(guò)程重合。此外,還需關(guān)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在實(shí)踐中的推行。
參考文獻(xiàn):
[1] 盧現(xiàn)祥.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4.34-40.
[2] 哈羅德·德姆塞茨.企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M]. 梁小民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4.20-44.
[3] 丁菊紅.中國(guó)轉(zhuǎn)型中的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公共品供給激勵(lì)[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10.19-21.
[4]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4.176-178.
[5] 奧利佛·威廉姆森,斯科特·馬斯滕.交易成本經(jīng)濟(jì)學(xué)——經(jīng)典名篇選讀[M]. 李自杰,蔡銘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20.
[6] 范家驤,劉文忻.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89-192.
[7] 余永定,張宇燕,鄭秉文.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第三版)[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03.234-236.
[8] 胡稅根.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管理——迎接效能革命的挑戰(zhàn)[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5.132.
[9] 喬納森·R.湯普金斯.公共管理學(xué)說(shuō)史——組織理論與公共管理[M]. 夏鎮(zhèn)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24.
[10] 胡寧生.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評(píng)估[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8.36.
[11] 姚正海.上市公司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及績(jī)效提升路徑淺探[J].財(cái)會(huì)月刊,2007,(3):19-21.
[12] 嚴(yán)耕.生態(tài)文明綠皮書(shū):中國(guó)省域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評(píng)價(jià)報(bào)告(ECI 2012)[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230-231.
(責(zé)任編輯:巴紅靜)
實(shí)踐中,習(xí)慣的力量不可忽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實(shí)施等需要消耗資源,會(huì)產(chǎn)生成本,同時(shí)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基礎(chǔ)上的獎(jiǎng)懲固然有利于組織績(jī)效的改善,但組織行為的慣性以及獎(jiǎng)懲的實(shí)施會(huì)招致組織中人員的反對(duì)等,都構(gòu)成了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進(jìn)行下去的阻力。但人們需要有長(zhǎng)遠(yuǎn)的目光。
2. 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
在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要實(shí)現(xiàn)的評(píng)價(jià)目標(biāo),從橫向上看,需要大量的信息并被有效的組織起來(lái)才能實(shí)現(xiàn)評(píng)價(jià)目的;從縱向上看,不同期間的績(jī)效信息相比才能更好地發(fā)現(xiàn)組織在經(jīng)營(yíng)中的問(wèn)題,并提供改進(jìn)的線索。特別是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成為制度并常態(tài)化后,連續(xù)期間展開(kāi)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更有利于發(fā)現(xiàn)組織績(jī)效變動(dòng)的原因,為未來(lái)提高績(jī)效提供更為完整的依據(jù)。要做到這一點(diǎn),就需要保留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降低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的復(fù)雜程度和成本。
而在目前的實(shí)踐中,對(duì)公共事業(yè)單位展開(kāi)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大量數(shù)據(jù)的搜集需通過(guò)對(duì)已有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理加工,或通過(guò)問(wèn)卷獲取,對(duì)于不能直接以利潤(rùn)衡量的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如國(guó)有林場(chǎng)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搜集、基本醫(yī)療服務(wù)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搜集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shí)間等,數(shù)據(jù)取得實(shí)屬來(lái)之不易。但在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中,這些珍貴數(shù)據(jù)的使用卻常常是一次性的,大多數(shù)的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和研究都是圍繞評(píng)價(jià)客體特定時(shí)間點(diǎn)或時(shí)間段的績(jī)效展開(kāi)的,數(shù)據(jù)隨評(píng)價(jià)者分散而分散,并且,多數(shù)情況下,相似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被不同的評(píng)價(jià)主體不同程度的重復(fù)著,但卻很難對(duì)評(píng)價(jià)客體形成完整、系統(tǒng)的看法。顯然,當(dāng)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化后則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問(wèn)題。
3. 改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中的激勵(lì)機(jī)制
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與激勵(lì)相輔相成,兩者與其他管理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的管理循環(huán)。激勵(lì)是基于組織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結(jié)果,從評(píng)價(jià)目的出發(fā),通過(guò)激勵(lì)激發(fā)組織中的人員來(lái)實(shí)現(xiàn)組織的目的,無(wú)論是組織外部還是內(nèi)部,激勵(lì)都只能施加于組織中的人員,使得評(píng)價(jià)具有了經(jīng)濟(jì)后果。在這一意義上激勵(lì)成就了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使之在本質(zhì)上作為一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
假設(shè)有兩個(gè)狀態(tài)類(lèi)似的組織A、B,甲、乙是它們的管理者,兩者同時(shí)上任,甲帶領(lǐng)A組織從組織戰(zhàn)略出發(fā),圍繞組織發(fā)展實(shí)施了必要的日常工作,由于定位準(zhǔn)確、措施到位,A發(fā)展平穩(wěn),當(dāng)外界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事件時(shí),A平穩(wěn)度過(guò);乙采取了與甲不同的管理方式,其以維持B現(xiàn)狀為日常工作,當(dāng)同樣面臨風(fēng)險(xiǎn)事件時(shí),B組織出現(xiàn)危機(jī),乙努力減少危機(jī)損失,假設(shè)其業(yè)績(jī)最終與甲的業(yè)績(jī)類(lèi)似,但由于危機(jī)的影響重大,乙挽救危機(jī)的行為廣為人知。此時(shí),評(píng)價(jià)甲、乙的工作并給以激勵(lì),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因?yàn)橐以谖C(jī)中的行為,使得乙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以此作為“信譽(yù)”的話,似乎乙較甲應(yīng)受到更多的正向激勵(lì),如升職或加薪;另一種情況,盡管兩者業(yè)績(jī)類(lèi)似,乙在危機(jī)中力挽狂瀾,但顯然在乙領(lǐng)導(dǎo)下的B組織的風(fēng)險(xiǎn)大于甲領(lǐng)導(dǎo)下的A。從風(fēng)險(xiǎn)與報(bào)酬的角度看,不同風(fēng)險(xiǎn)的投資,投資者要求不同的必要報(bào)酬率,風(fēng)險(xiǎn)越大要求的必要報(bào)酬率越高,組織經(jīng)營(yíng)的成本就越高,在同樣收益的條件下,風(fēng)險(xiǎn)越高,管理者的績(jī)效越差,這樣,甲的績(jī)效實(shí)質(zhì)上高于乙的績(jī)效,因此,甲較乙應(yīng)受到更多的正向激勵(lì),如升職或加薪等。
在不恰當(dāng)?shù)募?lì)機(jī)制下,會(huì)使得組織管理者在“不求有功但求無(wú)過(guò)”的氛圍中,過(guò)于謹(jǐn)慎而短視、固步自封,使得組織管理者的發(fā)展與組織發(fā)展相背離。組織中的人與組織目標(biāo)存在共同之處,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dǎo)致代理無(wú)效情況的發(fā)生。“重復(fù)博弈”和“聲譽(yù)機(jī)制”被用于防止代理無(wú)效情況的發(fā)生,關(guān)鍵在于對(duì)“信譽(yù)”的界定,這與組織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緊密相聯(lián),評(píng)價(jià)機(jī)構(gòu)對(duì)風(fēng)險(xiǎn)的偏好會(huì)影響到“信譽(yù)”的形成,從而影響激勵(lì)效果。
在績(jī)效和激勵(lì)之間建立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會(huì)更好地實(shí)現(xiàn)組織目標(biāo)。
五、結(jié)束語(yǔ)
在公共產(chǎn)品供給要求不斷擴(kuò)大和完善的今天,公共事業(yè)單位受托提供代理公共產(chǎn)品的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但需要其他制度或機(jī)制作為補(bǔ)充以避免“代理失敗”情況的發(fā)生。由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是必要的和經(jīng)濟(jì)的。在建設(sh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時(shí)遵循“3E”原則、治理原則、可比性原則和成本收益原則等,可以使得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過(guò)程與其治理過(guò)程重合。此外,還需關(guān)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在實(shí)踐中的推行。
參考文獻(xiàn):
[1] 盧現(xiàn)祥.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4.34-40.
[2] 哈羅德·德姆塞茨.企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M]. 梁小民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4.20-44.
[3] 丁菊紅.中國(guó)轉(zhuǎn)型中的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公共品供給激勵(lì)[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10.19-21.
[4]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4.176-178.
[5] 奧利佛·威廉姆森,斯科特·馬斯滕.交易成本經(jīng)濟(jì)學(xué)——經(jīng)典名篇選讀[M]. 李自杰,蔡銘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20.
[6] 范家驤,劉文忻.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89-192.
[7] 余永定,張宇燕,鄭秉文.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第三版)[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03.234-236.
[8] 胡稅根.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管理——迎接效能革命的挑戰(zhàn)[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5.132.
[9] 喬納森·R.湯普金斯.公共管理學(xué)說(shuō)史——組織理論與公共管理[M]. 夏鎮(zhèn)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24.
[10] 胡寧生.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評(píng)估[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8.36.
[11] 姚正海.上市公司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及績(jī)效提升路徑淺探[J].財(cái)會(huì)月刊,2007,(3):19-21.
[12] 嚴(yán)耕.生態(tài)文明綠皮書(shū):中國(guó)省域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評(píng)價(jià)報(bào)告(ECI 2012)[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230-231.
(責(zé)任編輯:巴紅靜)
實(shí)踐中,習(xí)慣的力量不可忽視。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實(shí)施等需要消耗資源,會(huì)產(chǎn)生成本,同時(shí)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結(jié)果基礎(chǔ)上的獎(jiǎng)懲固然有利于組織績(jī)效的改善,但組織行為的慣性以及獎(jiǎng)懲的實(shí)施會(huì)招致組織中人員的反對(duì)等,都構(gòu)成了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進(jìn)行下去的阻力。但人們需要有長(zhǎng)遠(yuǎn)的目光。
2. 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
在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要實(shí)現(xiàn)的評(píng)價(jià)目標(biāo),從橫向上看,需要大量的信息并被有效的組織起來(lái)才能實(shí)現(xiàn)評(píng)價(jià)目的;從縱向上看,不同期間的績(jī)效信息相比才能更好地發(fā)現(xiàn)組織在經(jīng)營(yíng)中的問(wèn)題,并提供改進(jìn)的線索。特別是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成為制度并常態(tài)化后,連續(xù)期間展開(kāi)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更有利于發(fā)現(xiàn)組織績(jī)效變動(dòng)的原因,為未來(lái)提高績(jī)效提供更為完整的依據(jù)。要做到這一點(diǎn),就需要保留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降低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的復(fù)雜程度和成本。
而在目前的實(shí)踐中,對(duì)公共事業(yè)單位展開(kāi)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大量數(shù)據(jù)的搜集需通過(guò)對(duì)已有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整理加工,或通過(guò)問(wèn)卷獲取,對(duì)于不能直接以利潤(rùn)衡量的公共事業(yè)單位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如國(guó)有林場(chǎng)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搜集、基本醫(yī)療服務(wù)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搜集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shí)間等,數(shù)據(jù)取得實(shí)屬來(lái)之不易。但在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中,這些珍貴數(shù)據(jù)的使用卻常常是一次性的,大多數(shù)的評(píng)價(jià)實(shí)務(wù)和研究都是圍繞評(píng)價(jià)客體特定時(shí)間點(diǎn)或時(shí)間段的績(jī)效展開(kāi)的,數(shù)據(jù)隨評(píng)價(jià)者分散而分散,并且,多數(shù)情況下,相似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活動(dòng)被不同的評(píng)價(jià)主體不同程度的重復(fù)著,但卻很難對(duì)評(píng)價(jià)客體形成完整、系統(tǒng)的看法。顯然,當(dāng)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化后則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問(wèn)題。
3. 改善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中的激勵(lì)機(jī)制
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與激勵(lì)相輔相成,兩者與其他管理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的管理循環(huán)。激勵(lì)是基于組織績(jī)效評(píng)價(jià)的結(jié)果,從評(píng)價(jià)目的出發(fā),通過(guò)激勵(lì)激發(fā)組織中的人員來(lái)實(shí)現(xiàn)組織的目的,無(wú)論是組織外部還是內(nèi)部,激勵(lì)都只能施加于組織中的人員,使得評(píng)價(jià)具有了經(jīng)濟(jì)后果。在這一意義上激勵(lì)成就了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使之在本質(zhì)上作為一種產(chǎn)權(quán)制度。
假設(shè)有兩個(gè)狀態(tài)類(lèi)似的組織A、B,甲、乙是它們的管理者,兩者同時(shí)上任,甲帶領(lǐng)A組織從組織戰(zhàn)略出發(fā),圍繞組織發(fā)展實(shí)施了必要的日常工作,由于定位準(zhǔn)確、措施到位,A發(fā)展平穩(wěn),當(dāng)外界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事件時(shí),A平穩(wěn)度過(guò);乙采取了與甲不同的管理方式,其以維持B現(xiàn)狀為日常工作,當(dāng)同樣面臨風(fēng)險(xiǎn)事件時(shí),B組織出現(xiàn)危機(jī),乙努力減少危機(jī)損失,假設(shè)其業(yè)績(jī)最終與甲的業(yè)績(jī)類(lèi)似,但由于危機(jī)的影響重大,乙挽救危機(jī)的行為廣為人知。此時(shí),評(píng)價(jià)甲、乙的工作并給以激勵(lì),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因?yàn)橐以谖C(jī)中的行為,使得乙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以此作為“信譽(yù)”的話,似乎乙較甲應(yīng)受到更多的正向激勵(lì),如升職或加薪;另一種情況,盡管兩者業(yè)績(jī)類(lèi)似,乙在危機(jī)中力挽狂瀾,但顯然在乙領(lǐng)導(dǎo)下的B組織的風(fēng)險(xiǎn)大于甲領(lǐng)導(dǎo)下的A。從風(fēng)險(xiǎn)與報(bào)酬的角度看,不同風(fēng)險(xiǎn)的投資,投資者要求不同的必要報(bào)酬率,風(fēng)險(xiǎn)越大要求的必要報(bào)酬率越高,組織經(jīng)營(yíng)的成本就越高,在同樣收益的條件下,風(fēng)險(xiǎn)越高,管理者的績(jī)效越差,這樣,甲的績(jī)效實(shí)質(zhì)上高于乙的績(jī)效,因此,甲較乙應(yīng)受到更多的正向激勵(lì),如升職或加薪等。
在不恰當(dāng)?shù)募?lì)機(jī)制下,會(huì)使得組織管理者在“不求有功但求無(wú)過(guò)”的氛圍中,過(guò)于謹(jǐn)慎而短視、固步自封,使得組織管理者的發(fā)展與組織發(fā)展相背離。組織中的人與組織目標(biāo)存在共同之處,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導(dǎo)致代理無(wú)效情況的發(fā)生。“重復(fù)博弈”和“聲譽(yù)機(jī)制”被用于防止代理無(wú)效情況的發(fā)生,關(guān)鍵在于對(duì)“信譽(yù)”的界定,這與組織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緊密相聯(lián),評(píng)價(jià)機(jī)構(gòu)對(duì)風(fēng)險(xiǎn)的偏好會(huì)影響到“信譽(yù)”的形成,從而影響激勵(lì)效果。
在績(jī)效和激勵(lì)之間建立關(guān)聯(lián)機(jī)制,會(huì)更好地實(shí)現(xiàn)組織目標(biāo)。
五、結(jié)束語(yǔ)
在公共產(chǎn)品供給要求不斷擴(kuò)大和完善的今天,公共事業(yè)單位受托提供代理公共產(chǎn)品的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但需要其他制度或機(jī)制作為補(bǔ)充以避免“代理失敗”情況的發(fā)生。由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公共事業(yè)單位建立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是必要的和經(jīng)濟(jì)的。在建設(sh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時(shí)遵循“3E”原則、治理原則、可比性原則和成本收益原則等,可以使得公共事業(yè)單位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過(guò)程與其治理過(guò)程重合。此外,還需關(guān)注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制度在實(shí)踐中的推行。
參考文獻(xiàn):
[1] 盧現(xiàn)祥.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4.34-40.
[2] 哈羅德·德姆塞茨.企業(yè)經(jīng)濟(jì)學(xué)[M]. 梁小民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4.20-44.
[3] 丁菊紅.中國(guó)轉(zhuǎn)型中的財(cái)政分權(quán)與公共品供給激勵(lì)[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10.19-21.
[4]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jīng)濟(jì)學(xué)[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4.176-178.
[5] 奧利佛·威廉姆森,斯科特·馬斯滕.交易成本經(jīng)濟(jì)學(xué)——經(jīng)典名篇選讀[M]. 李自杰,蔡銘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9-20.
[6] 范家驤,劉文忻.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89-192.
[7] 余永定,張宇燕,鄭秉文.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第三版)[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03.234-236.
[8] 胡稅根.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管理——迎接效能革命的挑戰(zhàn)[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5.132.
[9] 喬納森·R.湯普金斯.公共管理學(xué)說(shuō)史——組織理論與公共管理[M]. 夏鎮(zhèn)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24.
[10] 胡寧生.公共部門(mén)績(jī)效評(píng)估[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8.36.
[11] 姚正海.上市公司績(jī)效評(píng)價(jià)體系及績(jī)效提升路徑淺探[J].財(cái)會(huì)月刊,2007,(3):19-21.
[12] 嚴(yán)耕.生態(tài)文明綠皮書(shū):中國(guó)省域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評(píng)價(jià)報(bào)告(ECI 2012)[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230-231.
(責(zé)任編輯:巴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