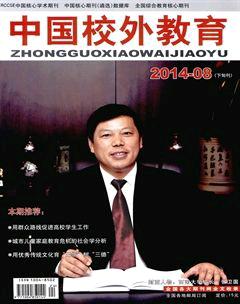簡論柏拉圖的藝術靈感理論
高銘陽
柏拉圖在《文藝對話集》中提出“靈感”說,對文學創作的源泉提出自己的解釋。靈感說的提出,強調了作家的主體性意義和價值。并從理論上證實了作家想象力、創造力、創作靈感等在藝術創作中的作用。柏拉圖對“藝術靈感”的論述,是從神力憑附和回憶兩個方面來具體論述的。
柏拉圖藝術靈感神力憑附回憶
“靈感”這個概念并不是柏拉圖首先提出來的,在他之前,古希臘的唯物論者德謨克利特就曾經說:“沒有心靈的火焰,沒有一種瘋狂式的靈感,就不可能成為詩人。”他還說:“一位詩人以熱情并在神圣的靈感之下所作成的一切詩句,當然是美的”。然而相比之下,柏拉圖的論述明顯更加體系和全面,主要的著作有《申辯篇》《伊安篇》和《斐德若篇》等。
一、從“神力憑附”論藝術靈感
從理性或者道德的立場來對待藝術是柏拉圖著作中一貫的傾向,柏拉圖對于理性的推崇,從他對“美”的定性規定中可以看得出來。柏拉圖認為理性和情感是人性中相互對立的兩種心理活動,理性是高尚的,是具有一定修養的人才具有的,情感是低劣的,情感是人人都有的,喜怒哀樂是人之常情,作為人性中的低劣部分的情感,應該由理性加以控制,這種對于感性世界的理性構建,幫助柏拉圖跳出了感性的模糊狀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具體到藝術創作中,柏拉圖充分肯定了詩人的“靈感”“迷狂”這些非理性存在,認為這是一種神靈附體的著魔狀態,并以此來解釋靈感現象,藝術家們偉大作品的誕生都離不開“靈感”,這些討論主要體現在《伊安篇》中的“神力憑附”說。
“凡是高明的詩人,無論在史詩或抒情詩方面,都不是憑技藝來做成他們的優美的詩歌,而是因為他們得到靈感,有神力憑附著,科里班特巫師們在舞蹈時,理都受一種迷狂支配,抒情詩人們在作詩時也是如此。”柏拉圖在此處所論述的神力憑附,與后來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的“酒神精神”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都強調人性在充分自主和自由的狀態下所達到的那種肉體和精神完美合一,意識飛翔在神性的天空中,藉此獲取多藝術的最為樸素和本質的理解,從而獲得文學創作的動力和精神資源。柏拉圖高度贊揚了“審理憑附”對詩人創作的影響,認為詩人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情感上的公共性特征并不是詩人本身的能力而是神所賦予其的特殊品格:詩人的創作“非憑技藝的規矩,而是依詩神的驅遣。因為詩人制作都是憑神力不是憑技藝,他們各隨所長,專做某一類詩,如激昂的酒神歌、頌神歌、合唱歌、史詩或短長格詩,于某一種體裁的不一定長于他種體裁。”在充分肯定“靈感”的創作源泉的地位和價值的同時,柏拉圖將詩人對“技藝”的學習作為與“靈感”和“神力”相抵觸的存在加以反對。他認為,寫詩靠的是靈感即神力,而不是人為的技能、技藝。認為單靠技藝是寫不出好詩來的。技藝是人人都可以學會的,而靈感則只有神靈憑附在人身上并將其靈氣灌注到人的軀體中時才能得到。他論證說,如果詩人可以憑技藝的規矩作詩,那么對于任何一種體裁或題目的詩,只要學會了做這類詩的規矩、規則,他就都應該能做,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同一詩人,有的詩做得好,有的詩做得不好。即使有名望的大詩人也不例外。原因在哪里呢?柏拉圖認為,原因就在于這類優美的詩本質上不是人的而是神力,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詔語,詩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憑附著,神將靈感賦予詩人,詩人才能進入到“迷狂”的狀態,創造出更好的詩來。
二、從“回憶”論藝術靈感
柏拉圖解說靈感時,除“神靈憑附”外,還提到了“回憶說”,他認為回憶即靈魂對天國或上界的回憶。柏拉圖主要在《斐德若篇》中進行了論述。柏拉圖認為,靈感是塵世事物對上界事物的回憶產生的,人的靈魂和肉體是分離的,靈魂在取得人形之前,便具有知識,附著于肉體后,需要重新學習忘卻的知識,“剩下的只有少數人還能保持回憶的本領。這些少數人每逢見到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就驚喜不能自制”,上界事物即是理式,少數人之所以對上界事物在下界的摹本產生驚喜而不能自制,是由于他回憶起了這個摹本所依據的理式世界,而且不僅僅是回憶了其中的景象,更包括那種喜悅之情,生起眷戀愛慕的情緒,即一種迷狂狀態。柏拉圖認為詩人的創作靈感也是由此而產生的,即由“塵世事物”對“上界事物”的回憶而產生的。在對“回憶”的論述中,其實柏拉圖堅持了自己一貫的“模仿”說,認為詩人的創作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且是那種毫無意義的模仿,并因此將詩人趕出“理想國”。這里從“回憶”來論述靈感,實則是對前文“神力憑附”的補充,增加了現實世界的詩人創作的影響方面。當然,這種解釋同前文所說的對“神力憑附”理論的解說一樣都帶有神秘主義色彩,也強調了藝術家的天賦重要性,只有德才兼備的藝術家才能夠擁有對天國或上界的回憶,得到靈感的光顧,創造出優秀的作品。
三、藝術靈感帶來的“迷狂”
柏拉圖認為,既然神力的依附能夠帶給詩人無限的創作欲望和想象力,而回憶則能夠幫助詩人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上界”的對應物。所以,藝術創作從創新到模仿都找到了“靈感”參與的蹤影,靈感是一切優秀作品誕生的源泉。而靈感的獲取往往意味著詩人陷入“迷狂”的狀態。就不同的迷狂而言,柏拉圖又把它分成四種:第一種是預言的迷狂,如巫神宣示神諭;第二種是教儀的迷狂,如祈禱和宗教儀式;第三種是詩歌的迷狂;第四種是愛情的迷狂。在對詩人“迷狂”狀態的描述中,我們其實可以看到柏拉圖所一直堅持的對于理智和情感、道德與迷狂之間的矛盾的分析:詩歌創作不是有沒有理智,而是什么樣的理智,是對最高理式的絕對信念還是對一般摹仿的技藝掌握?是迷狂的詩還是清醒理智的詩?這也是區別不同層次藝術的問題。
兩千多年前,柏拉圖深刻地意識到了靈感對于一個詩人的重要性,或許是因為當時社會的局限性,需要借助神力、靈魂來闡述靈感的來源問題,但即使是以“神力憑附”為前提的,柏拉圖的理論依然強調了詩人心理功能的積極作用。靈感為一個藝術家帶來了“迷狂”狀態,從表面上看與理性是矛盾的,但卻具有一定的真實性,靈感是藝術家進行良好創作的先決條件,任何一種寫作技巧都無法替代,因此靈感與理性應該是對立統一的,這既富有啟發性,又包含了柏拉圖對于藝術活動的真知灼見,這些思想都深深地影響著以后審美心理學以及創作心理學的作家們。
柏拉圖在其“靈感”說中肯定了理性與感性在藝術創作中的位置和作用,尤其是突出了感性的獨特價值。同時,我們要在柏拉圖的整體思想上來理解靈感問題,以及柏拉圖對藝術家的態度問題。因此,柏拉圖的“靈感”說,雖說著重論述了創作來源的問題,然而文學本身的錯綜復雜性使這個命題具有了更為廣泛的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西方美學家論美和美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2]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