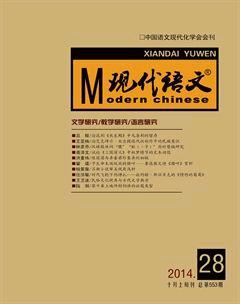論白居易“中隱”思想的形成
摘 要:“中隱”是白居易晚年所持的重要思想,對他的生活實踐和文學創作都有深刻影響。它的正式形成以唐文宗大和三年白居易寫下《中隱》詩為標志。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而是經歷了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它與白居易的仕途經歷有著密切的聯系。
關鍵詞:白居易 中隱 思想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白居易罷刑部侍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他真正遠離了當時的政治中心長安,直到會昌六年(846)去世,他除了大和九年曾短暫到下邽小住外,再也沒有離開過洛陽。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寫下了《中隱》詩,宣告了“中隱”思想的正式形成。
白居易《中隱》詩曰:
大隱隱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做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1](P1765)
不難看出,“中隱”是白居易深思熟慮后的有意識的主動選擇。他認為“大隱”與“小隱”都有所欠缺,最終走向了“中隱”。這實際上是白居易在經歷宦海浮沉之后,對于仕宦方式的一種深刻思考與選擇。它的形成不是偶然而是有一個過程。
貞元二十一年,白居易三十四歲,正在長安任秘書省校書郎。這年正月,德宗駕崩,順宗即位。二月十一日,韋執誼拜相。二月十九日,白居易即上書韋執誼(《為人上宰相書》),從這封書中見出白居易對韋執誼的仰慕和期望。韋執誼引用王叔文等,實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舉措,這即是被一些學者稱為的“永貞革新”。不過八月順宗內禪,憲宗即位,“二王八司馬”相繼貶出,韋執誼也被貶為崖州司馬。面對這樣的政治變故,白居易非常震驚,他的《寄隱者》詩就作于此時: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私怪問道旁,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祿厚食萬錢,恩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草,中有歸山路,歸去臥云人,謀身計非誤。[1](P128)
雖然他并沒有像詩中所說的那樣真的遠離政治,但這次事件必定給他心理上留下了一層陰影。他本年還有《感時》詩:
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將至。白發雖未生,朱顏已先悴。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雖有七十期,十人無一二。今我猶未悟,往往不適意。胡為方寸間,不貯浩然氣?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所以達人心,外物不能累。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斯言勝金玉,佩服無失墜。[1](P452)
比較這兩首詩,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白居易內心深處對仕宦的一些感悟。
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應制舉,入第四等,授盩厔尉。二年秋,由盩厔尉調京兆府進士考官,試畢,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招入翰林,授翰林學士。三年四月,除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可以說這一時期白居易的仕途是非常順利的。他在政治上也呈現出積極進取的姿態,所謂“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歌詠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2](P2792)這里的“歌詠”,指的應該是他的諷諭詩創作。他寫這些諷諭詩,目的在于“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2](P2792)。但是,這些諷諭詩同時也給他帶來了很多非議,“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茍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2](P2792)。可見,當時白居易面臨著相當大的輿論壓力。所謂“牛僧孺之戒”,指的應該是元和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登第。由于其策文言語激切,觸怒貴幸,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出為幕職。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王涯等坐貶。當時白居易擔任這次制舉的覆考官,可以說是親歷此事。元和五年還發生了一件事。這一年元稹由東都召還,途經華陰敷水驛,與中使劉士元為驛房發生了爭執,后元稹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曾上疏,極言元稹之不當貶,而疏入不報。這前前后后的一系列事件對于白居易的心理應該都有著不小的沖擊。
大約就在元和初,白居易對于禪宗思想的接觸逐漸多了起來。他文集中有《答戶部崔侍郎書》,云:“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2](P2806)崔侍郎即崔群。二人同在禁中的時間為元和二年十一月至元和六年。這里的“南宗心要”是洪州禪,洪州禪對白居易的思想影響很大,其“中隱”說的提出與之有密切關系,而白居易開始浸染洪州禪學,時間就在元和三年至六年間。這樣我們對于白居易這一時期作的一些詩就比較好理解了。他的《隱幾》詩,作于元和五年,詩云:
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既適又忘適,不知我是誰。百體如枯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四十心不動,吾今其庶幾。[1](P523)
詩中充滿了忘懷是非,身心兩遺的觀念。這里面有莊老思想,白居易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禪宗的因素。白居易的諷諭詩主要都是創作于元和前期,而從上面來看,即使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已經是比較復雜了。
元和十年六月,時任太子左贊善大夫的白居易首上疏請捕刺殺宰相武元衡之兇。宰相以宮官先臺諫言事,惡之,后忌之者又誣白居易母看花墜井死,而居易作《賞花》《新井》諸詩,有傷名教。八月,奏貶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復論不當治郡,追改江州司馬。這是白居易入仕以來遭受的最大打擊。
在貶江州司馬之前,白居易有《贈杓直》詩:
世路重祿位,恓恓者孔丘。人情愛年壽,夭死者顏淵。二人如何人,不奈命與天。我今信多幸,撫己愧前賢。己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況此知足外,別有所安焉。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外順世間法,內脫區中緣。進不厭朝市,退不戀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無不安。體非道引適,意無江湖閑。有興或飲酒,無事多掩關。寂靜夜深坐,安穩日高眠。秋不苦長夜,春不惜流年。委形老小外,忘懷生死間。昨日共君語,與余心膂然。此道不可道,因君聊強言。[1](P583)
詩中所謂“南宗禪”即是洪州禪,“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正說明白居易思想上正深受著洪州禪的影響。從他的《贈杓直》詩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這種新的“吏隱”觀非常的滿意和自足。不過很快到來的貶謫江州,使他明白這種新的“吏隱”也很難真正實現。政治上的風波過于險惡,若身在朝市稍有不慎即會傾覆,如今的貶謫即是明證。而隱于山林又如何呢?白居易有《江州司馬廳記》,云:“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茍有志于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2](P2732)但當時的州司馬是什么官呢,是“凡內外文武官坐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于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2](P2732)白居易所謂“有志于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之語很難讓人相信是他的真心話。《琵琶行》中言江州“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恐怕才是他的由衷之言。他的《中隱》詩中提到“小隱入丘樊”時也說“丘樊太冷落”。可見,處于低位、居于山林也不是白居易所希望的。不過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白居易的確已經有了“吏隱”之念,只是對于如何“隱”,他似乎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和方法。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白居易由江州司馬遷忠州刺史。十四年春,自江州啟程赴忠州。在路上他寫了一些詩歌,詩中避禍全身之意非常明顯。
元和十五年白居易由忠州召還,此后官職頻遷,至穆宗長慶元年十月即轉中書舍人。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除杭州刺史。白居易此次是主動請求外放,原因在于一方面成德軍牙將王廷湊殺節度使叛,唐軍十余萬討之,久無功,而白居易上書論用兵事,皆不聽。另一方面是朝中朋黨傾軋,兩河再亂,國事日荒。白居易不愿身陷其中,乃求外任。在論到白居易身居朝中之尷尬時,陳寅恪有一種觀點,他說:“蓋樂天既以家世姻戚科舉氣類之關系,不能不隸屬牛黨。而處于當日牛黨與李黨互相仇恨之際,欲求脫身于世網,自非取消積極之態度不可也。”[3](P330)所以我們看這個時候白居易實際上已經是在有意識的選擇一條他認為最合適的仕宦之徑了。
長慶四年五月,白居易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敬宗寶歷元年三月,除蘇州刺史。二年五月,以眼病肺傷請假百日,九月,假滿免郡事,后返洛陽。文宗大和元年三月,征為秘書監,二年二月,除刑部侍郎。十二月,乞假百日。三年三月末,假滿,罷刑部侍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返洛陽。本年,作《中隱》詩,標志著“中隱”思想正式形成了。
我們看白居易《中隱》詩,很明顯可以感受到它特別注重的是人生的少憂患和豐富的物質享受,所謂“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這是白居易在重新修正了他的吏隱觀后形成的一種思想和作出的選擇。從政治上來講,他遠離了喧囂的朝市,避免了“貴則多憂患”;從經濟上來講,他遠離了冷落的丘樊,避免了“賤則苦凍餒”。這可以說是真正獲得了身心俱適。“個體身心的自由適意是中隱的中心目標;社會義務和責任雖然未被徹底拋棄,但已處于服從前者的地位。”[4](P115)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白居易《中隱》詩中表現出來的自我享樂之唯恐不足:“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這是他“中隱”思想最明確的體現。
白居易的“中隱”思想在他的生活實踐和文學實踐中都得到了明顯的體現,這在開成三年他所作《醉吟先生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礨,次開詩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童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數十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后已。……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余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后賦釀者不與焉。[2](P3758)
白居易不厭其煩地敘述著他的居洛生活,顯示出他對這種生活的主動追求和喜愛。不過白居易“中隱”思想的意義還不僅在于此,而是同時在于他在東都的時候和很多人都有唱和,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詩歌創作群體,白居易在其中的位置又相當重要,因此這些詩人也相應地受到其影響。這樣,伴隨著“中隱”思想的傳播,白居易的詩歌也相應地在這一群體中得以流傳。當然,這應當是接下來繼續研究的問題,非本文所涉及的了。
注釋:
[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3]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董超 陜西延安大學西安創新學院中文系 7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