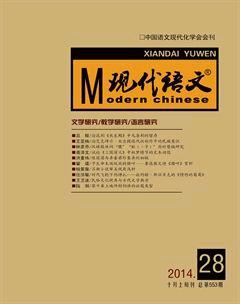《屬羊女》地域民俗文化意蘊研究
孫淑芹+李彥麗
摘 要:吉林延邊本土作家于雷創作的《屬羊女》展示了一定生態基礎上具有濃郁滿族及滿漢融合文化特色的東北地域民俗文化。小說運用東北豐富生動的民間話語展示了滿族薩滿文化中對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同時又對東北歲時習俗的民俗事象進行了描寫,并且塑造了一些東北典型人物形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審美空間。
關鍵詞:《屬羊女》 東北地域 民俗文化 滿漢融合
東北是滿族的發祥地,在東北的山川村落都留有滿族文化的印記,同時,東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漢、滿、蒙、朝等民族雜居的社會現實,各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形成了獨特的東北地域文化。延邊作家于雷創作的《屬羊女》就展示了一定生態基礎上具有濃郁滿族及滿漢融合文化特色的東北地域民俗文化。
一、滿族薩滿文化的展現
滿族宗教信仰多元化,但主要以薩滿教為主,他們相信萬物有靈,對神靈敬畏與崇拜,因此形成了祈求神靈的各種祭祀活動,跳神就是其中的一種。薩滿教的神職人員被稱為薩滿,是人與神靈之間的使者,薩滿分家神和大神兩類,在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是大神。我們所熟知的“跳大神”就是巫嫗通過舞蹈和“神歌神詞”來消災降福。“跳神”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寄托,也是小鎮人長期信仰薩滿的的自然表露。康大頭病得奄奄一息,小鎮人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跳神”。和蕭紅《呼蘭河傳》中描寫的跳神一樣,《屬羊女》中的跳神也是一幕丑劇與鬧劇。蝲蛄鎮的神職人員大腳仙和賴嚎子裝腔作勢,頭上搭著紅布,全身抽搐搖擺,腰間的鐵腰鈴當當作響,口中更是念念有詞。愚昧的小鎮人絲毫不顧及躺在炕上倒氣的康大頭,而是完全沉浸在看熱鬧的喜悅中。大腳仙和賴嚎子正是利用了人們對“跳神”的“誠意”與“虔誠”,不時抓住時機抽抽顛顛地下神,用拙劣的把戲對抗現代文明與進步。“跳神”體現了滿族人對自然的崇拜。
“信奉薩滿教的滿族人向來都有尊敬長者嚴教后代的風俗,特別是由于靈魂不滅的觀念,各氏族都將自己的祖先奉為神明,或木刻偶像,或彩繪想象中的先祖影像供奉在西條炕上方的祖宗板上。”[1]這種祭祖形式就是“上影”。《屬羊女》較為細致地描寫了關家正月“上影”的儀式。“上影”是滿族傳統中“辦族譜”的簡化。傳統的“辦族譜”必須嚴格經過接譜、亮譜、續譜、宰牲、收譜五個程序,小鎮經歷了幾百年漢文化的沖擊,上影的形式不再那么嚴格,盡管如此,我們在文中還是能夠領略滿族旗人祭祖的虔誠和隆重。上影時的族譜最上端是有如仙人般飄逸的祖宗影像,下面是一代又一代祖先的名字,關老爺子帶領關氏一族分長幼尊卑站好,向祖宗影像叩拜。“上影”體現了滿族人強烈的家族觀念和祖先崇拜思想。
在這里,跳神和上影已成為一種有著特定意義、相對獨立的儀式,表現了東北人的共同情感和價值認同,甚至是集體無意識。透過這些獨特的符號表意系統,于雷發掘了巨大的歷史文化意蘊。
二、東北歲時習俗的表現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因素,使居住在白山黑水間的東北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風俗,而日常生活、歲時節日及婚喪嫁娶等民俗事象的描寫,表現了濃郁的鄉土情蘊,體現出東北民俗文化的動人之處。
東北人民用黑土地賜予的智慧和食物為每一個傳統節日賦予了鮮明色彩,讀《屬羊女》,讀者會充分感受到異樣的文化內蘊。臘月二十三小年,家家都會殺年豬,灌血腸,而親朋好友之間互贈殺豬菜已經成了小鎮人的保留習慣。過了小年兒,女人們忙著蒸面點,包凍餃子、包粘豆包。到了年三十兒,人們還要忙著迎灶王爺、上影。五月節時,小鎮家家屋檐插上一排排的艾蒿,姑娘們縫針線荷包,扎小笤帚,圖個辟邪免災:《屬羊女》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生動的東北民俗傳統文化。
東北的冬天寒冷而漫長,所以“貓冬”成了東北黑土地上的一種特殊習俗。貓冬——多么愜意溫暖的字眼。大雪封山,人們像靠著火爐蜷縮著取暖的貓一樣,在東北方言中“貓”也有“藏”的意思——藏在屋里熱炕頭上,打牌,摸紙牌,吸自制的土煙,抓“嘎拉哈”——由此形成具有東北特色的“火炕文化”。東北森林茂密,滿族人還有游獵打圍的傳統,蝲蛄鎮的男人大多都是狩獵高手。狩獵雖然會收獲很多美味的野物,但也很危險,何大林就死于一次圍獵。《屬羊女》真實地再現了東北林區人們的原生態生活。
除此之外,《屬羊女》還為讀者描畫了生動傳神的婚喪習俗。關玉河的婚禮完全是遵照關老爺子的指示按照舊禮熱熱鬧鬧辦的,“新娘的炕席底下放上蔥和松明子,這才聰明,再撒點芝麻、高粱,能節節高,撂把斧子,輩輩福。”[2]而小鎮最長壽的老人關老爺子去世后的葬禮辦得非常隆重。關老爺子下葬時,黃布遮著刺眼的陽光防止返陽,給其開光認準陰間的路,當聽見“左躲釘,右躲釘”時,關老爺子壽終正寢了。于雷從文化與地域的角度表現社會生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審美空間。
三、東北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當年因為馬車店店主用一碗蝲蛄豆腐救了清始祖布庫里·雍順的命,所以乾隆爺將蝲蛄鎮冊封為清始祖發祥地,并遷來了三百戶旗人。蝲蛄鎮位于長白林區深處的偏遠鄉村,與世隔絕了幾百年,解放后才進入人們的視野,小鎮人封建保守思想嚴重,對新事物本能地排斥。縣婦救會在蝲蛄鎮進行婦女解放運動,想拆除代表封建思想的郎氏貞節牌坊,幾個郎姓老太太在那整整守了三天三夜,還大罵“傷天害理”。關連山作為小鎮的區長,想破除封建迷信,可關老爺子卻翹著小辮子到處跑,還親自或者煽動別人搞封建迷信活動。而裝神弄鬼的大腳仙和賴嚎子,則為了一己私利制造謠言,阻擋文明的進入。
東北偏居一隅,地理環境開闊,自然資源豐富,形成了東北人寬容大度、不斤斤計較的性格特征,民風質樸。關連山和何大林就是其中的典型。關連山作為小鎮的權威人物,卻難改粗人本性,遇到不滿或棘手的問題,總要大聲嚷嚷幾句“扯不扯呢”。他語言雖然粗俗,但并不粗鄙,為人剛正不阿。何大林作為狩獵高手,體現了山民的威武和抗爭意識,以及東北人的信守承諾和耿直講義氣。東北民眾面對嚴酷的自然生存環境和社會壓迫通常表現出執著的生命意識和倔強的生命力量,體現出一種心理上的強悍,這一點從陶曼與蘇小石的愛情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現。同時,東北這塊“化外之地”較少受到中原封建傳統禮教影響,女子表現更多的是野性潑辣、大膽奔放。“大花碗”是小鎮公認的“有名兒的潑娘兒們”[3],郭惠娟身上則浸透著原始的奔放與野性,敢愛敢恨,不離不棄。在于雷筆下,很多形象被理想化了,表現了作者對生于斯長于斯的東北黑土地的熱愛。
四、豐富生動的東北民間話語的運用
一個地域的民俗文化,也可以通過語言體現出來。于雷從小生活在東北,耳濡目染了東北原生態的生活和語言,因此,作家在創作時能自覺運用方言這一民間話語資源,既具有濃郁的地域色彩,又形成了作家自己的個性風格。
首先,東北方言形象生動,具有特殊的表現力。如關連山說何大疤瘌眼子“別他媽的叨木鸛子找食——靠嘴兒,把能耐得真使出來,扯不扯。”[4]關老爺子反對關連山封“藥王廟”和“娘娘廟”,在廟前嚎叫,關連山要拿槍崩了他,“嚇得他一鼓肚子,把個紅褲腰帶掙斷了,縫著白褲腰的黑夾褲差點沒禿嚕到腳跟兒。”[5]其次,東北方言還表現人物的個性化特點。當馬大哈哈問關秧歌兒到醫院來干什么,關秧歌兒露出了無賴相:“俺屁股上扎根刺,俺想……”面對關秧歌兒的挑逗,郭惠娟一把拉住關秧歌兒的褲帶往床上拽:“來,姑奶奶給你挑(刺),你把褲子脫下來,脫!”[6]再如關老爺子:“狗日的,南蠻子,想在這兒扎根兒,還敢把房子蓋到最東頭擺浪!這不明明貶弄咱們臭糜子嗎?關連山,臭小子還幫狗吃食,哎呀天哪,這些敗家的子孫,咋都這樣不著調哇……”[7]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我們可以從《屬羊女》的字里行間傾聽到久違的鄉土鄉音,觸摸到尚未走遠的民風民俗,給人一種本色自然、原汁原味的感覺。第三,自覺的鄉土意識,使作家從文化層面關注東北生活,運用多種修辭手法開拓出藝術的新境界。如:“人們在為陶曼沸騰著,舌頭像一把把燒紅的柔軟的劍,伸進了小鎮那條狗腸子一樣的小街。”[8]“傍年根兒的夜晚總是黑黑的,月牙兒不等太陽落山時,就先溜到山下面去享福,撇下那些星星像沒娘的孩子一樣眨著眼睛,窺視著奇特的大地。”[9]“車站里,火車像得了齁嘍病,大口大口的喘著。”[10]簡單明了的語言,卻傳達出作者深厚的感情,傳達出濃濃的詩意。
東北這片土地上聚集了多個少數民族,其中滿族居多。滿族與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在交往過程中相互借鑒和吸收言語詞匯。滿語具有純樸、直觀、形象、生動等特點,反映了滿族作為狩獵民族的民族特征。正是因為滿語的精當凝練,富有親和力,才使得漢族及其他生活在一起的民族更容易接受它,一些滿語直接融入到東北日常方言中,并得以傳承下去,形成了語言融合現象。如大寶才介紹馬大哈哈時“馬大哈哈是個江湖牙醫,也會扎古點兒其他的小病”[11]。這里的“扎古”就出自滿語,是“診治”的意思。再如“抓嘎拉哈”,“抓”在滿語中應讀“chuǎ”,是指把散落的東西撿起來,“嘎拉哈”是羊或豬的膝蓋骨,“抓嘎拉哈”是舊時東北小女孩的玩具。其他如“旮旯”“寒磣”“邪虎”“邋遢”“啰嗦”“禿魯”等也都來自滿語,且按照滿語的意思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詞語都是在民族交往過程中形成的語言的產物,它們早已悄無聲息地融入東北的日常生活,《屬羊女》體現了語言的融合性特點。
于雷有著深厚的鄉土意識和鄉土情結,鄉音、鄉民、鄉土、鄉情深深地烙在作家心中,并在作家筆下構成了一個個詩意的家園,作家始終關注充滿苦難與深情的滿族龍脈地,也正因如此,地域民俗文化成為《屬羊女》的重要文化元素。
注釋:
[1]尹郁山:《吉林滿俗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頁。
[2][3][4][5][6][7][8][9][10][11]于雷:《屬羊女》,延邊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頁,第22頁,第171頁,第7頁,第54頁,第251頁,第314頁,第66頁,第28頁,第38-39頁。
(孫淑芹,李彥麗 吉林延吉 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 13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