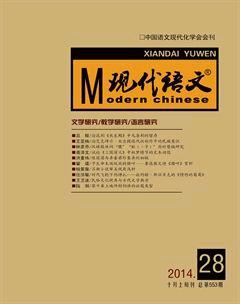人生如夢
摘 要:19世紀(jì)末老紐約的習(xí)俗,在《天真時代》中得以生動的展現(xiàn)。它造成了令人扼腕嘆息的愛情悲劇,同時也探索了走出痛苦的道路。評論界多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fā),關(guān)注其中受壓迫的女性角色,極少從哲學(xué)層面予以解讀。本文從叔本華的悲劇理論出發(fā),勾勒女主人公人生悲劇的解脫之道。
關(guān)鍵詞:悲劇 欲望 痛苦 意志
伊迪斯·華頓的代表作《天真時代》,榮獲美國普利策小說獎,其作品以老紐約上流社會為背景,揭示其風(fēng)俗習(xí)慣,并以細(xì)膩的筆觸剖析家庭、人性、倫理、婚姻,展示了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的社會風(fēng)貌。
《天真時代》中的男主人公阿切爾陷入一場愛情困境:與剛從歐洲歸來的埃倫相愛,卻又與她的表妹梅·韋蘭訂婚、結(jié)婚,最終有情人也未能成為眷屬。在他們所處的時代,上流社會相當(dāng)保守。阿切爾與埃倫迫于世俗的壓力,還是各奔東西。其間,盡管埃倫并不畏懼保守的家族勢力,但她的善良本性不容許她去破壞別人的家庭,因而遠(yuǎn)離紐約,定居于巴黎。她的愛情雖然破滅了,但始終沒有向自己卑劣的丈夫妥協(xié)。時隔將近三十年之后,她丈夫已去世,可是她仍然保持了自己既有的生活方式。這時的她,顯然已經(jīng)看透了人生:放下各種欲望,脫離世事的牽絆與苦惱。然而,將近三十年的平靜,何嘗不是一種幸福呢?評論界對這部小說多從女性主義角度進(jìn)行解讀,探討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及女性追求自由的斗爭,本文則采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對這部小說進(jìn)行解讀,以揭示人生的本質(zhì)。
一、引言
叔本華將非理性哲學(xué)的意志確立為哲學(xué)與美學(xué)的本體,認(rèn)為意志也是悲劇的本體。由于意志的存在,人生就出現(xiàn)多種欲望,這些欲望又是盲目的。欲望一旦得到滿足,就會產(chǎn)生下一個欲望。更為可怕的是,欲望得到滿足會覺得無聊,得不到滿足就會感到痛苦。痛苦與無聊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貫穿于人的一生。王國維也指出生活因欲而至痛苦的本質(zhì):生活之本質(zhì)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狀態(tài),苦痛是也!……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而一矣![1]因而,如何面對人生的苦痛,成為古今中外無數(shù)賢哲不斷思考的問題。叔本華認(rèn)為必須否定生命的意志,才能達(dá)到對人生的靜觀,這樣才會擺脫煩惱與痛苦。“生命意志的否定,就是把欲求的千百條繩索,作為貪心、恐懼、嫉妒、盛怒,在不斷的痛苦中來回簸弄我們的繩索,統(tǒng)統(tǒng)都割斷了。”[2]所以,若能夠領(lǐng)悟到這一點(diǎn),生的痛苦自然也就消失了。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指出,得以解脫的情況又分為兩種:“一存于觀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覺自己之苦痛。”當(dāng)一個人目睹了他人所受之痛苦,領(lǐng)略到宇宙人生的本質(zhì),感受到苦痛與意志如影隨形,之后能夠放下自己的欲求,達(dá)到精神的解脫,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一個人不斷地為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奮斗,又不斷地遭到挫敗,直至絕望,那他最后也就否定了生命的意志,這種解脫也是頗為悲壯的。
叔本華認(rèn)為:“對于悲劇來說,只有表現(xiàn)大不幸才是重要的。”[3](P347)他將不幸的來源分為三種:一是壞人的挑撥或惡行,二是盲目的命運(yùn)所釀成,三是由于悲劇中人物所處的地位關(guān)系所造成的。第三類被王國維認(rèn)為是“悲劇中之悲劇”,因為人們在正常情況下,互相對立,但又并非惡意而制造的悲劇最讓人痛苦。
二、“剪不斷,理還亂”
埃倫從歐洲歸來,希望能夠得到自己家族的支持,與齷齪的丈夫離婚,不料卻在上流社會引起了非議。阿切爾,作為一個思維超脫于傳統(tǒng)的年輕人,盡力去幫助埃倫緩解尷尬的處境。作為一種手段,他與埃倫的表妹梅訂婚了,從而不自覺地為自己將來的愛情之路設(shè)置了一個巨大的障礙。埃倫的率真與坦蕩打動了阿切爾,同時她也為阿切爾的與眾不同所吸引。可是,畢竟兩人都承擔(dān)著自己將要面臨的家庭責(zé)任,在忍受著巨大痛苦的情況下,這對情侶只能勞燕分飛。
人生的欲望是盲目的,阿切爾自然也不例外。埃倫第一次在公共場合公開亮相,是在劇院看演出。可是,因為她的衣著的肩部和胸部露出的部分比當(dāng)?shù)亓?xí)俗略多了一些,就引起了不滿,并且有人認(rèn)為她是不甘寂寞,所以來看演出。阿切爾看不慣眾人羞辱她,就決定宣布與梅訂婚,希望借此能夠證明埃倫此行并非隨性而來,而是必須參與家族的事務(wù)。毫無疑問,他的做法會起到相當(dāng)?shù)淖饔谩H欢伺e也把自己逼進(jìn)了死胡同。某種程度上,他的訂婚滿足了紐約社交界的期待與家族的要求,但這都是出于外界的“壓力”,阿切爾并不真正了解梅,更談不上愛慕。梅的可愛之處,也只能是她符合老紐約對女性的各種行為規(guī)范的要求。因而,盲目的欲望也使他一度陷入極度痛苦之中。
曾見過埃倫丈夫的人這樣評價他:“老喝的半醉,蒼白的面孔上露出譏笑……,我來告訴你他那德行: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據(jù)我所知,他對兩者都不惜任何代價。”[4](P13)與這樣的丈夫在一起生活,何談幸福?埃倫希望離婚,就常理而論,并無不當(dāng)之處。紐約上流社會的風(fēng)俗確實是絕對不允許的,他們所關(guān)注的是埃倫的行為是否符合他們的標(biāo)準(zhǔn),女性離婚就有損自己家族的榮譽(yù)。從中外的傳統(tǒng)來看,女性離婚的確是社會的一種禁忌,不少文化中甚至更極端。但是當(dāng)時整個社會就是那種氛圍,所以也不能認(rèn)為反對埃倫決定的人就是邪惡的,他們也不過是按照通常的社會倫理道德作評價。這樣一來,就是兩種善的力量的對立與沖突,造就了阿切爾與埃倫“一種相思,兩處閑愁”的悲劇,也可謂“悲劇中之悲劇”。
埃倫之所以放棄自己的訴求,完全源于她對戀人的愛與善良的本性。她曾很明確地告訴阿切爾,她放棄離婚并非為了婚姻的尊嚴(yán),也不是害怕在別人眼中淪為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為了家庭避免輿論、避免丑聞,必須自我犧牲,我才放棄了嗎?因為我的家庭即將變成你的家庭——為了你和梅的關(guān)系——我按你說的做了,按你向我指明應(yīng)當(dāng)做的做了。她突然爆發(fā)出一陣笑聲。我可沒有隱瞞:我是為了你才這樣做的!”[4](P148)她是不畏懼任何勢力阻擾她獲取幸福的,而當(dāng)自己的戀人充當(dāng)家族的說客勸她不要離婚時,她還能指望什么呢?如果將她視為一個戰(zhàn)士,那她絕對稱得上是一員虎將。可是面對自己人時,她就不知所措,“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梅和阿切爾只是訂婚,并非沒有一點(diǎn)兒回旋的余地。假如她奮力一搏,把阿切爾爭取過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幾百年前,羅密歐與朱麗葉都敢做的事,憑什么她不能呢?“愛之愈深,情之愈切”,她不希望自己成為阿切爾人生的包袱。對于自己而言,即使被家族遺棄也無所謂,可是她不希望連累自己的至愛。毫無疑問,刻骨銘心的痛是她長時間都揮之不去的。非理性的欲望就是這樣折磨她,她也只能默默地承受。
在阿切爾眼中,埃倫這位貴族少婦為人坦率,不拘世俗,老紐約的風(fēng)俗人情卻是充滿了世故與圓滑。“她身上卻散發(fā)著一種美的神秘的力量,在她毫無做作的舉目顧盼之間有一種自信,他覺得那是經(jīng)過高度訓(xùn)練養(yǎng)成的,并且充滿一種自覺的力量。同時,她的舉止比在場大多數(shù)夫人小姐都純樸。”[4](P53)這在埃倫對客廳的裝飾中也有所體現(xiàn),桌椅擺放得極為講究,花瓶里插著紅玫瑰。而她所讀的書,保羅·布爾熱,休斯曼和龔古爾兄弟的書,都是浪漫主義或現(xiàn)實主義作品,可以看出她是力圖探尋生活的本來面目的人。這樣,在阿切爾眼里,“經(jīng)過高度訓(xùn)練”也就不足為奇了。相比之下,梅所表露出來的人格特質(zhì)恰恰相反。“所有這些坦率與天真只不過是人為的產(chǎn)物。未經(jīng)馴化的人性是不坦率,不天真的,而是出自本能的狡猾,充滿了怪僻與防范。他感到自己就受到這種人造的假純潔的折磨。”[4](P39)這是在他仔細(xì)剖析了梅的性格之后得到的結(jié)論。梅自然很善于利用各種社會關(guān)系,借以向阿切爾和艾倫施壓,率真的艾倫又怎么能是她的對手呢?梅所做的每一件事,又都是以上流社會的規(guī)范為依據(jù)的,無可挑剔。任何人也不能否認(rèn)一位女性按照社會所認(rèn)可的倫理追求自己幸福的權(quán)力,她的所作所為也不應(yīng)該受到指責(zé)。在明知自己未婚夫移情別戀時,卻不能拍案而起,據(jù)理力爭,因而她也是那種特殊社會風(fēng)俗的受害者。這也是埃倫與阿切爾愛情悲劇最令人心痛又扣人心弦之處,也注定了埃倫最后必然再次選擇放棄阿切爾的追求。
身為不幸婚姻的受害者,雖然具有悲劇英雄的氣概,卻在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中不能施展自己的抗?fàn)幰庠浮o法解脫與自己的丈夫的婚姻關(guān)系,更不能與心儀的男人長相廝守,同時還遭到世俗的壓力,卻無人愿意去傾聽她精神上所忍受的痛苦。她盡管也堅持過,但終究還是妥協(xié)了。人生的欲求無以滿足,接連挫敗,對一位少婦而言,這種打擊過于沉重了!
三、道不同,不相為謀
梅疑似“懷孕”的消息,促使埃倫下定決心離開紐約這個傷心之地。但是,她還是堅持了離開自己的丈夫,選擇定居巴黎,而非回“家”。在阿切爾婚后的一年半中,她逐漸理解了這個小圈子,明白自己與它是格格不入的,“經(jīng)歷了最初的新奇興奮之后,她發(fā)現(xiàn)自己——像她說的——是那么‘格格不入,她無法喜歡紐約喜歡的事情。”[4](P208)生活中雖有許多高雅的樂趣,但要想得到,就必須付出巨大的“艱辛與屈辱”。埃倫此時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與其呆在紐約與阿切爾糾纏不清,受人誹謗,還不如遠(yuǎn)離是非之地,一個人去過平靜的生活。
歌劇《浮士德》在書中反復(fù)出現(xiàn),這也正是男女主人公所面臨的艱難抉擇。浮士德難題也是困擾整個人類永恒的難題:“怎樣使個人欲望的自由發(fā)展同接受社會和個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約束協(xié)調(diào)一致起來——怎樣謀取個人幸福而不出賣個人的靈魂”[5]阿切爾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恪守自己做丈夫和父親的責(zé)任,因而家庭是“美滿”的。與此同時,他積極參與各項社會活動,成為執(zhí)政當(dāng)局眼中的“好公民”。可是,他本人的行為始終都是循規(guī)蹈矩的。像他這樣出身顯赫的人,也僅僅是處于墨守成規(guī)的水平。但是,在社會的發(fā)展進(jìn)程中,他是有責(zé)任與義務(wù)去引領(lǐng)社會的發(fā)展方向,以使整個社會習(xí)俗更加合乎人性情理。滑稽的是,社會己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卻沉溺于往昔的習(xí)俗之中不能自拔。盡管自己失去了“生命的花朵”,仍認(rèn)為“舊的生活方式也有它好的一面”。老紐約那一套家庭倫理觀已完全被拋棄,自己的兒子和曾經(jīng)被上流社會驅(qū)逐的博福特的女兒相戀,無疑也是對那種壓抑人性的家庭倫理觀的嘲諷。過去神圣的規(guī)則歸于虛無,這令生活于其中的阿切爾難以接受。“這壯觀的景象已擺在他面前了,當(dāng)他放眼觀看它的時候,卻感到自己畏縮了,過時了,不能適應(yīng)了,與曾經(jīng)夢想過的那種意志堅強(qiáng)的堂堂男兒相比,他變得渺小可悲……”[4](P309)甚至當(dāng)自己妻子過世,兒子安排他與埃倫會面,他仍然不敢面對。或許他為當(dāng)初自己的怯懦與“理性”感到慚愧,無顏面對所愛的人;或許他認(rèn)為舊有的風(fēng)俗還是比較好,自己應(yīng)當(dāng)至死堅守。無論如何,他都落伍了。
與阿切爾相比,埃倫在巴黎的日子顯然是自得而又愜意。關(guān)于埃倫的生活,書中并未正面闡述。但是從阿切爾兒子的話語中,可以得知她對博福特的女兒范妮很友好,帶著她在巴黎到處玩。她的生活方式在這三十年中沒有改變,盡管令她傷心的丈夫已經(jīng)過世。阿切爾的兒子是和父親一塊兒看望埃倫的,可是阿切爾卻沒有進(jìn)門。這時的埃倫也是知曉往日的情人到達(dá),她也沒有主動去迎接。她并不是回避,也沒有任何畏懼,只是順其自然。歷盡了人世的滄桑,酸甜苦辣皆已品嘗過,無怨無悔。這在她離開紐約前已深刻地表現(xiàn)了出來。在阿切爾婚后將近兩年時又提出與埃倫逃離紐約,到一個類似于愛情烏托邦的地方時,埃倫很敏銳地意識到了其虛無縹緲。她認(rèn)為希臘神話中的戈爾工已經(jīng)擠干了她的眼淚,“她也打開了我的眼界。說她弄瞎人們的眼睛那是一種誤解,恰恰相反——她把人們的眼瞼撐開,讓他們永遠(yuǎn)不能再回到清凈的黑暗中去。”[4](P253)總之,她在經(jīng)歷了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認(rèn)識到人生的虛無。此刻的眼界更開闊了,她已經(jīng)能夠達(dá)到對生命的靜觀。阿切爾仍然寄希望于埃倫能夠同意保持情人的關(guān)系,這怎么可能呢?“背著信賴他們的人尋歡作樂”,必將玷污愛情,也將侮辱他們的人格,埃倫絕不接受。她明確地告訴阿切爾,“你從來沒有超越那種境界,而我已經(jīng)超越了。”這些細(xì)節(jié)足以說明埃倫對于人生的看法業(yè)已發(fā)生根本的轉(zhuǎn)變:她不再留戀塵世的歡樂,不再對未來有明確的追求。
在這場愛情悲劇中,阿切爾本身并沒有受到多深的傷害。盡管沒有得到埃倫,他仍然擁有了“大家閨秀”梅做妻子,兒女的出生,也為這個家庭增添了一抹亮色。梅的品格完全符合當(dāng)時的社會要求,阿切爾對她也是滿意的。之所以與埃倫相戀,是因為埃倫身上率真、正直的品格補(bǔ)充了梅的一些不足,但也并非不可或缺。所以,在妻子過世后,他仍然放不下往日的世俗偏見。埃倫則不同,她從歐洲到紐約,幾乎是孤注一擲,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要離婚。這其中她究竟流過多少淚水,書中沒有正面交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個老紐約社會中的“入侵者”,她所受的委屈常人無法理解。如此之大不幸,使其放棄所有欲求,擺脫人生的痛苦,也是理所當(dāng)然的,這便是“覺自己之痛苦”而悲壯地獲得了解脫!
四、結(jié)語
即便身處“煙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xiāng)”,也必有夢醒的一天。人生就如一場夢一樣,只是一部分人在歷盡悲歡離合之后,能夠夢醒歸來。“說什么王權(quán)富貴,怕什么戒律清規(guī)”,到頭來終究都是一場空。無論“觀他人之痛”,還是“覺自己之痛苦”而放下欲望,否定生命的意志得以解脫的,都是幸運(yùn)的人!
注釋:
[1]王維玉:《王國維悲劇理論的哲學(xué)視界》,社科縱橫,2012年,第5期。
[2]蔚志建:《論叔本華的人類悲劇與藝術(shù)悲劇觀》,東岳論叢,2005年,第5期。
[3]朱光潛:《朱光潛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伊迪斯·華頓,趙興國,趙玲譯:《天真時代》,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
[5]傅守祥:《理性悲劇〈浮士德〉:人類靈魂與時代精神的發(fā)展史》,解放軍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2004年,第3期。
(張玉 湖南長沙 湖南大學(xué)外國語與國際教育學(xué)院 41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