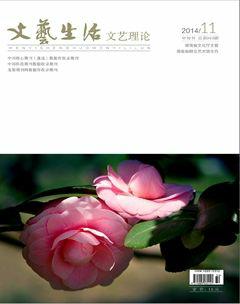評析賈平凹長篇新作《帶燈》的創作風格
劉靜
(包頭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35)
評析賈平凹長篇新作《帶燈》的創作風格
劉靜
(包頭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35)
《帶燈》是一部絕望與希望交織的小說,是一部理想與現實碰撞的英雄贊歌,它全面展示了城鎮化進程中中國鄉村世界的當代困境,但反過來它又通過對帶燈這個散發理想光芒的基層鄉鎮干部的人物塑造,表達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理想,并試圖為解決現階段我國鄉村世界中存在的困境探索一種新的出路。
賈平凹;帶燈;創作風格
賈平凹是當代文壇上少數同時擁有眾多作品以及龐大讀者群的作家。他的目光始終聚焦在中國農村,在創作過程中一直以來都未曾放棄過對中國傳統審美情趣的創作理念的追求,由此也就構成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
一、中國經驗的中國式敘寫
賈平凹在《帶燈》中沿襲了自己一貫創作風格的承襲,比如在敘事時間的處理,依然習慣于采用通過短時間幾個月或者一年來反映出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跨度;在文本方面,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同時在每個人身上都設置了獨特的性格以及位置;另外作者還承襲了自己最為擅長的細節敘事風格,也就是利用細致入微的生活觀察以及人物言行摹寫來反映出每一個人物的性格特征。而《帶燈》中作者創作風格上和之前差異最為顯著的一點就是改變了傳統經典的故事性講述,而采用絮語式的日常言說。著名學者韓魯華將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稱之為“中國經驗的中國式敘寫”。在小說中,賈平凹以帶燈為核心,從民間底層寫起,透過帶燈眼中的一件件小事和人物來看世界,用細節來推動敘事,通過大量的生活細節的描寫達到了在有限的時空中人文品質含蓄密集的效果。賈平凹始終堅持將目光專注在中國文學傳統,因而在《帶燈》中也打上了濃厚的中國本土化的印記,字里行間都流露著鮮明的中國氣派以及中國味道。比如在形形色色的上訪者中,其中有連續上訪多年的老上訪戶,也有無理取鬧者,竟然還有人充當上訪代理。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李雪蓮,其為了一個既成事實,堅持上訪長達二十年,但是無論是縣里還是市里的領導干部,均將其當做一件非常頭疼的大事來看待,每年都出動警力對其圍追堵截,這些令讀者看似好笑、荒唐的語言行為卻又流露出濃厚的中國特色,折射出當今社會上屢見不鮮的“上訪”問題。
王后生是《帶燈》中一位關鍵的上訪者角色。和其他上訪者相比,王后生有頭腦,會根據情況采取一定的計謀,比如他曾拿著蛇把書記堵在辦公室,也曾經在民間四處散布謠言,以達到煽風點火的目的,但與此同時他也非常善于幫助或者煽動別人上訪,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也或多或少的能得到一些利益,也因此他成為最令鎮政府頭痛的上訪者。在小說的“折磨”章節中,鎮政府工作人員最后實在無法忍受而對王后生下了最后通牒,通過多種途徑威逼其交出上訪材料,并成功的控制了王后生以及其他上訪者。一直以來,中國都不缺乏像王后生這樣的農民,他們即讓人有咬牙切齒的痛恨,但與此同時又不免讓從心中生出些許憐憫,所以作者僅僅是以王后生為載體,折射除了千千萬萬像王后生一樣,即狡猾、聰明但同時卻又可憐可悲的阿Q式的我們的中國農民。農民這個隊伍實在是龐雜混亂肆虐無信,對于他們所能夠起到約束作用的也無非只有現實的生存以及后代的依靠。對于帶燈而言,她受過良好的知識教育,寧愿放棄城市的生活而來到鄉村“受苦”,其很大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心中鄉村的田園圖景抱有憧憬及幻想,在她心中農民是淳樸與善良的。然而隨著工作的不斷開展,她卻深深的認識到了農民丑陋的另外一面,于是她心生失望,但是她又不得不哀嘆:對于這些連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能夠得到滿足的貧苦農民,我們還能提出什么更多的要求呢?
二、被神化的現代女性形象
(一)人物的神圣性與虛幻性
帶燈的職位是鎮政府綜治辦主任,主要擔負的是農民們的上訪工作,對于領導而言,帶燈能力出眾,是得力的助手,對于農民而言,帶燈則是能夠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活“菩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帶燈一方面需要尊重在鄉鎮政府工作的領導,嚴格的執行上邊下達的所有政策、條令、任務以及指示,一旦出現差錯就只能受責挨訓被罰,而這些領導們卻一味的追權逐利,極力要跳出鄉鎮,希望自己能夠從科級升遷副處,不斷的向上司獻媚,不過一到鄉到村寨了,就可以大口吃肉喝酒,脾氣暴戾。另一方面,帶燈還需要面對農民們像污水一樣潑向她的所有的不滿、怨恨,雖然帶燈同情農民們地位低下,收入微薄,冷餐冷飲,但與此同時帶燈也明顯的看到農民們在這種環境中扭曲了,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弄虛作假,巴結上司。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認識到帶燈的可敬可親之處,和這些人相比她是高貴的、智慧的。即使整日身處于如此丑惡的環境中,帶燈卻能夠始終堅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在逼仄的環境中依舊毅然決然的服從內心的呼喚。
在小說的最后,帶燈在長期的精神折磨及身體的打擊下,最終患上了夜游癥,由此也走向了個體的瘋狂。但與此同時,櫻鎮卻飛來了在之前從未曾有過的巨大的螢火蟲陣。更為神奇的是,全部的螢火蟲都向帶燈飛去,散落在她的頭上、肩上以及衣服上。此時的帶燈就像圣潔的佛一樣,全身都散發出神圣的暈光。對于帶燈而言,這些螢火蟲陣實際上就是為她送行的挽歌,而她身上所帶有的一些虛幻色彩和神性,實際上也就是作者內心深處那片美好而神秘的鄉村家園,但是隨著帶燈的離去,實際上也就預示著這田園只能成為一去不復返的幻景,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作品的批判力度。
(二)政治理想和審美理想的統一表達
關于帶燈的人物形象的寓意,有人指出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是“政治倫理的困境與美學理想的終結”,所以主人公實際上充當了的是一個理想化的社會主義新人形,可以將其看作是“政治浪漫想象的產物”。但筆者認為,這并不全面。如果我們根據劉再復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來進行分析的話,不難看出,任何一個人的性格中實際上都蘊含著正反兩級,而如果從生物的進化理論來分析,人類一方面具有動物原始需求的動物性一極,但與此同時也具有超越動物性特征之上的社會性一極,只有如此才能夠真正形成“靈與肉”的。
三、書信的敘事結構
帶燈寫給元天亮28封信件是作品的一個重要線索,一方面其拉開了帶燈精神世界和現實生活之間存在的距離,真實的反映出了帶燈身上所具有的超越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整個小說現實敘事中的書信的穿插式結構實際上也大大的緩解了現實世界由于各種矛盾而帶來的壓力緊張感;對于讀者而言,這種敘事方式還能夠減輕文本由于生活言說而導致的瑣屑細碎以及缺少頭緒的閱讀疲勞。實際上,這28封信也是作者一直以來所慣于使用的主體意象型創作風格的一次反映。
采用書信的敘事結構,實際上是我國小說創作傳統處理技法的一種體現,也即是以虛見實,原因在于在這種寫實性的小說中,其中實際上蘊含了相當一部分的抒情性、空靈性以及漂浮性。在這種背景下,看似非常實在的寫信的情節,實際上屬于一個虛寫,其中暗含的是帶燈的超越,同時也是對痛苦現實生活的超越,更深層的意義還在于對這個世界當中最堅硬的東西同時也是最殘酷的東西所采取的一種優雅的超越。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虛寫”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容易帶有寫信者的主觀色彩。比如帶燈在信中對于元天亮的形象進行了明顯的夸大,對天元的相信、敬重以及依賴稍微有點過,對其賦予了某種信任和崇拜色彩。在這種情況下,兩人并無法保持一個現代性的平等對話,帶燈更沒有表達出自己從天亮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某些相異的看法,兩者之間實際上是一種單向的崇拜而非雙向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貶低了帶燈形象的現代性意義。
四、結語
小說《帶燈》中以極強的現實感,通過鄉鎮干部帶燈的所見所聞,描述了中國鄉村正在經歷的一種翻天覆地的變化及其對于農村各個階層的人們的內心所帶來的巨大波動。著力表現了在當代中國鄉村政治以及倫理人性不斷轉型的過程中,千千萬萬像帶燈一樣始終伴隨著社會的變革而成長的知識分子形象,表達了他們心中的理想與迷惘,他們堅強、隱忍,從而在逼仄的環境中放棄最基本的道德倫理。
[1]陳曉明.螢火蟲、幽靈化或如佛一樣——評賈平凹新作《帶燈》[J].當代作家評論,2013(03).
[2]汪政,曉華.失去記憶的故鄉——賈平凹筆下的鄉土中國[J].中國作家,2009(03).
I207.42
A
1005-5312(2014)32-0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