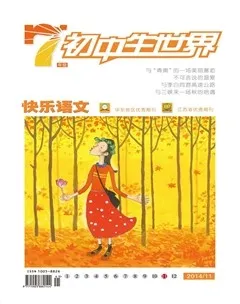不可言說的溫愛
谷新軍
茶峒是沈從文筆下的一座依山傍水、宛若仙境的小城。
“端午日,當地婦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了個王字。”“把飯吃過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鎖了門,全家出城到河邊看劃船。”“于是長潭換了新的花樣,水面各處是鴨子,同時各處有追趕鴨子的人。”“船和船的競賽,人和鴨子的競賽,直到天晚方能完事。”沈從文憑著對湘西端午民俗的細致觀察和深切感受,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茶峒人同慶端午的溫情畫卷。
然而在這幅畫卷里,有一些場景似乎有點異乎尋常。比賽前,“這一天軍官、稅官以及當地有身份的人,莫不在稅關前看熱鬧”;比賽后,“好事的軍人,當每次某一只船勝利時,必在水邊放些表示勝利慶祝的500響鞭炮”;賽船過后,“城中的戍軍長官,為了與民同樂,增加這個節日的愉快起見,便派兵士把30只綠頭長頸大雄鴨,頸脖上縛了紅布條子,放入河中,盡善于泅水的軍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趕鴨子”。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個湘西小城,軍官、稅官與百姓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那么對立緊張。這種官民和樂的場景,在當時的社會,在其他的文學作品中,是極少見的。
但是,《邊城》中這樣的場景卻不止這一處。
“這地方城中只駐扎一營由昔年綠營屯丁改編而成的戍兵,及五百家左右的住戶。……一營兵士駐扎老參將衙門,除了號兵每天上城吹號玩,使人知道這里還駐有軍隊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
“兩省接壤處,十余年來主持地方軍事的,注重在安戢保守,處置極其得法,并無變故發生。水陸商務既不至于受戰爭停頓,也不至于為土匪影響,一切莫不極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樂生。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發生別的死亡大變,為一種不幸所絆倒,覺得十分傷心外,中國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不會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
在“邊城”的世界里,沈從文有意識地消解了種種對立因素(兩種婚俗觀念的對立除外),既無階級對立,又無經濟利益上的沖突,更無人際關系間的矛盾,有的是慈愛孝順、恬靜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濟。這里雖有貧賤之分,富人卻樂善好施,如掌水碼頭的船總順順不因家境的富實而盛氣凌人,反而能夠常常體恤窮苦人,端午節送給老船夫鴨、粽子等。這里的各色人等均待人以誠,表現出仁厚、淳樸的民俗風情。作者筆下的“邊城” 世界,人性皆善,人性皆美,是一個充滿了“愛”與“美”的天國,瑰麗而溫馨。
然而,當時的社會現狀并非如此。茶峒地區原為歷史上犯人流放之地,偏僻、荒涼,苗族、土家族等在這里耕作,過著原始的、自由自在的牧歌生活。在20世紀20年代以后,封建軍閥、國民黨反動派在這里實行黑暗、罪惡的統治,殘酷鎮壓苗民起義,大肆屠殺無辜人民。
青少年時代的沈從文,經常目睹發生在家鄉的饑荒、暴亂與殺人越貨的情景。他從小就產生了非暴力抗惡的人性、人道主義思想,這些正是其創作的思想基礎。沈從文正是以充滿“美”與“愛”的“邊城”世界,表現他對至善至美的人情與寧靜和諧的理想境界的想象,以此對照黑暗、罪惡的現實社會,表達了他對當時湘西黑暗社會的批判。
其實,對人性進行謳歌與表現,是沈從文在創作中一以貫之的審美理想。他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這種廟供奉的是‘人性”。而且,沈從文把人性看成是美的至極,把它當作文學表現的終極理想,貫穿于自己20多年文學創作的始終。對筆下的人物,無論地主、紳士,還是農民、士兵、小業主等各類勞動者,沈從文都著力表現他們真、善、美的人性。正如他在《邊城》題記中所說:“對于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皆可以看出。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我動手寫他們時,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