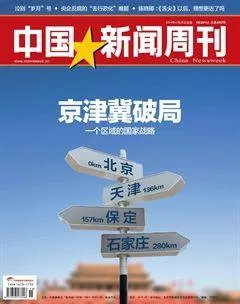“協同發展應以市場為主角”
王全寶

肖金成最近有點忙。他不僅要應付各路媒體采訪,并且不斷接到地方政府以及一些證券研究機構的邀請,讓其講解“京津冀”規劃對當地以及本行業的影響。
自從今年2月習近平主持京津冀協同發展座談會并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后,兩個月來,京津冀都市圈一體化成為社會熱議話題。
早在十年前,肖金成就參與了有關“京津冀”區域規劃的相關編制工作,并且給河北的石家莊、保定等城市以及北京都做過區域規劃。
4月21日,作為國內較早研究區域經濟發展的學者之一,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他認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根本問題仍然是市場和政府關系問題,應該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輻射范圍之爭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京津冀區域規劃,最早稱之為“京津冀都市圈”規劃,后又稱為“首都經濟圈”,今年中央強調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什么規劃名稱不斷發生變化?
肖金成:這是因為一直存在爭議。2006年,編制“十一五”規劃開始,國家發改委就將其定義為“京津冀都市圈”,但直到“十一五”末,“京津冀都市圈”規劃也沒有推出來。
2010年,開始啟動的“十二五”規劃,沒有再提“京津冀都市圈”這個名稱。2011年的全國兩會上,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京津冀都市圈”的概念被“首都經濟圈”的概念取而代之。
而在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中,與此相關的表述則是:“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打造首都經濟圈,推進河北沿海地區發展。”
名稱微妙變化的背后,實際上存在規劃范圍應該覆蓋多大的爭議。也就是“首都經濟圈”輻射范圍要多大?京津冀包括了河北全省,那么首都經濟圈是否包括河北全省呢?
“首都經濟圈”顧名思義,以北京為中心,向外輻射。但是北京輻射是有限的。所以范圍就存在了爭議。這個爭議有很長時間,輻射范圍無法確定,規劃就無法進行。
在爭議期間,河北一直非常積極希望將全省納入進來。2004年,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在廊坊召開了一個“2+7”的“京津冀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七個城市分別是:廊坊、張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島、滄州、保定。
會議過程中,河北提出意見:“石家莊不納入規劃是不行的”,所以后來就把石家莊加進來,形成“2+8”模式,即北京、天津加河北8個地級市,共同推出了一個合作宣言——《廊坊共識》。
我參加了《廊坊共識》的起草,其中列出了包括建立高層聯席會議制度、聯合設立協調機構、啟動京津冀區域發展總體規劃編制工作、在容易突破的領域開展合作等近十項舉措,可以說拉開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序幕,但后來的落實并不好。
當時提出“京津冀都市圈”規劃后,河北的邯鄲、邢臺、衡水三個城市并沒有納入進來,河北方面一直希望將這三個地區能納入進來,因此存在爭議。
“十二五”規劃中,國家發改委地區司就準備編制“首都經濟圈”規劃,但這個規劃到現在也沒有出來。
據我了解,在提出“首都經濟圈”后,天津方面也不太積極,但提出可以允許靠近的三個縣納入首都經濟圈。于是提出“1+3+6”模式,不包括石家莊和滄州,但河北又提出異議,因此圍繞范圍引起很多爭議。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沒有了首都經濟圈的概念,這樣爭議也就少了。
中國新聞周刊:既然在范圍上存在爭議,那么“京津冀一體化”多大為適宜呢?
肖金成:我個人認為,河北既可以受到北京、天津兩大城市輻射和帶動,同時也是這兩大都市的支撐。
另外,河北不能僅僅依賴北京、天津的輻射和帶動,因為河北區域太大,“首都經濟圈”不可能輻射整個河北。理論上可以說“首都經濟圈”輻射整個河北,但是實際上輻射不到全省,因此還需要新的城市來支撐。
新的城市我們指的是石家莊。京津冀應該有三大支點:即北京、天津、石家莊,因為石家莊可以把冀南地區輻射起來。
單靠北京能輻射多遠?最大也就是200公里,到不了秦皇島、石家莊以及冀南地區。
我很早就說,河北不能僅依靠北京、天津輻射,還需要新的中心出現,所以我們提出要變“雙城記”為“三城記”,這是我在2005年報告中就提出的。
都市圈形成的本質原因是大都市的輻射與帶動,其原動力是都市本身,其范圍大小取決于輻射力和帶動力,由內向外,由強到弱。
在中心城市的極化效應到一定程度后,產業要向外轉移,集聚—擴散—再集聚—再擴散,這是都市圈擴張的發展演化模式。
因此,石家莊自己要發展起來,在京津冀規劃中,決策層要在河北全域做文章,把石家莊要作為一個支點來考慮。
中國新聞周刊:京津冀規劃除了在范圍上有爭議之外,在產業布局上以往存在哪些問題?
肖金成:我在做京津冀相關規劃時發現,三省市產業未能發揮各自比較優勢。盡管京津冀各城市在經濟發展中有較強的互補性,但是在現有行政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下,各地區對經濟增長尤其是對產業發展都有很強的內在動力,過分追求與保護地方利益,追求自成體系的產業結構,使京津冀地區一直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產業分工與合作機制,地區間產業關聯比較弱,產業融合程度低,未能形成功能互補和各具優勢的產業結構。
比如,從北京天津河北制定的“十一五”規劃看,他們所確定的產業發展方向基本雷同,北京、天津市都以電子信息、機械制造、石油化工、鋼鐵旅游等行業作為主要產業。由于兩城市產業結構雷同,造成產業間惡性競爭,資源分散利用,產業無法做大、做強,也制約了北京天津的產業結構升級。
河北省各城市之間產業同構程度也很高。河北11個地方市工業總產值中位居前六位的行業多為能源、原材料產業。
此外,在區域合作中,受行政體制束縛的影響較大,在資源整合、產業鏈形成、信息溝通等方面缺乏相應機構予以指導,制約了產業合作發展。
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在推動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政府應該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
肖金成:不可否認,中央高層推動京津冀一體化意義重大。但是我認為,高層推動并不能解決阻礙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諸多復雜因素。我們要分清阻礙京津冀一體化緩慢的主要原因,分清是政府還是市場在起決定性作用。
在京津冀一體化問題上,政府應清有醒意識,政府應該把握好自己定位,在絕大多數微觀經濟事務決策上,應該充分發揮好市場的作用。
我認為,政府該推動三個地區所有城市之間實現交通一體化,打破行政區化對于基礎設施的壟斷,做好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應該制定戰略性產業規劃,尊重產業和城市發展規律;打破地區之間公共服務的界限,充分結合市場手段,而非單一行政手段推進京津冀的一體化。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實現京津冀一體化被上升為一個重大國家戰略,原因是什么?
肖金成:我認為有三大原因:首先,北京存在的問題確實很嚴重,這三大問題是,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人口膨脹。
2004年,我們參與了北京規劃修編,主要做空間布局研究。當時我們就提出到2020年,要按照2500萬人口承受力來規劃。
北京當時人口約是1400萬,但最后他們按照1800萬人口來規劃,結果到了2009年,北京人口就超過1900萬。這10年北京每年人口增長70萬,10年就是700萬,現實情況是北京很被動。
霧霾問題以及城市攤大餅式規劃引發的連鎖反應,這些問題靠北京自身已經無法解決了,所以再次提出京津冀都市規劃。
其次,北京、天津、河北三個地區之間差距問題。三個地區區域發展不協調,差距很大。河北發展了化工業、鋼鐵業,但GDP仍排在靠后位置,即使搞了這么多落后產業,河北經濟還是上不去,如果不搞呢?因此,合作是必然的,讓河北經濟發展上去。
第三,整體生態惡化問題,霧霾非常嚴重。不解決一體化問題,就會產生產業同構,都發展“三高一低”產業,環境會更加惡化。如果現在因為霧霾治理,要把河北6000萬噸的鋼產量減掉,那它的經濟就更差了,直接威脅到就業和基本公共服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讓河北產業發展上去。這些問題,都要放在京津冀協同的框架下去解決。

從這三個方面來講,一個是需要高層協調、另外要加快一體化,加強區域合作。但是就是因為合作問題沒解決,相互存在競爭,導致整體效益下降,效率降低。
強化頂層設計
中國新聞周刊:中央提出京津冀要協同發展,你認為該如何謀劃京津冀一體化頂層設計?
肖金成:我認為,京津冀一體化需要頂層設計。否則,爭議不斷,很難達成共識。
京津冀協同發展,我的理解是“攜起手來、共同發展”。所以,從頂層設計上要實現城市規劃的統一,要實現產業的對接協作,發展產業鏈條。
我想“協同”有兩層含義,即“協調”和“共同”之意。北京、天津、河北三個地區應加強溝通,實現經濟結構優勢互補,基礎設施共享共用,經濟政策協調統一,最終形成人口、產業的最佳空間結構。
現在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差距很大,特別是河北與京津之間的發展差距很大。讓河北發展起來,這應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
具體到頂層設計方面,我認為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各個城市之間要明確功能及分工。
比如:北京除政治、文化、國際交往的首都功能外,其余的都可以轉移出去;重點發展服務業,將制造業、石化、汽車、IT產業都轉移出去。天津發展高端產業,一般制造業也應該限制;北京、天津轉移出的一般制造業應由河北發展,河北做好功能區的承接和產業轉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