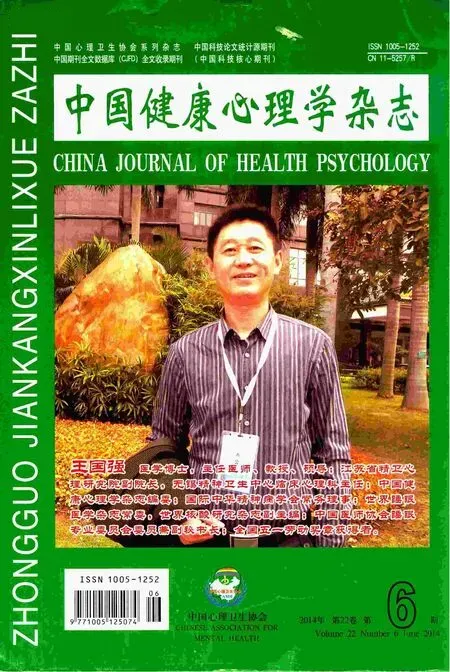養血清腦顆粒聯合米氮平治療失眠癥臨床觀察
鄭 琳 王麗萍 張曉娟 高海波
失眠是指睡眠啟動和睡眠維持障礙,致使睡眠質量不能滿足個體需要的一種狀況。失眠有多種形式,包括入睡困難、睡眠不深、易醒、多夢早醒、再睡困難、醒后不適或疲乏感,或白天困倦[1]。根據賽諾菲圣德拉堡制藥集團2002年在全球的睡眠調研結果顯示,中國地區有45.4%的人曾經歷過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2]。焦慮癥狀在失眠患者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很多失眠癥患者害怕失眠或失眠帶來的危害而產生的入睡前焦慮情緒會進一步加重患者的失眠癥狀[3]。因此,在治療失眠的同時一定要有效地控制患者的焦慮癥狀。目前臨床上除了使用苯二氮卓類藥物治療失眠外,新型的抗抑郁劑米氮平也廣泛用于治療失眠[4-6]。養血清腦顆粒是以當歸、川芎、白芍、熟地、珍珠母、元胡為主要成分的中藥制劑,具有滋陰補血,平肝潛陽,活血通絡之功效,主治血虛肝亢所致各種頭暈、頭痛、眩暈眼花、心煩易怒、失眠多夢。有人研究此藥能有效地改善失眠癥狀[7-8]。為了進一步提高失眠癥患者的治愈率,我們將養血清腦顆粒與米氮平聯合使用進行了臨床觀察,評估兩種藥物合用的療效及安全性。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所有病例均來自2013年2-11月在我院門診及住院的主訴為失眠的患者,所有患者符合ICD-10[9]中失眠癥的診斷標準,性別不限,年齡23~74歲,平均(52.6±11.6)歲;平均病程(38.9±28.1)個月;匹茨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SQI)[10]評測總分>7 分;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10]≥8 分;既往無精神病史,排除嚴重軀體疾病、合并其他精神疾病者;將62例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養血清腦顆粒聯合米氮平)和對照組(米氮平)各31例。其中研究組男性13例,女性18例,年齡(52.7±13.8)歲,病程(40.0±25.4)個月;對照組男性15例,女性16例,年齡(52.6±14.5)歲,病程(38.9±28.2)個月。兩組之間不僅在性別、年齡、病程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在基線時的PSQI 及HAMA 評分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
1.2 方法 入組前和治療2、4、6、8 周末采用匹茨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PSQI)和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治療中出現的癥狀量表(TESS)[10]及8 周末實驗室檢查評定治療的安全性。兩組間以量表評定的減分率變化為評價指標:減分率<25%為無效,25%~49%為好轉,50%~74%為顯著改善,≥75%為臨床痊愈。分別在治療前及治療第2、8 周末各評1次癥狀量表(TESS)評定其不良反應。在治療前和治療第8周末分別進行血、尿常規、血生化以及心電圖的各項檢查。
1.3 統計處理 所有資料采用SPSS 15.0 測試版進行統計分析,界定α=0.05(雙側檢驗),作相應的正態性檢驗和t 檢驗。
2 結果
2.1 兩組間PSQI和HAMA 總分的變化
2.1.1 PSQI 總分變化 研究組PSQI 總分治療2 周后與對照組比較即有顯著差異(P<0.01),至第8 周結束時,差異仍具有顯著性(P<0.05),見表1。
2.1.2 HAMA 總分變化 研究組HAMA 總分治療2 周時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但治療4 周時,研究組的HAMA總分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2。
2.2 兩組間PSQI和HAMA 減分率的對比 研究組在治療2周及8 周末PSQI 減分率與對照組相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而HAMA 減分率在治療2 周時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在治療8 周末時與對照組比較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3。
表1 研究組和對照組治療前后PSQI 的比較(±s)

表1 研究組和對照組治療前后PSQI 的比較(±s)
表2 研究組和對照組在治療前后HAMA 的比較(±s)

表2 研究組和對照組在治療前后HAMA 的比較(±s)

表3 研究組和對照組PSQI和HAMA 減分率的變化(%)
2.3 關于睡眠質量的改善 研究組在治療第2 周末時PSQI評分<7 分即治愈者有10例,治愈率為32.3%,而對照組治愈者只有5例,治愈率為16.1%,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至治療后第8 周末時,研究組的治愈者為26例,無效5例,治愈率為83.9%,而對照組治愈者為21例,無效10例,治愈率為67.7%,兩組間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
2.4 副反應比較及安全性 兩組在治療第2、8 周末,TESS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常見的不良反應為:便秘、惡心、口干、頭痛頭暈。這些不良反應大多發生在開始治療的2 周內,癥狀均較輕微,均未做特殊處理,未影響患者繼續服藥治療,隨著治療時間的延長副反應逐漸消失。兩組的血、尿常規以及血生化和心電圖等檢查在治療前后無明顯變化。
3 討論
隨著社會節奏的不斷加快,人們面臨的壓力日漸加大,失眠癥的患者越來越多。失眠癥患者主要表現為難以入睡、睡眠不深、多夢、早醒或醒后不易再睡,醒后不適以及疲乏感,白天困倦,易疲勞,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下降,導致工作效率降低生活質量下降[11]。因此很多患者極度關注自己的睡眠狀況,白天擔心自己的睡眠問題,從而引起焦慮情緒,而這種焦慮情緒反過來又會加重失眠的癥狀,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有高達50%的患者常常同時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癥狀[12-13]。所以,在治療失眠的同時也要注意改善患者的焦慮情緒,本研究從中西醫結合的治療點出發,將失眠癥患者的睡眠治療和焦慮狀態同時作為治療失眠癥的療效評價指標,探尋一種更為有效地治療方式,為更多患者解決失眠的問題。
失眠,在中醫古籍《內經》中稱為“目不瞑”、“不得眠”、“不得臥”,《難經》稱為“不寐”。其病因病機可概括為:①思慮勞倦太過,傷及心脾;②陰虛火旺,肝陽擾動;③陽不交陰,心腎不交;④心虛膽怯,心神不安;⑤胃氣不和,夜臥不安。由上而知,失眠原因很多,但總是與心脾肝腎及陰血不足有關,其病理變化總屬陽盛陰衰,陰陽失交。因為血之來源,由于水谷之精微所化。上奉于心,則心得所養;受藏于肝,則肝體柔和[14-16]。
TNS(中國)調研公司2006年中國6 城市普通人群睡眠問題調查報告:只有27%的患者接受醫生的治療。在接受藥物治療的患者中,有的患者接受苯二氮類藥物治療,有的患者接受抗抑郁藥治療,有的患者接受中醫藥治療或中西醫結合的治療。由于苯二氮類藥物有藥物依賴、撤藥反應及失眠反彈等副作用,傳統三環類藥物有抗膽堿能副作用及心律紊亂、過量致死等危險,所以非精神科醫師需要謹慎應用。
米氮平是一種去甲腎上腺素能和特異性5HT 能抗抑郁劑,具有獨特的雙重作用機制,臨床上除用于治療抑郁癥之外,也可以用來改善失眠癥狀。在臨床試驗中,米氮平除有鎮靜過度的副作用外,還有食欲增加、體重增加、浮腫以及靜坐不能等副作用[17-18]。
養血清腦顆粒中當歸、川芎、白芍、熟地黃組成為四物湯,其功效為補血和血;其中川芎為血中之氣藥,走而不守,上行頭頂,活血化瘀;當歸補血活氣,祛風止痛,二者皆為君藥;熟地、白芍和珍珠母補血養腎,養血滋陰和平肝潛陽為臣;佐藥決明子、夏枯草藥性寒涼,能清肝之熱而抑陽之亢,使藥細辛則起通竅作用。雞血藤補血行血,舒經活絡;鉤藤平肝熄風,潛陽;延胡索活血行氣。故養血清腦顆粒功效為補血活血,平肝熄風,兼清肝火。主治血虛肝亢所致各種頭暈、頭痛、眩暈眼花、心煩易怒、失眠多夢。而失眠多夢,心煩易怒,膽怯心悸,遇事善驚,類似現代醫學中的焦慮現象。而動物實驗證實,養血清腦顆粒能明顯減少小鼠的自主活動,對小鼠具有一定鎮靜作用,能明顯延長使用戊巴比妥鈉后小鼠的睡眠時間,具有催眠作用,且均與閾下劑量(不引起明顯藥理作用的劑量)的戊巴比妥鈉有協同作用,亦說明養血清腦顆粒具有一定的鎮靜、催眠作用[19]。所以有助于緩解患者的失眠癥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米氮平聯合養血清腦顆粒治療失眠癥明顯優于單獨使用米氮平治療,兩組在治療后PSQI和HAMA總分均較基線時有明顯下降,而且研究組的PSQI 分數在治療2、4、6、8 周末時均顯著低于對照組,HAMA 總分在治療4、6、8周末時顯著低于對照組;研究組的PSQI 減分率在治療2 周及8 周時顯著高于對照組,而HAMA 減分率在治療8 周后顯著高于對照組;研究組治療失眠癥的總有效率達83.9%,對照組為67.7%,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說明聯合用藥起效更快,療效更好;同時,觀察在治療過程中出現的副反應,兩組間的TESS 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實驗室檢查也未見明顯異常,提示養血清腦顆粒的安全性較高,聯合使用并不加重單獨用藥的副作用。
綜上所述,米氮平與養血清腦顆粒聯合使用,具有標本同治、緩急兼顧之功效,兩藥配合取得了滿意療效,能更快、更有效地緩解失眠癥患者的失眠癥狀以及焦慮癥狀,且安全及耐受性好。
[1]郝偉,于欣.精神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151-157
[2]失眠定義、診斷及藥物治療共識專家組.失眠定義、診斷及藥物治療專家共識(草案)[J].中華神經科雜志,2006,39(2):141-143
[3]劉勇,印玲.情緒異常與失眠的相關性研究[J].實用診斷與治療雜志,2008,22(3):238-239
[4]唐章龍,唐健,徐英納,等.米氮平治療失眠癥的臨床效果觀察[J].實用全科醫學,2007,5(15):407-408
[5]朱金富.米氮平與氟西丁治療老年抑郁癥患者的對照研究[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6,14(5):199-200
[6]宋傳福,李江涌.失眠癥患者臨床用藥情況分析[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09,17(4):655-656
[7]黃各寧,陳積優.養血清腦顆粒治療婦女更年期失眠及其對內分泌激素影響的觀察[J].中醫藥臨床雜志,2007,19(1):42-43
[8]陳金鷗.養血清腦顆粒治療失眠的臨床觀察[J].中國醫院用藥評價與分析,2007,7(6):461-462
[9]劉平,許又新.ICD-10 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研究用診斷標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107-110
[10]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21-133
[11]郝偉,于欣.精神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152-159
[12]張露,嚴由偉.元擔憂和失眠的關系[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1,19(3):899-890
[13]李融,侯鋼,武玉蘭,等.失眠相關因素調查[J].上海精神醫學,2002,14(1):28-33
[14]王永炎.中醫內科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32-136
[15]嚴曉麗,王翹楚.王翹楚教授從肝論治失眠癥[J].北京中醫藥,2008,27(1):22-23
[16]王翹楚.失眠癥的中醫診斷辯證與治療[J].中醫藥通訊報,2006,5(5):10-13
[17]沈漁邨.精神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900-901
[18]申秀云,周俠.米氮平與帕羅西汀治療抑郁癥對照研究[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07,13(5):446-447
[19]高雅玲,王彩娥.養血清腦顆粒對小鼠的鎮靜催眠作用[J].鄭州大學學報:醫學版,2007,42(5):88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