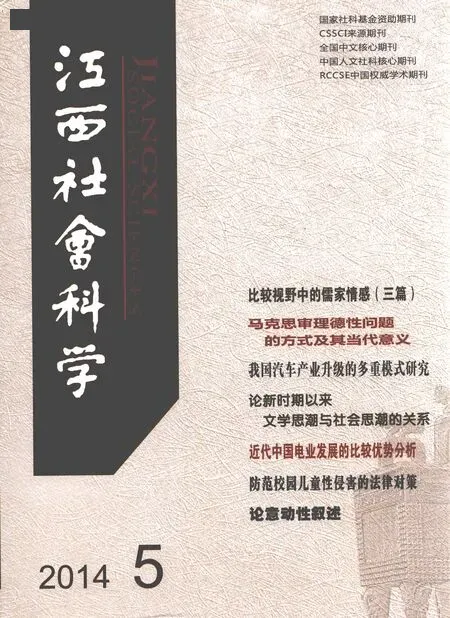后昆體七律的內容拓展與時代特征
■張立榮
北宋在太祖朝的十六年間,尚處于東征西戰的國土擴張期,在太祖駕崩的前一年南唐瓦解,北宋完成國土統一。在此期間,黃袍加身的宋太祖深刻體會到軍權的可怕,繼位不久就采取“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巧妙剝奪了將領的權力。為作出補償,他以厚金賞賜,并進而提倡享樂之風,為五代入宋詩人徐鉉、李昉等人的享樂詩風奠定了政治基礎,提供了思想指南。太宗朝始治文藝,促使白體七律的享樂唱和詩風大盛。到真宗、仁宗朝,經過近四十年的經濟復蘇及文化建設后,從朝廷到市野,呈現出一幅盛世繁榮景象,這一點在詩、詞、賦、圖畫、音樂等方面皆有體現。有學者將其概括為文人的“治平心態”①,體現在詩學上,是雍容典贍的西昆體詩風的出現。
本文將《西昆酬唱集》結集前,昆體的開創期作家,稱為“西昆體詩人”或“前期昆體詩人”;將結集后學習西昆體的詩人,稱為“后昆體詩人”。②后者與前者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前者有明確的學習對象,有近似的詩歌主張,有相對固定的創作場所,這使他們的詩風體現出驚人的一致性;而后者只是受西昆前期詩風影響,既無固定的人員構成,也無共同的詩歌主張,只是流風所布,應者云集而已。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曾云:“世但知楊、劉、錢、晏數子,不知宋初諸名家,往往皆同,蓋一時氣運使然。”[1](P223)這一點與白體、晚唐體詩人群體類似。因此,后昆體詩人在七律創作上,除有西昆體的某些特征外,還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及時代風尚,他們的詩風也因此呈現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本文將夏竦、晏殊、宋庠、宋祁、胡宿、文彥博、趙抃、余靖、王珪、蔡襄等人歸為后昆體詩人,探討后昆體七律在內容取舍上與西昆體的不同,進而看出在《西昆酬唱集》出版一年即遭禁的情況下,士人在詩歌內容取向上的及時調整和對皇權的迎合。
一、對西昆體七律的揚棄及士人心態的轉變
西昆體七律最擅長的題材為詠史、詠物、愛情三大類,這既是對李商隱七律的繼承,也是對宋初白體七律的反撥。這三個題材中又以詠史七律成就最高。后昆體詩人在這三大題材上既有繼承又有變化,但后昆體詩人的詠史七律成就并不高,數量也較少,而且大多變詠史詩為懷古詩。其原因應與創作環境有關。西昆體七律屬典型的館閣創作,而后昆體詩人的游宦經歷和豐富學識,使他們對游歷之地多起懷古之思。
后昆體詩人中,夏竦的懷古七律別具一格,如《江南懷古》、《金陵》等。西昆體的詠史詩,以敘事為主,在感嘆中寓微諷。夏竦懷古七律則是將景物與歷史相結合,邊敘邊議,詩旨明快,毫無諷意,反而暗含著對當時王朝的歌頌。如此立意在懷古詩中極少見,顯示了詩人獨特的歷史視角及歷史觀。作者在詩中并不是純發議論,而是攜情思以行,尤以思致取勝,這又顯示出對西昆體言志寫意一面的發展。
胡宿的詠史懷古七律也較有特色,懷古詩有《湘夫人祠》、《過李白墳》、《函谷關》等,詠史詩有《淮南王》、《長卿》、《舊將》、《飛將》、《公子》等。從詠史詩題可明顯看出胡宿對西昆體的繼承與模仿。其《長卿》詩以凝練的筆墨概括了司馬相如的一生,特別是頸聯“已托焦桐傳密意,更因殘札寄遺忠”,不僅對仗極其工整,而且寫盡了司馬相如人物之風流、文采之出眾。尾聯以問句回收全詩,顯示出作者對大賦諷喻筆法的懷疑。胡宿本人工于四六駢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二言:“當時文格未變,尚沿四六駢偶之習,而宿于是體尤工。所為朝廷大制作,典重贍麗,追蹤六朝。”[2](P1310)胡宿對司馬相如大賦諷喻功能的懷疑,正反映了詩文革新前夕,后昆體詩人自己對典贍偶麗之作的否定,也由此預示了詩風由昆體之偶麗向平淡轉變的跡象。
王珪的懷古七律,在風格上類似晚唐許渾的懷古七律,以感慨抒情為主,算是后昆體詩人中此類題材比較突出的。其《三鄉懷古》、《游賞新亭》、《登海州樓》等皆由眼前景物引發出悠悠懷古之情,意境蒼涼凄迷,以抒發悲慨之感為主,與其代表詩風“至寶丹體”七律判若兩人之作。但畢竟受時代影響,他的懷古之作中也有以議論為主的作品,如《登懸瓠城感吳季子》,此詩一句一事,議論縱橫,絲毫不講含蓄,是典型的宋型詩風。
宋祁、宋庠等亦有懷古七律,但不僅數量少,質量亦平平,未能代表其創作水平。由此看出,在西昆體七律中成就最高的歷史題材,在后昆體詩人這里并未受到青睞。除地域與環境因素外,當與后昆體詩人的心態有關。論歷史與文學素養,后昆體詩人并不輸于西昆體詩人,而七律詠史懷古成就不高,應有其政治因素。《西昆酬唱集》問世僅一年左右,就遭朝廷禁毀,應與其詠史詩所含的對朝廷的諷刺意有關。后昆體七律在此題材上采取了有意規避的安全措施。
后昆體詩人對愛情七律創作也較少。夏竦在這一題材上的創作比較突出,如《仙姬怨》、《宮詞》等從女子角度立意的詩作;宋庠有一首《無題》詩。這些詩細膩工整,但較昆體《無題》類詩作,顯得秀媚明快。夏竦《宮詞》的尾聯“夜來夢上檀香閣,猶映珠簾避貴妃”,有一種小心翼翼、惟恐罹禍的心理,頗類昆體同類詩作詞旨幽微的感覺。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上曾云:“夏英公竦每作詩,舉筆無虛致。”[3](P3)宋魏泰《東軒筆錄》卷二言其“平生好為詩,皆有所屬”[4](P20)。朝政的復雜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詩人是否將為政的感慨寄托于此也未可知。李商隱自創《無題》詩以來,是否有寄托,就是詩壇一直爭論的話題,西昆體與后昆體七律的此類作品,也面臨同樣的爭議,此處暫且不論。只以此題材來看,后昆體七律的大量縮減,一方面與愛情題材向詞轉移有關,另一方面當與詠史詩一樣,有其政治因素。這種詞旨幽微的詩作,自后昆體之后,在北宋七律中較少創作,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應與詩詞分野的詩學觀有關。北宋詞作及詞論的發展,逐漸達到偏離詩學而獨立的地步,晏殊詞中用了不少其七律原句,詩詞尚未有明顯界限,但在宋祁、歐陽修等人的創作中,我們已可明顯看出“詩莊詞媚”的詩學觀已漸成共識。
詠物七律是后昆體詩人創作成就較高、模仿西昆體七律最成功的一種題材。二宋的《落花》詩,是此中典范,托物寓意,深婉含蓄,繼承了李商隱及前期昆體詩人重寄托的表現手法,而摒棄了前期昆體詠物七律中堆垛典故、詞繁意淺的特征。余靖的詠物七律《落花》、《和錢學士見謝新栽竹》、《和胡學士館中庭樹》、《回雁》等在選詞用語的精挑細選、風格的典麗精工及審美情調的細膩幽婉方面最類西昆體。文彥博詠物詩《幽蘭》、《桃花》、《柳絮》、《重陽前五日探菊》等亦此種風味。胡宿的詠物之作在后昆體詩人中,數量最多,特征也最明顯,在選詞設色、組織用典方面幾乎完全采用昆體手法,如《嘲蝶》、《雪》、《殘花》、《橘》、《太湖石》、《竹》、《詠鶴》、《千葉瑞荷花》等詩,皆華麗工巧、屬對親切、音韻諧婉,大多借用相關典故細致地摹寫物象。與李商隱詠物詩相比,缺少比興寄托及一唱三嘆的韻味,而與西昆體諸公的《梨》、《淚》等詩相比,卻略顯疏朗。何焯曾評其《雪》詩,認為“亦昆體,但較之唐人不無粗直耳”[5](P436),“不無粗直”正是其泥于典故及物象而缺少唐詩神韻之處。《落葉》在摹寫物態的同時,抽繹出“萬物歸根”之理,這就將傳統詠物詩的托物言志引向借物說理,漸開北宋詠物七律的理趣之門。這與晚唐詠物詩的“比物諷刺”顯然不同。[6]雖然這種傾向在其詠物七律中尚不明顯,但畢竟已漸露端倪,昭示了詠物七律由唐詩的抒情言志向宋詩的體物說理演變的發展方向。
從以上可見,在西昆體七律中備受青睞的三大題材,后昆體詩人做了不同程度的揚棄,詠史、愛情七律數量不多,質量也不高,詠物七律頗有佳作。西昆體遭禁的主要原因應是詠史及無題詩中隱含的諷刺之意,后昆體對這兩類題材進行了有意的規避,這一微妙的心態變化直接反映到他們對前輩題材的取舍上。
二、應制題材的突破及時代特征
奉和應制七律是后昆體七律中最富麗堂皇也最具特色的一道風景。七律在初盛唐創制之時,就以奉和應制的面貌出現,在宋初白體七律中表現比較突出,在后昆體詩人手中創作大盛。夏竦、晏殊、王珪、胡宿、宋祁等在這方面皆有突出表現。這一題材,由于限制較多,比較容易雷同,如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言: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實富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啟玉京。冉冉游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云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沽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調當如是也。[7](P498)
說明了后昆體頌美詩風的大同小異,但事實上他們的詩風各有不同。
夏竦的奉和應制七律較之北宋前期的奉和應制詩增添了新的內容。前期奉和應制詩常見詩題如《和御制賞花詩》、《奉和御制雪》等,皆為普通詠物詩,而夏竦奉和應制詩中許多反映祥瑞之氣的事物被頻頻歌詠。當然,奉和應制詩的內容取決于皇帝,但從夏竦此類詩的內容變化上可以看出,在宋真宗東封西祀之后,各地為了迎合上意,開始進貢傳說能體現天下太平的祥瑞之物,這些物件又被皇帝用來作為與群臣唱和的材料,如《五月同州奏牡丹一枝開三花》、《閏六月眉州奏禾生九穗》、《八月梓州奏光化寺池蓮五莖各開二花》等。這種奉和應制七律的出現,反映了真宗、仁宗朝天下承平的氣象,也體現了那個時代體認的“天人感應”思想。七律的頌美功能幾乎被發揮到了極致,似乎回到了它初創期的高貴地位。七律從初盛唐的宮廷走向民間,而今在后昆體詩人手中又從民間重回宮廷。但從奉和的內容及風格來看,早已失去了盛唐的磅礴大氣,只是更加富艷精工而已。奉和應制七律內容與風格的變化反映了唐宋文人精神意趣的差異。
晏殊與夏竦的奉和應制詩的內容略有不同。晏殊的奉和應制大多是節日慶典之作,如《奉和圣制除夜》、《奉和應制元日》、《奉和圣制上元夜》、《扈從觀燈》、《奉和應制社日》等。其應酬唱和之作也以節日及宴集為主,如《和至日北園宴集》、《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勘》、《次韻和王校勘中秋月》、《九日北郡登高見寄》、《九日宴集和徐通判韻》、《次韻和史館呂相公九日偶成》等。經過宋初三朝的休養生息后,國家到仁宗朝達到風物全盛,經濟的發展,都市的繁榮,表面的承平,使整個社會由上而下沉浸在一片安樂祥和的氣氛中。早期太祖皇帝就提倡的享樂,在仁宗朝初期發展至頂峰。晏殊的應制詩與夏竦的頌詩、柳永反映太平盛世的詞一脈相承,正如《東京夢華錄》真實記錄北宋都城的繁華景象一樣,晏殊等人的七律適時地反映了時代特征。
從晏殊與夏竦的奉和應制詩的內容差異來看,在真宗朝后期,達官貴人還沉迷于符瑞呈祥的氣氛中,到仁宗朝前期則變成了現實的享樂,尤其是借詩歌反映節日的盛況,展現出一個王朝經濟與文化的繁盛。從晏殊七律中可以看出一年四季,從元日到除夜,幾乎每個節日都有皇帝的御制及個人宴集的酬唱。這從另一側面反映了北宋中期享樂之風的發達,或可為詞作的繁盛提供理論依據,也說明了后昆體七律中對個人情懷的悲苦吟唱始終未能成為主旋律。時代詩風擯棄了晚唐體的“悲”“苦”,繼承了白體的“頌”“樂”。
王珪最為人稱道的詩作是《恭和御制上元觀燈》,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言此詩“典實富艷”,與夏竦《和上元觀燈》如出一人之手,并言宋神宗在眾多和作中,獨賞此詩,云“妙于使事”。[7](P498)王珪七律中確有一些辭藻華美、工于使事、典實富麗的“至寶丹體”七律,如《依韻和賈直孺舍人初春祠左太乙二首之一》、《上元》、《題道錄陳景元中太乙宮種玉軒》等。這些詩大多采用與皇家相關的意象,組織成瑰麗的意境,鏤金錯彩,美艷精工,不僅是其一生優游富貴的體現,也展示了北宋仁宗朝經過宋初休養生息后漸至全盛期的富麗堂皇。宋祁的《聞圜丘禮成肆眚》、《元夜觀正陽賜宴》、《再侍經筵有感》、《禮局致齋》、《禁門待漏》、《觀上朝》等,以敘事為主,典實雍容,較之他人略有不同。胡宿的奉和應制大多描寫京都的宏偉壯觀及個人的安逸心態,繼承了夏竦、晏殊的頌美及抒寫安樂之情的主基調。這些詩或典麗華贍,氣勢闊大;或雍容富貴,神氣安雅,體現了一個王朝進入全盛期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早期昆體詩人用鏤金錯彩的語言表現的是一種憂傷感,這與李商隱類似,而夏竦率先將這種文風用在了歌功頌德上。楊億提倡頌美,《西昆酬唱集》卻多事微諷,真正用西昆詩風頌美的是后昆體詩人。
三、對其他題材的拓展及詩學意義
后昆體詩人在其他題材上,也做了多方面的拓展,以寫景詠懷詩成就最高,在技巧上也很有新意,顯示出后昆體詩人在詩藝上力求突破唐詩所做的努力,在寫志言意方面也有較大創新,擬分別論之。
在唐詩中反復出現的對自身遭際的詠嘆,在后昆體七律中未成主旋律。對自身遭際的詠嘆集中體現在二宋的詩作中,尤其是宋祁。二宋許多詠懷詩都感嘆世路風波的險惡,宦海浮沉的無常及對湖海盟鷗的眷戀。在宋庠七律中屢次提到回歸田園的渴望,而宋祁詩中卻充滿了憂饞畏譏、嘆老念衰的內容,正如《載酒園詩話》所言:“善寫牢騷之況。”[8](P409)詠懷之作一般借自然物的變遷引發人世之感慨,而昆體詠懷詩卻借用大量典故來抒情,成為與搖曳的唐風完全不同的宋調詠懷詩。二宋可謂是北宋較早使用昆體手法大量寫詠懷七律的詩人。
這種個性化的內容不僅是詩人一己之感情的體現,更反映了北宋仕宦制度對文人心態的影響。北宋時期,官員多起自畎畝,憑自身的才華躋身政壇,不一定有家族背景和經濟實力,全靠自己在政界艱難摸索,動輒罹禍。宋庠雖身至相位,一生卻沒有晏殊那樣優游富貴,而多次貶外。宋祁一生更是沉浮不定,曾四為學士,五出外郡。兄弟二人皆出身平民,又皆高中皇榜,以才華見取于時,走上仕途,又同時經歷了宦海浮沉,所以,他們的七律既有得遇皇恩、如沐春風的快感,也有見棄遭貶、憂思沉痛的悲情。尤其宋祁的四百余首七律就像他的一部仕途風波史,反映了文人入仕后屢起屢貶的遭際,但這類詩作在整個后昆體七律中并不占主流,反映了時代詩風的由悲轉樂。
后昆體七律寫景詠懷之作成就最高,風格最多樣,手法也較獨特。夏竦的部分寫景詠懷之作,與《西昆酬唱集》同類作品大異其趣,如《帝京春日》、《寒食》、《春游》,這三首詩從不同角度描寫了京城春日的繁華景象,尤其“一帶樓臺擎落月,萬家桃李待朝輝”,氣勢宏闊,筆力開闔,只有身處太平盛世,深受其潤澤的人才能有如此欣欣向榮的感受。這些詩的確反映了北宋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之后,在真宗、仁宗朝進入了太平盛世,作為現實的神經,詩歌最敏銳地感受到了它的變化。連布衣詞人柳永的《迎新春》都言“太平時、朝野多歡康阜”,何況是富貴優游四十年的夏竦,他的體驗就更為真切直接。所以,我們從詩中讀不到歌頌的矯情,反而可以跟著詩人一起體驗身逢盛世的安樂和平。這些詩語言絢麗而不濃艷,用典而不晦澀,富貴而不鄙俗,風骨高秀,華實并茂。詩人還極擅長剪裁之功,常常不正面描寫熱鬧場面,而是鬧中取靜,以靜襯動,給人留下無限的想象空間。
宋庠寫景抒情之作以兩類為主,一類瑰麗典雅,一類沉博開闊。這些詩淡化了借風云月露等自然意象抒發感情的晚唐體七律特征,而將典故與抒情寫景相結合,形成了別具特色的昆體抒情詩,或可稱為宋型抒情詩。李商隱七律將借典抒情固定成一種創作范式,前期西昆體詩人已經體認到這種新的創作手法,并將它帶入北宋七律詩壇。后昆體詩人,尤其是宋庠繼承并發展了這一手法,對前期昆體抒情詩從形式到內容進行全面改造,開闊了抒情范圍,形成雍容舒緩、含蓄蘊藉、典雅瑰麗的抒情詩風。宋祁除此之外,尚有清麗之作。
胡宿的山水寫景七律《夏日舟行》、《芙蓉湖泛舟》、《過桐廬》、《江城春日》、《題漣漪亭》等,風神俊秀,色彩明艷,既不同于晚唐詩之哀感頑艷,也不同西昆體之繁縟秾麗,真可謂“興象高遠,優入盛唐”[1](P225)。他的借景言懷之作中,還有一類略有晚唐風調,如《宛陵秋晚》、《早夏》等,語言清秀典雅,情調凄婉感傷,含韻悠長,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卷九所言“起結尤多義山神理”者,當指此類詩。因此,胡宿七律整體上體現為“唐音”。但他畢竟身處北宋,尤其受西昆體影響,創作時代又正值西昆體逐漸衰落而詩文革新運動逐步醞釀之時,所以他的七律仍然洗滌不盡宋詩意味,如《山居》:“老矣求田魚稻鄉,兒孫常要在余旁。提籃買菜須靈照,舉案齊眉只孟光。醫國有方三折臂,扣關無路九回腸。紫芝白發秋風里,悵望商山綺與黃。”這首詩語言質樸平淡,用典卻不少,正是后昆體詩人以平淡變西昆體秾麗的又一嘗試,屬典型的宋型七律。
蔡襄亦極善于寫景,他的七律中成就最高的即是山水寫景之作。即便在其他題材詩作中,蔡襄也常插入一聯景物描寫,這一聯往往成為全詩的亮點,使整首詩反而有難見全璧之憾。④蔡襄在山水寫景七律上的一個突出貢獻是采用了連章組詩的形式,他的《漳南十詠》分別寫了白云亭、城東水閣、滿月池亭、龍臺、西湖、南山廟等十個景致。這種七律組詩形式,自杜甫開創《秋興八首》后,繼作者并不多,可能因為七律章法較嚴,成詩不易,像蔡襄這樣連寫十首的確不多見。
在言志寫意說理方面,后昆體七律最有創變。先不說以詩說理言志,是否合乎詩的本質特征,也不言其優劣,但就其創新而言,顯示出宋人在突破前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宋詩之所以迥別于唐詩,也正是在這方面的融匯與突破。如夏竦的七律《話道》,主旨是反對求仙,但與西昆體反真宗求仙的詠史詩欲吐又吞,戰戰兢兢的風格相比,此詩顯得更為大膽直率。這是一首典型的宋調七律,詩題就與一般唐詩不同,在創作手法上繼承了白體的“以議論為詩”,也融合了昆體的“以才學為詩”,呈現出獨特的宋詩面目。此前七律極少有類似風格的作品,因此,盡管夏竦只作此一首,卻透露出北宋七律漸變的端倪。在這方面有突出成就的還是二宋,宋庠數首言志寫意七律,如《世事》、《求志》、《淮南自訟》、《乾興詔罷自詠》、《郡圃觀春物有感》、《晚春小園觀物》等;宋祁的《自訟》、《古意》等。這些詩作從詩題上就可看出對傳統七律題材的突破,尤其“觀物”之作,體現出詩人在“格物致知”方面的思考,這類詩作在七律中的出現,意味著宋代理學的學術思維方式向詩歌創作的滲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胡宿還有三首比較特殊的類似讀后感作品,如《覽朱表臣卷》、《覽孫佑甫卷》、《覽海東相公尹川集》。讀后感七律的出現,一方面體現了宋人之博學,另一方面也是宋詩學問化、議論化傾向于七律創作中的滲透。
趙抃在這方面也有突出貢獻,他的言意說理七律,如《勸學示江原諸生》、《勉郡學諸生》、《青州勸學》、《勸成都府學諸生》、《信筆示諸弟侄子孫》,這些詩作繼承了白居易七律好議論說理的風格,但其說理方式卻不是借物言理,而是用樸實的語言直接說教。所言之理也不是玄妙的哲理或普遍的事理,而是實用的為學做人之道,詩的內容讓我們聯想到韓愈的《勸學篇》。趙抃用七律表現散文內容,開拓了七律的題材,這也是“以文為詩”在內容方面的體現。言理勸學七律的出現,反映出北宋仁宗朝儒學的重建及對士人“人格”、“氣格”的要求。氣格之健舉直接關系到詩風之健舉,這正是歐陽修等詩文革新詩人的努力方向。
純粹說理言志寫意作品雖然不多,成就也不算高,但后昆體詩人在七律上的創新卻不容忽視,尤其是對這種創作手法的嘗試,其后成為宋人的一種思維慣式及宋詩的主要特征,不得小覷。
宋初三體中,最關注現實的當屬西昆體,可惜由于其詞旨幽微,反因形式被詬病近千年。詩人之旨,不可不察也!后昆體詩人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往往被看成是對西昆體的糾正,實際上只是對西昆體的發展。七律關注現實,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對杜甫的接受,二是受詩文革新精神的影響。
在對現實的關注上,趙抃七律表現得最為明顯。他的七律內容突破了后昆體詩人常見的寄贈送行、詠物懷古、寫景詠懷之作,而出現了關心時事政治、國計民生等內容,繼承了杜甫開創的以七律寫時事的傳統,如《聞嶺外寇梗》、《武林閱兵》。在《夏末喜雨》一詩中,他還表現出與百姓同喜同憂之情。趙抃還有一些詩也表現出與民同樂之情,如《過左綿偶成》、《寄永倅周敦頤虞部》、《次韻錢顗喜雨》、《次韻董儀都官見贈》,這些詩突破了后昆體詩人的閑適宴游之樂,將一己之情與天下蒼生相聯系,正是范仲淹“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表現;而其《虔州即事》、《再有蜀命別王居卿》等詩為我們刻畫出一位不畏艱險、迎難而上,為國家政務勞苦奔波、任勞任怨的朝廷官員形象,體現出范仲淹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北宋中期士大夫精神。因此,方回曾言:“其人可敬,不止于詩。”[9](P1426)余靖寫時事七律有《賀運使學士分散傜人》、《聞欒駕部度嶺見寄》,這些詩筆力勁健,善用典故,組織工整,正類西昆體中風格較為勁健的詩作。
由此可以看出詩文革新精神對后昆體詩人的影響已經從詩風的平淡深入到內容的關注現實,也體現出后昆體詩人由二宋的多表現個人內心感受轉向對外部世界的關注。
后昆體七律中出現了純粹寫日常生活題材,表現親情的詩,如蔡襄《馬馭周思之因成》,詩的第三聯寫小兒咿呀學語、踉蹌學步的姿態十分傳神。趙抃七律中還有幾首表現親情的詩,如《憶信安五弟拊》、《憶松溪三兄縣尉》、《送十二弟太博揚倅潭州》,這在多寫較為嚴肅題材的七律中極為少見,預示了北宋七律題材的生活化傾向,而注重在詩中反映日常生活情趣正是詩文革新詩人七律的發展方向。
胡宿的邊塞七律明顯體現出其詩健拔遒麗的一面。《塞上》詩起句就先聲奪人,充滿了昂揚樂觀的進取精神。《涼州》詩則略有蒼涼之感,頗類詠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其五七言律詩,波瀾壯闊,聲律鏗訇,亦可仿佛盛唐遺響”[2](P1310),此類詩作可以當之。
日常生活題材在后昆體七律中尚屬嘗試之作,但指示了北宋七律內容的開拓方向,梅堯臣、蘇軾、黃庭堅的七律在這些方面皆有不俗表現。
四、結語
綜上可見,西昆體七律主要以詠史、詠物、愛情及寄贈酬唱為主,總體情調上多體現悲感。后昆體詩人的七律繼承了楊億的“頌美”理論,以昆體華麗典贍的文風歌頌王朝氣象,這種作品在《西昆酬唱集》中幾乎沒有。西昆體詩人以詠史寫時事,后昆體詩人則繼承了杜甫七律的直接以時事入詩法,擴大了北宋七律的題材。言志寫意內容的發展,是對白體七律的繼承,更是突破。一些七律中不多見的題材,如邊塞、題畫等,后昆體詩人也有嘗試。在總體情調上,后昆體詩風較少悲情而多為閑適優游之樂,體現出對白體內容上的回歸。[10]這些內容方面的取舍反映了北宋士人在面對皇權時,出于安全考慮,在詩歌創作中做出的選擇。這些選擇一方面固然體現了現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明顯看出詩學內部的發展規律本身的整體性及頑固的延續性。
注釋;
①劉培在《雍容閑雅的治平心態的流露》(《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澶淵之盟后,真宗有意渲染太平氣象,造成文人的太平心態。”在《論北宋真仁間辭賦創作的治平心態》(《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一文中進一步闡發:“所謂治平心態,是指在太平環境中形成的以優游不迫、縱逸閑雅、細膩深婉為感情基調的心理態勢。”
②在古代文論中,沒有西昆體與后西昆體的劃分。20世紀30年代末,梁昆《宋詩派別論》將晏殊、二宋、文彥博、趙抃、胡宿等稱為“西昆余派”。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中,將仁宗朝受西昆體影響比較明顯的詩人稱為“西昆派的后期作家”。程杰《北宋詩文革新研究》有“西昆體”與“后西昆體”的稱謂。祝尚書有《論后期“西昆派”》一文,見《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5期。
③北宋時期的《古今詩話》、《中山詩話》等已經將晏殊與楊億、劉筠等人并稱為西昆體詩人。方回在《送羅壽可詩序》中將“二宋”歸為西昆體,在其所列西昆體詩人中,只有二宋沒有參加過西昆酬唱。清王士禛等又將文彥博、胡宿、趙抃等人歸入西昆體詩人。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二十引《三山老人語錄》,認為余靖《落花》詩“可亞于二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王珪為“二宋之亞也”。清吳喬《圍爐詩話》認為蔡襄近體詩“洗滌不盡西昆”。清翁方綱《石州詩話》卷三稱胡宿、王琪“皆堪于晏、宋方駕”,但因為王琪七律只有一首,且并非昆體風格,本文不涉及。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三之《恢大山西山小稿續》云:“別有一派曰昆體,始于李義山,至楊、劉及陸佃絕矣。”陸佃(1042-1102)年輩較晚,此處不論及。曾棗莊《論西昆體》一書中認為《西昆酬唱集》外的昆體詩人有李建中、石中立、晏殊、胡宿、二宋、文彥博。段麗萍的博士論文《后期“西昆派”研究》認為,后昆體詩人有夏竦、胡宿、王珪、晏殊、王琪、二宋、文彥博、趙抃。昆體詩風影響達三、四十年之久,詩風受其影響者,不止數人,歐陽修早年七律也從西昆體入手,但不占主流,所以不將其列入后昆體詩人群。西昆體詩風在七律創作上體現得比較明顯,因此本文確立的后西昆詩人群體基本以其七律詩風為標準。
④明謝肇淛評蔡襄七律云:“惜其全璧寥寥,才學筆氣尚在蘇、黃之下。”見(清)方坤編:《全閩詩話》卷二引《小草齋詩話》語,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明)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3](宋)文瑩.湘山野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4](宋)魏泰.東軒筆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3.
[5](清)錢牧齋,何義門.唐詩鼓吹評注[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
[6]郭鵬.晚唐五代“苦吟”詩風的“比物諷刺”內涵及其意義[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
[7](宋)葛立方.韻語陽秋[A].(清)何文煥.歷代詩話[C].北京:中華書局,1981.
[8](清)賀裳.載酒園詩話[A].郭紹虞.清詩話續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李慶甲.瀛奎律髓匯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張立榮.論徐鉉七律詩風的轉變及其詩學內涵[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